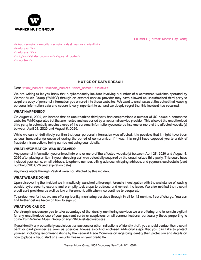我失败的音乐生涯
我很早就到了最后一次试镜,定于2018年12月的一个星期五上午9点20分。我在市政厅音乐与戏剧学院的门厅里坐了一个小时,然后被派去弹钢琴热身,我的贝多芬、肖邦、拉赫玛尼诺夫、格什温和格拉斯的节目在我脑海中回旋。评审团的两名成员坐在一个原本空荡荡的演讲厅里的一排座位的顶部,除了下面舞台上的施坦威。我玩的时候,一片混乱。我往往会忘记表演的细节,但我知道有绊倒、握手、调整凳子的情况。有一次-尽管我不能肯定-我记得有一块完全松开了。后来,当我尴尬地坐在评审团下面一排的椅子上进行“面试”时,我对失败的怀疑得到了加强,谈话持续了不到5分钟。几天后,我收到了我的拒绝--我在一家音乐学院攻读表演、钢琴和硕士学位的海选最终结果。我没有被皇家学院或皇家音乐学院录取,但曼彻斯特的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给了我一份录取通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就不会去了。我会放弃对音乐事业的追求。我四岁开始弹钢琴,别人告诉我我很有天赋。我很幸运,有支持我的父母,也有机会学习乐器和课程。音乐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对我说话,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我发现我的音调很完美。这让我深深地、亲身感受到了即使是最傲慢的流行音乐的细微差别,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从父亲那里借来的晦涩CD(Pat Metheny,Moondog,Imogen Heap)和我们在青年交响乐团演奏的任何晚期浪漫主义交响乐之间听过这种细微差别。虽然我继续每周上一次钢琴课,直到18岁离开家,一路上还学会了大提琴和萨克斯管,但我总是对自己在别人面前演奏的能力缺乏信心。我很紧张,太尴尬了,无法在舞台上完全表达自己的意思。我认为这是我焦虑性情的一部分。然而,总是准备不足也无济于事。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位钢琴老师告诉我应该做的事情:练习,直到你不能弹错为止。当我在大学学习音乐时,我发现它不像在学校时那样是我的了。其他人分享了我的热情-而且做得更好。我的许多同龄人的才华不仅得到了慈爱的父母和鼓励教师的培养,也得到了精英机构(少年音乐学院、国家青年交响乐团、BBC青年音乐家)的培养。与其试图竞争,我更愿意写文章而不是玩耍。私下里,我被嫉妒吞没了。我担心退出钢琴会以某种方式颠覆我自己的命运。同样,我太害怕在总是成功的同龄人面前失败,不敢尝试。在我的课上,我需要越来越多的安慰。与其说我对我正在演奏的东西感兴趣,不如说我只想把它打好。我问我大学的钢琴老师,一位来自皇家学院的教授,是否值得我继续下去。“那里有人才,”他耸了耸肩,“但这需要大量的工作。”毕业后,我开始在市政厅跟一位硕士学生上课。在我的第一节课上,我焦急地问她是否认为我好。“是的,”她说。“是的。但我的意思是,“--她同情地笑了--”你永远不会成为霍洛维茨。“。2018年初,我在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理人员,与正在攻读表演学位的学生进行了互动。我不能放弃可能是我的想法。我决定测试一下这个理论。我找到了一位新老师。我决定第二年申请名牌音乐学院的硕士课程。我大学的钢琴老师曾建议,要想达到我想要的水平,我应该开始每天至少练习两三个小时。我会照他说的去做,看看我到底有多棒。凭记忆学习45分钟的精品音乐节目本身就是“大量的工作”。到了11月份的第一次试镜时,我几乎做好了准备,但我从来没有感到完全舒服过。有一些棘手的段落我会害怕,和弦中间的音符我会虚张声势,希望没有人注意到。但在紧张发作的间隙,当我设法让音符闪闪发光时,当我的头脑、手和耳朵都同步时,我感到一种兴奋,一种和谐的感觉。我会做练习和试镜,这一点从未怀疑过,但我仍然不确定我的目标是什么。最终我承认,即使我去了皇家北方大学,我也几乎无法想象我会以单人生涯告终。但我也不够想要独唱生涯。每一步都感觉很艰难。我太累了。有时钢琴琴键本身似乎对着我转,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