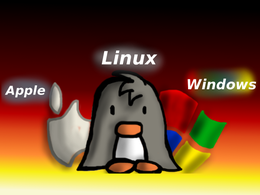软件工程师控制论指南
在“网络”成为所有互联网和计算机的前缀之前,它是数学家征服世界的方式。
我第一次接触到控制论这个词是在读本杰明·彼得斯(Benjamin Peters)关于苏联试图发明互联网的书“如何不让一个国家联网”(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时(麻省理工学院没有拼写Nyetwork,还是有点失望,拜托!)。当时,我对它的反应是“恶心”--任何以Cyber为前缀的东西--感觉既俗气又过时--紧随其后的是困惑。日期似乎是不可能的。控制论实际上比互联网和计算机业的兴起早了几十年?这可能是对的吗?网络这个词有没有可能有另一个意思,与完全丢失的虚拟体验无关?
在二战之前,控制论这个词偶尔被数学家用来表示政府在社会中的动态。认为社会有一套数学规则来支配它,就像物理对象有物理定律一样,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赞赏。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这一点。双方都使用技术来协调部署,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纳粹利用IBM的制表机犯下了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种族灭绝罪行。英国人用它来破解据信是无法破解的密码。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短时间内利用它大规模生产武器(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追踪和围捕日裔美国人)。这种技术的积累表明,国家和它们的经济可以被集中起来,引导到极端的目的。
亲眼目睹了这种动员的数学家们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允许这种动员发生的原理是纯粹的人类结构还是自然界中发现的力量。看到动员回报的赌注的政客们开始怀疑,社会是否真的可以被设计出来。1948年,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与交流”中总结了他对这一主题的看法。
控制论这个词来自希腊语κυβερνήτης(kybernḗtēs),意思是飞行员、州长、掌舵的人。因此,控制论是对控制和自动化系统的研究。维纳认为,反馈环,而不是智力,是认知的基础,从神经科学到物理学,再到经济,任何形式的系统行为都可以被理解,并可能根据反馈环进行编程。控制论既不是关于计算机的,也不一定是关于政府的。被原子弹的后果吓坏了,维纳想把学术讨论的重点放在系统之间的通信上,他想要对通信本身有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在他对控制论的后续研究“人类对人类的利用”一书中,他写道: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的行为,或者任何智力中等的动物,如小猫。我叫了一声小猫,它抬起头来。我已经给它发送了一个信息,它的感官已经接收到了这个信息,并且它在行动中记录了这个信息。小猫饿了,发出一声可怜的哀号。这一次它是消息的发送者。小猫在摆动的线轴上拍打。线轴向左摆动,小猫用左爪抓住它。这一次,非常复杂的信息都是通过小猫自己的神经系统内通过关节、肌肉和肌腱中的某些神经末体发送和接收的;通过这些器官发出的神经信息,小猫知道自己组织的实际位置和张力。只有通过这些器官,任何像手工技能这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
最后一对可能是关于技术的控制论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尽管线轴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不会思考,但它通过接收输入(敲击)与小猫交流,并通过改变小猫的运动来做出回应。在控制论中,这也是交流。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一系列的反馈循环:有些是负面的,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强化的,有些是平衡的。控制论是关于这样的循环是否可以测量、量化和最终编程的学术研究。
这就是数学家们设计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简单地观察和记录它。
控制论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很快就枯竭了,但在此之前,一些羽翼未丰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关于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许多想法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模仿人脑通信路径的机器可能比目前的机器具有更高的智能。
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和沃尔特·皮特(Walter Pitt)开发了第一批神经网络计算模型,作为他们控制论研究的一部分。
克劳德·香农证明了电路可以解决布尔代数问题。今天,工作成为数字芯片的基础。
艾伦·图灵(Alan Turing)在控制论活动高峰期访问美国,标志着他对人工智能潜力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图灵决心充实他对大脑中神经元的理解,他投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最终出版了“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为细胞生长和图灵机器创造了革命性的模型。
J.C.R.Licklider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通过维纳的每周晚宴接触到控制论,他将以人机接口专家的身份加入SAGE项目。那些对计算机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从另一个上下文中认出了Licklider的名字:他最终被国防部聘用,成立了他们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该办公室将开发ARPAnet……。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互联网。
维纳和冯·诺伊曼的友敌地位堪称传奇。曾经的合作者,他们会断断续续地促进和破坏彼此的工作和声誉。维纳会出现在冯·诺伊曼的谈话现场,大声地打鼾。冯·诺伊曼会坐在维纳演讲的前排,装模作样地翻阅当天的“纽约时报”,而不是听。
其根源在于重大的政治分歧。虽然二战把这么多伟大的数学家带到了同一个研究机构和专业关系网络中,但从那段时间应该学到什么的问题确保了合作不会持续下去。冯·诺伊曼非常反苏联,支持发展更先进的核武器,以威慑战争。维纳对此感到震惊,对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深感悲观,对社会主义事业深表同情。他鼓励那些试图在宏大的社会工程规模上实施他的想法的苏联控制论者。这促使控制论落入宣传之手,助长了未来主义,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其创始学者之间的个性冲突正在减缓其在学术界的势头。维纳嫁给了一个毫无歉意的纳粹分子,这一事实也无济于事。
维纳的书很受欢迎,控制论的跨学科性质意味着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都开始使用它的语言。苏珊·尤辛(Susanne Ussing)阅读了“人类对人类的利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并创造了一系列被称为网络空间的感官艺术体验。1966年,医生称他们的新款半人半机器怪兽为赛伯人。“华尔街日报”讨论了“网络加速器”。智利政府为他们的计划经济建造了一个高科技的计算机化指挥中心,他们称之为Cybersyn。在没有学术界支持的情况下,控制论进入了时髦的领域,任何想要引用未来乌托邦模糊概念的人都会提到控制论。对未来的许多设想都涉及到计算机或机器人技术,控制论周围的许多早期人物对计算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事实帮助有效地抹去了控制论在政治上不具吸引力的过去。
当我创造“网络空间”这个词的时候,我所知道的就是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效的流行语。它似乎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它暗示了一些东西,但没有真正的语义意义,即使对我来说,当我看到它出现在书页上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到互联网开始进入消费社会时,20世纪60年代的网络未来主义是复古和怀旧的。它似乎符合早期黑客的个性:有点深奥,有点反文化,带有理想主义的社区倾向(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话)。事实上,它还与计算机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它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数字世界的完美俚语。
即使没有人格冲突,控制论也努力发展出一套坚定而完全归因于追求控制论的著作。相反,它是一个领域的专家探索其他领域的桥梁。当一项重大进展发表时,它成为了一个主办领域的子学科的开创性工作,而不是推进控制论本身的关键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控制论的贡献被剥离,被重新归类为其他东西。早期关于认知反馈回路的工作变成了人工智能。反馈回路形式的模型成为信息论。围绕生产的反馈循环的工作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关于复杂系统的数学表示的工作变成了系统动力学。对行为反馈循环的研究转向社会学和心理学。控制论理论实际上奠定了人类学和认知科学的基础。最近在人机交互方面的工作可以被视为追溯了维纳关于控制论分支的许多原始哲学辩论。
作为一种关于技术和框架的哲学,用来思考复杂系统的控制论可能值得从知识垃圾桶里拉出来。自动化系统正在各地扎根。官僚机构的数字化要求政策制定者从起草法律转向设计控制系统。虽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控制论者只能以假设的方式真正写下反馈循环,并推测其影响,但现代软件工程师的日常生活却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