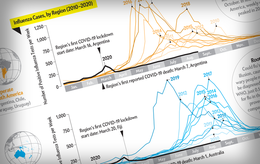1957年的亚洲流感流行是抗生素历史的转折点
五十周年纪念是回顾抗生素时代的首例流感大流行的合适时机,该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1957年2月在中国发现的“亚洲流感”于当年秋天到达英国,在那里直接或间接杀死了16,000多人,可能多达40,000人。
比流感本身更危险的是继发感染,这种感染有时会导致致命的肺炎,并使医生面对细菌的证据表明细菌对迄今胜利的青霉素的抵抗力正在增强。即使全世界都在庆祝这种新奇药物和其他类似药物的神奇发现和深远影响,它们的使用方式也可以通过鼓励抗性生物体的繁殖来抵消其影响。
在现代人看来,“抗生素时代”一词听起来有些陈旧,但半个世纪前,它表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的一些革命性希望。彼得·范西塔尔(Peter Vansittart)后来在其自传《五十年代》(1995年)中回忆起,连同法西斯主义,大规模失业和(不久)殖民主义,细菌的威胁似乎已被消除。对传染病的恐惧已成为过去。 14世纪和17世纪的瘟疫流行,19世纪霍乱的爆发,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流感流行,都是英国“岛上的故事”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开创性的医学社会学家报告说,传染病的经验显然已被取代。当时的一本主要教科书,麦克法兰·伯内特(Macfarlane Burnet)的《自然传染病史》(第二版,1953年)庆祝了“虚拟消灭传染病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些态度在医生的手术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虫很容易用抗生素治疗,肺炎可以在几天之内治愈,甚至可以治愈结核病。
抗生素被认为是终结感染带来的风险的主要因素。第一种青霉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引入的。其次是抗结核药物链霉素,然后是四环素药物“黄金大军”中的许多强大而广泛有效的成员。在1950年代,很快就发现了其他重要的抗生素家族。可以说,这一新技术被赋予了太多的重要性。至少在较富裕的国家,诸如住房和营养状况改善等社会因素是造成结核病等疾病威胁长期下降的原因。但是,抗生素可以通过减少感染的危险和确保治疗的确定性来补充这些因素。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信心似乎变得轻而易举。 1980年代目睹了艾滋病的恐怖袭击,随后是“食肉病毒”,克雅氏病,非典和禽流感。对抗生素治疗有抗药性的细菌进入了感染医院和社区。对MRSA(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管理(最近的担忧)在2005年大选中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策制定者已公开讨论了“抗生素后时代”的影响。
从战后庆祝胜利到我们时代害怕失败的叙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可以与希腊的悲剧相提并论。的确,在这部最现代的戏剧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定义的“复杂悲剧”的特征-转折点(peripiteia)和主人公觉察到的时刻(诊断)-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特征。 1957年的流行病无疑可以成为转折点,而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岁月可谓是公众的关注点。
亚洲流感被证明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六分之一的英国人口具有高烧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关节酸痛。与1956年的所有罢工相比,十月份的病假损失的工作时间多于1956年的所有罢工。由于矿工的放倒,煤炭的产量下降了一百五十万吨。媒体报道说,这种感染正在使学校停滞不前,并使海军舰船瘫痪:在9月,由于北约组织的船员生病了,两艘船和两艘潜艇被撤职。根据10月8日的《泰晤士报》,伊顿州一半的男孩生病了。
尽管发生了短暂的高烧,但温度迅速升至39ºC(102ºF),症状通常较为轻微,通常证明阿司匹林,大量饮酒和卧床休息是有效的。英国医学协会不鼓励广告宣传,要求患者致电医生。每三周间隔两次注射的疫苗只能限量提供给医疗和福利工作人员等优先病例。女王在当年访问北美之前接受了培训。
对于该流行病的一部分受害者-占总数的一小部分,但实际人数却很大-该疾病远非轻而易举。在老年人,体弱者和非常年轻的人群中,其痛苦程度要高得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死于不是流感本身,而是死于最近对所有抗生素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80/81引起的细菌性肺炎。这种细菌可以产生一种酶,即青霉素酶,从而破坏了青霉素分子。这种细菌不仅具有强大的抗药性,而且对人类的攻击也具有毒性。
事实证明,葡萄球菌性肺炎对感染该病的患者有四分之一以上,通常是在住院流感后。其效果迅速:三天之内,受害者变成了蓝色,被窒息。在美国,到1950年代,儿童因肺炎死亡的人数急剧下降。现在的数字显示出短暂的高涨。对于那些希望看到的人,已经暴露了抗生素时代的脆弱性。
甚至在流感流行之前,葡萄球菌就可以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已经对抗生素的治疗能力构成了主要的细菌威胁。该品种于1884年被命名,代表其金色,类似于一串葡萄。尽管细菌具有吸引人的外观和诗意的名字,但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医院中的一种危险。确实,这是青霉菌对葡萄球菌的作用。这种文化使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意识到了霉菌的潜能,并最终导致了青霉素的分离和使用。
首先,斯塔夫。金黄色葡萄球菌几乎普遍对青霉素敏感。但是,这种细菌的抗药性菌株取代了那些比其他易感物种不能快得多的菌株–伦敦哈默史密斯医院的细菌学家在1948年注意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特征。在短短两年内,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人群已从主要对青霉素免疫的主要疾病转移到了青霉素。一种细菌的免疫菌株,特别是葡萄球菌。金黄色的80/81病毒在1950年代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医院。
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80/81不仅会在流感患者中引起肺炎,还会感染新生婴儿的皮肤。那时,医院里出生的婴儿被放在大拐杖里,与母亲分开,容易感染。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感染了皮肤,通常非常轻微,然后传染给了哺乳母亲的乳房。这个数字可能更高:南威尔士一家医院报告说,其新生儿中有六分之一患有某种皮肤感染或结膜炎。手术患者的伤口在需要经常更换的绷带的保护下也可能被感染。在1958年的一次美国会议上被告知,有5%至9%的清洁伤口会感染葡萄球菌。
“抗生素时代”在提供更多医学工具的同时,也给个人医生和全球医疗机构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1964年向英国医学协会致辞的瑞典医师不仅谈到了技术的成功,还谈到了远远超出医疗保健需求的需求。需求增长的结果是医生急诊或通过病床的病人流失率越来越高。可以迅速有效地使用抗生素,因为患者迅速开了开处方或使用药物来管理医院感染的手术。然而,管理不善的使用可能导致抗药性菌株的自然选择,从而使抗生素有时无效。
新闻界意识到了斯塔夫的威胁。 1958年1月的aureus 80/81。常设医疗咨询委员会的档案现在摆在国家档案馆中,里面充满了公务员当时汇编的新闻剪报。 1月12日,根据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的报告,《星期日快报》特别强调了病房的关闭。第二天,《每日邮报》和《每日电讯报》都处理了葡萄球菌的威胁,而《每日先驱报》则谈到了“神秘菌X”。 1月21日,常设医疗咨询委员会发出了更为清醒但主题相同的警告,警告说耐药细菌的危险传播。
这些细菌显然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 1958年10月,美国外科医生在一次公共卫生会议上说:“这里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在这个民族问题上的利害攸关之举。”他还承认,英国科学家在识别和处理这一威胁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伦敦北部科林代尔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已经开发出一种广泛使用的细菌识别技术。科林代尔的链球菌,葡萄球菌和空气卫生实验室的主任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是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国际分析师网络的中心。
分析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抗生素时代,清洁标准已经允许。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1963年,英国皇家卫生学会组织了一次名为“医院感染的预防”的会议。皇家利物浦儿童医院的护理老师D. Sissons女士建议护士
不应该害怕去看房员说,‘那半挂着的面具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穿上剧院的衣服走到门诊去?医生是不育的,护士不是吗?’人们会说它们是老龙,但是她自己为成为一体而感到自豪。是否每个人都不清楚,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专业人士,他们手中都有患者的生命,应该恢复严格的纪律吗?绝对的权力应该授予护士长或医疗主管,而不是非专业人员。
由于病床从未冷却,病房从未得到适当的清洁,病房的感染率上升了,一年中爆发的时间达到了三倍–感染范围很广,必须关闭该地方。 ..现在,医院由少校军士组成,很少有领导人,他们应该回到真正与病房感染问题密切相关的人们那里。
但是,如果1957年的流感危机向公共卫生专家发出了明确的警告,那就是抗生素本身无法预防广泛的感染,那么公众仍然不会意识到转折点已经到来。四十年后,美国媒体对技术评估办公室进行了一项研究,突显了公众在1950年代对抗生素的持续信念。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威胁。 Aureus 80/81激起了专业人士的不安,新闻界的普遍报道既没有政治色彩,也没有激怒色彩,呈现出强力和抵抗性的葡萄球菌病的流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职业挑战。如果要使用领先的抗生素化学家约翰·希汉(John Sheehan)的话,如果细菌可能是“狡猾的”,化学家也可以。
巧合的是,正当1957年流感大流行开始之时,在比查姆公司工作的化学家们发现了如何酿造青霉素的“大桶”,他们可以在青霉素上附着分支来生产新型抗生素。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从科学技术突破到了医学突破,1960年Beecham推出了甲氧西林,其结构使其对Staph产生的破坏性酶免疫。金黄色80/81。甲氧西林似乎证明化学家可以胜过细菌。
新药的好处是巨大的。当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在埃及艳后的电影中染上葡萄球菌性肺炎时,甲氧西林救了她。尽管如此,葡萄球菌的衰败。金黄色葡萄球菌80/81的威胁并不完全是由于单一药物的部署;无论如何它也许正在消失。此外,从该药物投放市场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在Roehampton玛丽皇后儿童医院的一名感染儿童死亡后,MRSA(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危险变得非常明显。
1962年MRSA的死亡,恰逢新的权威质疑问世,这将对控制抗生素的使用产生具有讽刺意味的后果。同年,英国医生莫里斯·帕普沃思(Maurice Pappworth)发出警告,称公众在医学实验中将其用作不知情的“人类豚鼠”,而由沙利度胺引起的胎儿异常的丑闻已广为流传。新的焦虑症刺激了患者协会的成立,并有早期迹象表明公众越来越怀疑医学界乃至制药公司的善意。
然而,这种越来越多的怀疑并没有抑制对药物和医疗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似乎使医生对抵制他们认为患者接受手术的期望更加谨慎-抗生素处方正在淘汰中。无论患者实际想要什么(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许多医生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开抗生素处方来赢得信任。
MRSA和其他威胁细菌,例如抗药性肺炎球菌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广泛传播。在随后的几年中,人们已经忘记了早年的焦虑,但是对技术战胜细菌力量的信心也下降了。在对基因组学和机器人寻找新的和有效的药物的承诺产生了短暂的,常常是毫无回报的热情之后,与半个世纪前相比,新抗生素的开发吸引了制药公司的投入较少。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确实看到了对过度使用抗生素的强烈不安,更加重视对抗生素使用的管理。探索了医生与患者之间新的协作形式,患者自己可以共同决定是否以及如何用药。改变当代经验的这种尝试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叙事之中,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了工程化。在反思1957年的经历和Staph的威胁时。 aureus 80/81我们经历了抗生素故事的转折点,这是现代标志性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