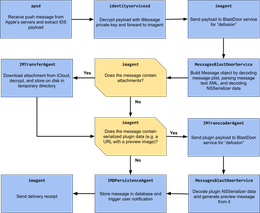一种新颖的努力,看看贫困如何影响年轻的大脑
大流行救济方案中的新月支付有可能将数百万美国儿童带出贫困。一些科学家认为,通过他们的大脑更加根本地改变儿童的生活。
建立贫困与教育成就,健康和就业的差异越来越熟悉。但神经科学的新兴分支询问贫困如何影响发展大脑。
在过去的15年里,数十名研究发现,与来自更高手段的家庭的儿童相比,在微薄情况下提出的儿童具有微妙的大脑差异。平均而言,大脑外层的细胞层的表面积较小,特别是在与语言和脉冲控制有关的区域中,这是称为海马的结构的体积,这负责学习和记忆。
研究表明,这些差异不会反映遗传或天生的特征,而是儿童长大的情况。研究人员推测,贫困的具体方面 - 子公司营养,升高的压力水平,低质量的教育 - 可能会影响大脑和认知发展。但几乎所有迄今为止的工作都是相关的。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在不同家庭的各种程度上,但贫困是他们的共同根。一个持续的研究称为宝宝的第一年,于2018年开始,旨在确定减少贫困本身是否可以促进健康的脑发展。
“我们都没有人认为收入是唯一答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和儿科医生博士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他共同领导工作。 “但是对于婴儿的第一年来,我们正在继续相关的相关性以测试减少贫困是否直接导致儿童认知,情感和大脑发展的变化。”
诺布尔和她的合作者博士正在检查给予贫困家庭现金支付的效果是否与拜登行政当局相比,将作为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的一部分分配。
研究人员随机分配了1000名母亲,曾在纽约市,新奥尔良,双城市和奥马哈一起居住在贫困中,每月举行借记卡20美元或333美元,以至于家庭可以在他们所希望的时候使用。 (拜登计划将每月300美元,6至17岁的儿童每月为250美元。)研究在几年内使用名为Mobile EEG的非侵入工具来培训脑波模式的非侵入工具使用20个电极的可穿戴帽。
该研究还追踪母亲的金融和就业状况,孕妇健康措施,如压力激素水平和儿童保育。在定性访谈中,研究人员探讨了金钱如何影响家庭,以及母亲的同意,他们遵循他们如何花钱。
该研究旨在从家庭访问中1岁及3岁的儿童收集大脑活动数据,研究人员在大流行击中之前,研究人员在大约三分之二的儿童中获得了第一套数据。由于家庭访问仍然无法维持,他们将研究扩展到4岁,并将在明年收集第二组大脑数据而不是今年。
大流行,以及大多数美国人在过去一年获得的两次刺激支付,无疑是以不同方式影响参与家庭,正如今年的刺激检查和新的每月付款都一样。但由于该研究随机化,研究人员仍然希望能够评估现金礼物的影响,诺布尔博士说。
宝宝的第一年被视为通过随机试验证明的大胆努力,这是减贫与大脑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绝对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家和研究贫困和社会中心主任的认知神经科学家Martha Farah表示具有直接政策影响的第一个,如果不是第一个”的研究。大脑。
然而,法拉教授承认,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经常折扣大脑数据的相关性。 “带来神经科学忍受的是,我们是否会得到可操作的见解,或者是人们只是被漂亮的脑形象下雪,而且来自神经科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她说。
怀疑论者比比皆是。詹姆斯·赫克曼,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获奖经济学家研究了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他说“即使是一个暗示一个政策会出现的政策,除了说,是的,是的,有一个印记更好的经济生活。“
他说:“仍然是一个问题,即父母现金通过它有助于儿童的大脑,他说,加入这一机制直接可能既便宜,更有效。
在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的儿童津贴提案上工作的贫困和福利政策主任Samuel Hammond,同意跟踪任何观察到的认知福利的来源是棘手的。 “我难以解开实际帮助的干预措施,”他说。例如,政策专家辩论某些育儿方案是否直接使儿童的大脑受益或只是释放她的照顾者获得工作并提高家庭的收入。
然而,这正是为什么利用现金提供弱势家庭的原因,诺布尔博士说,贵族们可能是测试脑发展联系的最有效方法。 “对于孩子们的成果的特定途径有可能不同于家庭,”她说。 “因此,通过赋予家庭能够使用金钱,因为他们认为合适,它不会预先假定一个带来儿童发展差异的特定途径或机制。”
神经科学有一种转变社会思维和影响政策的轨道记录。研究表明,大脑在过去的青春期并进入一个人的20世纪20年代,重塑了与少年司法有关的政策。
在另一个例子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罗马尼亚孤儿院的儿童的脑和认知发展研究改变了制度化和寄养的政策,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儿童的神经科学家查尔斯·尼尔森表示经医院联合领导那项工作。
这些研究表明,剥夺和忽视症智人和妨碍留在2岁以上的儿童的心理发展,并且制度化深刻地影响大脑发育,抑制电力活动和降低脑大小。
但这工作也强调了研究的消费者如何,他们之间的决策者,易于给予大脑数据的重量,而不是其他研究,就像其他研究表明一样。当纳尔逊教授向政府或发展机构官员展示了这些调查结果时,“我认为他们发现它是实施政策变革的最强烈的弹药,”他说。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视觉,比我们说,嗯,他们有较低的智商,或者他们的附件并不强烈。” (他是婴儿第一年的顾问。)
诺布尔博士说,这种数据的生动不一定不好。 “如果我们发现差异,大脑数据使这些差异对利益相关者更加引人注目,那么这对包括的重要性是重要的,”她说。此外,脑数据在自己的权利中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在婴儿和幼儿中,她说的是认知的行为测试通常是不准确的或不可能进行的。她说,脑差异也倾向于可检测到比行为的差异。
法拉教授说,该领域可能只是太年轻,无法将其对政策的贡献。 但是,越来越多地了解特定脑电如何受到贫困的影响,以及衡量这种电路的更好工具,可能会产生基于科学的干预措施,她说。 与此同时,宝宝的第一年希望解决在政策层面已经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对父母的现金援助是否有助于他们的孩子的大脑以帮助他们一生的方式发展。 Alla Katsnelson是北南普顿的科学记者。您可以在@lalakat的推特上跟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