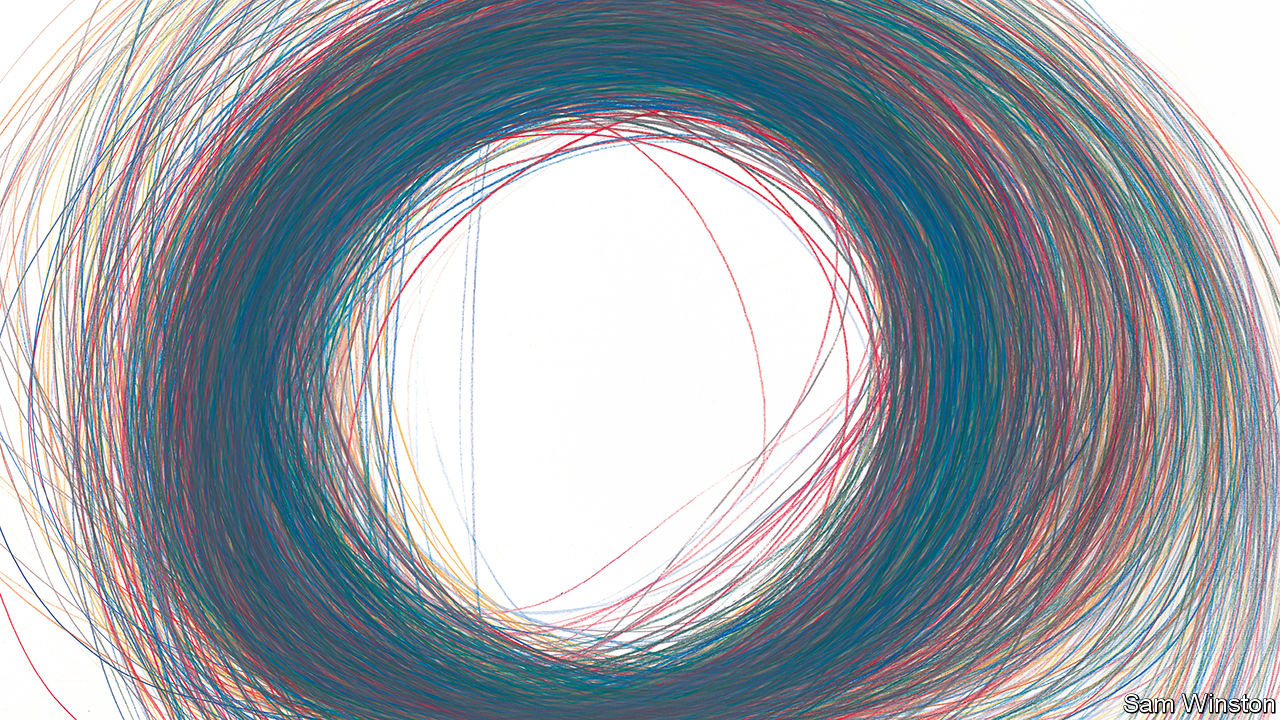我们能摆脱信息过载吗?
2016年12月的一天,37岁的英国艺术家萨姆·温斯顿(Sam Winston)带上了一把梯子、一把剪刀、几卷遮光布和大量的胶带,开始着手一个他考虑了一段时间的项目。温斯顿身材瘦小,留着胡子,有一双灰蓝色的大眼睛,20世纪90年代末从德文郡搬到了伦敦。他通过教书,为杂志做插图,向收藏家和博物馆出售更大、更自由的艺术品,其中许多是铅笔画来养活自己,直到20多岁和30多岁。他刚刚与作家奥利弗·杰弗斯(Oliver Jeffers)合作出版了一本儿童书籍,并为推动“图书之子”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他很感激商业上的成功,但温斯顿发现他不喜欢公司出版。所有的电子邮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铅污迹斑斑的理想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隐士。他从小就受到神经质和压力的困扰,是一个间歇性失眠症患者,很难过滤公共场所的噪音和干扰,而且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他越来越依赖手机和电脑。所以温斯顿决定躲几天。没有屏幕。没有太阳。没有任何形式的视觉刺激。他打算在黑暗中独处一段时间。
他花了几个小时,在他的工作室里爬上爬下梯子,覆盖了每一个入射光线的光圈和针孔。这间工作室位于伦敦东部的一家由工厂改造而成的工厂里,拥有巨大的公寓窗户和镶嵌着天窗的倾斜屋顶,这些天窗特别难密封。根据温斯顿的保守估计,他用了200米长的管道胶带,直到他完全满意这里终于是一片黑暗。他会坐在里面,用铅笔和纸画画,做瑜伽,吃点零食,等着看黑暗是否有任何缓解作用。
21世纪的世界并不比过去更富有质感或异国情调。闻起来差不多,没有新口味。自从工厂出现以来,飞机、家用电器和高速公路上的声音污染就没有出现过严重的上升。然而,我们眼前的信息溢出和分心,二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增长,没有任何停顿或停滞的迹象。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看到的信息和分心一直在不断增长,没有任何停顿或停滞的迹象。DM!突发新闻!收件箱(%1)!这是一个滚动的、无底的视觉时代,公交站和地铁站台的弧形墙壁播放视频广告,奶奶的脸游到智能手机上打招呼。人们在排队时观看奥斯卡提名的电影,他们的设备与腰部齐高。Netflix的高管可以半认真地打趣说,他觊觎我们的睡眠时间(目前我们没有流媒体Netflix节目的时间)。苹果在我们的手腕上多装了一个屏幕,谷歌则暗暗地希望我们最终会在眼镜里佩戴屏幕。大新闻不超过140个字符,最好是一张令人震惊的图片或一段视频,否则就不会被注册为大新闻。
我们的大脑倾向于依赖视觉,严重优先考虑视觉而不是其他四种感官。自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爬上两只脚,把鼻子带到离芳香四溢的大草原地面更远的地方,我们就被连线连接到看到生物,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通常通过我们的窥视者来体验这个世界的下一步是什么。作为一名艺术家,萨姆·温斯顿(Sam Winston)经常留意颠倒的项目-奇怪的、侧面的方式,让他摆脱熟悉的习惯,或者推动他的作品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他想知道,如果他暂时躲避眼球闪电战,他和他的工作会发生什么。
现在,在他昏暗的工作室里工作和睡觉时,他开始注意到新的东西。没有阳光的指引,一天的节奏是通过他以前只模糊意识到的听觉线索来的:伦敦空中交通连夜停止,或者是车辆在高峰时间从红绿灯下移动所需的时间稍长一些而发出的空转声音。在高峰期,这一天的节奏来自于他以前只模糊意识到的听觉线索:伦敦的空中交通连夜停止,或者在高峰时间里车辆空转的声音。当他在他的茶站用死记硬背的动作冲泡几杯rooibos时,他注意到当他倒冷热液体时,他能听到它们的区别。他开始意识到,他后来告诉我,“我们的感官是多么聪明。以及我们是如何在海啸中淹死他们的。“。
温斯顿发现,他在黑暗中也很有成效,他一直画到铅笔变成块头,并创作了一系列巨大的素描-在一些地方画得很宽,或者用他古怪的笔迹挤满了重叠的句子-这些素描后来成为伦敦南岸中心(Southbank Centre)展览的一部分。在画锯齿图的间隙,他做了生动的白日梦,甚至出现了幻觉,“就像我的大脑是一个数字收音机,一直在寻找可用的频道”。
温斯顿的哥哥在前一年突然去世了,丧亲之痛是促使他躲在黑暗中的另一个原因。他本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来深刻地思考爱与失,感恩他的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也是他的朋友。
到2017年和2018年,他制定了计划。他用谷歌搜索零星的研究资料。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了一项关于感觉剥夺的开创性实验,在此期间,数百人被要求独自呆在一个密封的黑房间里,尽可能长时间地忍受。大约三分之一的受试者在几天内戒烟。他们至多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温斯顿想,如果他再一次陷入黑暗,他能撑得住一个月吗?他又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些,然后去网上购物,订购了更多的遮光布,更多的胶带。
信息超载是美国社会科学家伯特伦·格罗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个术语。1970年,一位名叫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作家,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可靠的未来主义者--一个预言未来生活的人--将信息过载的想法作为一系列关于人类最终对技术的悲观预测的一部分而流行起来。(说得好,艾尔文。)。另一组学者在1977年的一项研究中写道,信息过载可能发生在人或机器身上,“当系统的输入量超过其处理能力时”。然后出现了录像机、家用电脑、互联网、移动电话、带互联网的手机--以及我们可能即将达到能力极限的焦虑浪潮。
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美国人每天接收的信息量是25年前的五倍-这是在大多数人购买智能手机之前。2019年,德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学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正在缩短,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入侵,但它同时表现为“线上和线下”。
到那时,一家名为信息过载研究小组(Information Overload Research Group)的组织已经做了一项研究,估计每年有数千亿美元因数据过载而以杂项生产力成本的形式从美国经济中流失。该集团于2007年由计算机工程师出身的顾问内森·泽尔德斯(Nathan Zeldes)共同创立,他曾被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Intel)要求减轻员工的电子邮件负担。到2019年底,泽尔德斯已经准备好发出失败的信号。他在一篇博客中写道,“我很愿意给你一种神奇的药水,让你的注意力恢复到你祖父母的水平,但我做不到。在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十多年后,这种伤害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他建议人们培养一种爱好。
在一个负荷过重的时代,人们可能会觉得技术似乎相当幸运。推得太深,太深,太深了。甚至在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之前,部分文化就已经开始将与世隔绝和剥夺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的象征,这是今年的热门话题,就好像独处和没有设备的一段时间是新一季的服装,下一个克罗纳特,另一个书呆子。
在一场大流行限制了在别人温水中打滚的吸引力之前,伦敦各地的浮罐中心都在开放。在捷克共和国,有一些水疗中心每周在黑暗中向客户出售百叶窗、服务式套房。2020年3月,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面无表情地在推特上写道:“社交距离被低估了。”这是一个令人晕眩的笑话,但这个笑话会让硅谷的科技兄弟们知道,对他们来说,休养生息是一种选择。
最近,我看到旧金山一位名叫席琳的人在推特上向她的2500多名追随者表示,“在为期一周的冥想静修、塔霍周末和长达一个月的远程工作会议之间,尝试与科幻男孩约会是多么困难……”大约有4000人点击支持这一观点,将席琳推上了数量呈指数级的陌生人的屏幕,包括我自己的屏幕。任何新推文的默认声音都是口哨声,介于邻里间友好的“哟-呼”声和遛狗者的呼唤声之间。
英国心理学家希尔达·伯克(Hilda Burke)曾写过一篇关于智能手机成瘾的文章,她告诉我,在这个超负荷的时代,部分问题在于每一封新信息都会吸引我们的注意,这种执着就是Yoo-hooing的坚持。扬声器叮当作响。像素化的柱子紧急地洗牌,或者图标弹跳,似乎是在发出信号,表明这里是火灾发生的地方。我们对紧急情况的抽搐反应是在恶意的情况下触发的。
在一个空闲的周五,当席琳的推文在我的手机上吹着口哨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觉得读起来有点压力。是不是因为它让我觉得自己老了?我已经有足够多要考虑的事情了吗?最终我意识到,对我来说,每一条推特都有一点压力。伯克说,每一次琐碎的、吹着口哨的更新都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只披着狼皮的绵羊。”身体突然引起注意,准备奔跑或战斗,而这一切都是不值得的。这令人困惑。“。
在萨姆·温斯顿的案例中,顿悟的时刻到来了,当时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享受一夜外出后的宿醉。他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他并不觉得“成为Twitter、Instagram、Facebook的目标,所有这些带有算法的服务都是故意设计成尽可能性感、多汁、让人分心的,尽可能频繁地触发我的突触。”这是什么老生常谈?‘保护我不受我想要的东西的伤害。’“。他意识到,他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想在游轮上呆一个月:“体验一下明确的停靠。”
2018年夏天,温斯顿在黑暗中为他计划的一个月争取到了一个地点。一位熟人同意把湖区的一间一室宾馆借给他,只是要求一旦房子用布和胶带彻底封锁,温斯顿就签署一份弃权书,承担任何灾难的责任。他买了橱柜、冷冻馅饼和世界末日供应的瓶装水。他安排了一群值得信任的人打电话来,偶尔拜访一下,以确认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他不会把诺曼·贝茨(Norman Bates)全部带到那里”。
温斯顿决定再定几条基本规则。他会做四周的工作,10月初的周一入狱,年底的周日出院。这相当于672小时的与世隔绝。他会在录音机上做语音记录,并在一系列铅笔画中记录较少的字面印象。
为了与这项努力的特立独行精神保持一致,他没有深入研究健康风险。他读了一些关于褪黑激素和血清素的书,这两种激素是由豌豆大小的松果腺在大脑中产生的,有助于身体调节睡眠-觉醒周期。温斯顿认为,他最终会相当缺乏血清素,血清素通常在白天分泌,帮助我们保持警觉,但他会得到绝对丰富的褪黑素,一种安眠药。他没有咨询医生,尽管他确实在一次例行预约期间询问了Specsavers的一名员工。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温斯顿忍不住发了最后一条推文,然后把自己锁起来:“没有接待。没有屏幕时间。在黑暗中作画。11月见。“。九月的最后一天,他在庄园周围的田野里夕阳西下散步,凝视着山丘和奶牛,总的来说,他试图享受这最后一次传统的眼球使用。然后他走进室内,上床睡觉,在接下来的28天里熄灭了灯。
他可以应付漆黑的早晨,因为他以前尝试过这个实验的一个较短的版本。因此,当温斯顿醒来,克服了短暂的恐慌--不,他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失明--就很容易又愉快地重新进入了昏昏沉沉的第二次睡眠。当他真的下了床,摸索着走向小厨房和冰箱时,早餐的准备和食用时间比往常要长。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定的时间延误。甚至在最初的几天里,他都以为自己起床了,正在做一些早上的活动,在他的工作台上画画,或者在地毯上做瑜伽伸展运动,结果却接到了女朋友的报到电话,女朋友告诉他,他落后了几个小时。由于没有精确的时间感,他又一次屈服于某种东西的模糊、平静的节奏--比如早晨,比如下午,比如傍晚,比如夜晚。
乡村宾馆比城市工作室安静多了。温斯顿的耳朵不得不收听更遥远的听觉线索。不久,他意识到他可以从半英里外一条A路上的交通噪音密度来区分白天和黑夜。他经历了他以前经历过的其他过渡阶段,比如当他的心灵清理花絮和饼干时,新闻和时事奇怪地突出起来,正如温斯顿在第五天的录音机笔记中所说的那样,“积累的歌曲,小小的思想漩涡,万花筒般的东西”。一天后,他又录下了另一条笔记:“我发现无论你在黑暗中走哪条路,前进还是倒退,都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怎样,你什么都看不见。挺好的,倒着走。“
由于他的视力受到抑制,他的其他四种感官都有机会站出来展示自己的作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失明的人可能会体验到其他感官上的收获。随着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脑扫描技术的进步,学者们开始用实证研究来检验我们对轶事的理解。他们的发现表明,非视觉感觉增强在黑暗中发生得很快。即使在灯光熄灭30或45分钟后,我们的指尖也会随着更大的反应而兴奋,我们似乎在确定声音传播方向方面变得明显更好。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进行中,这让专门研究感官的科学家们兴奋不已,因为这表明大脑的适应能力更强--用他们的术语来说,更“可塑性”--比之前认为的更“可塑性”。
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系的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把大脑可塑性说得像个地产大亨。“当身体陷入黑暗时”,他告诉我,“大脑的这个巨大的视觉部分不再做它通常做的事情。”这是大量闲置的房地产,你会发现,房地产被重新装备或重新利用的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其他感官只是简单地接管它。根据一些研究,非视觉感官可以如此迅速地占用大脑空间,根据一些研究,这让斯宾塞等专家感到兴奋,因为这表明我们正在使用潜在的联系,而不是培养新的联系,而新的联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形成。通过关灯,换句话说,我们不一定是在增强其他感官,我们只是更倾向于注意这些其他感官已经在说的话。
当他在黑暗中进入第二个星期时,温斯顿花了很长时间用手指摸着普通的物体,东西的边缘,表面,他能辨别出的细微的纹理细节让他感到娱乐和分心。他一直在黑暗中作画。现在,每当他拿起一支铅笔时,他确信他可以从铅笔在纸上的振动和“它的声学,它在整个页面上的能量”来直觉地判断铅笔的密度。某些触觉体验伴随着令人兴奋的视觉印象。洗澡尤其令人兴奋--“阵雨就是奥尔顿大厦”--因为在温斯顿的脑海中,每一滴水似乎都会召唤出相应的一滴颜色。当他的女朋友从伦敦公交车上给他打电话时,他发现他喜欢背景中单调的噪音,通勤者的声音,嘟嘟声。“这就像是事后要想一整部电视迷你剧。”
他其他感官的提炼也导致了妥协和挫折。温斯顿在超市洗涤剂洗过的床单上再也睡不着了,因为他发现香味太浓了,让他作呕。他一直喜欢的食物变得不好吃了,特别是加工过的食物。和麦考伊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温斯顿确信,他现在可以追踪脆片中饱和脂肪进入食道的过程。有一天,由于消化不良的困扰,他的大脑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画面,他的肚子膨胀了。从那以后,他开始吃得更少了。锻炼,哭泣,减少手淫。当温斯顿用更丰富的感官意识刺痛时,这些基本的身体活动结束了,因为他发现它们太戏剧性、太奇怪、太多了。他是到黑暗中逃跑的,但这感觉不像是真的。
到第三周开始时,温斯顿被褪黑素浸透了,她在沙发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他陷入了回忆之中。白日做梦。产生了幻觉。他看到风景漂流而过,大部分是海岸线,波光粼粼的大海。他的幻觉可能是工作日的,他发现他的心灵渴望重新画出他周围的宾馆,那里刷着米色的墙壁,那里铺着瓷砖的小厨房…。然后,在经历了这样平淡无奇的事情之后,他会看到云雾缭绕的天空。一片星空。
如果静修对身体的影响是奇怪的(迷幻阵雨,对脆片的蛇形消化),那么与精神影响相比,这些都是山脚下的体验。之后,温斯顿会很难把这些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们会进行长时间的对话,试图描绘出他到底去了哪里,试图区分白天的幻觉和晚上的梦,有时还会求助于温斯顿在黑暗中记录的录音机笔记。
他对那些浮现出来的记忆的模糊性和广泛性感到惊讶,“这些来自过去的奇怪的小气泡‘爆’了。”和特朗普一样,出现在他身边的人-有时是幻觉,有时只觉得是幽灵-很少像他预期的那样。当温斯顿17岁的时候,他对他的第一个女孩有点无精打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