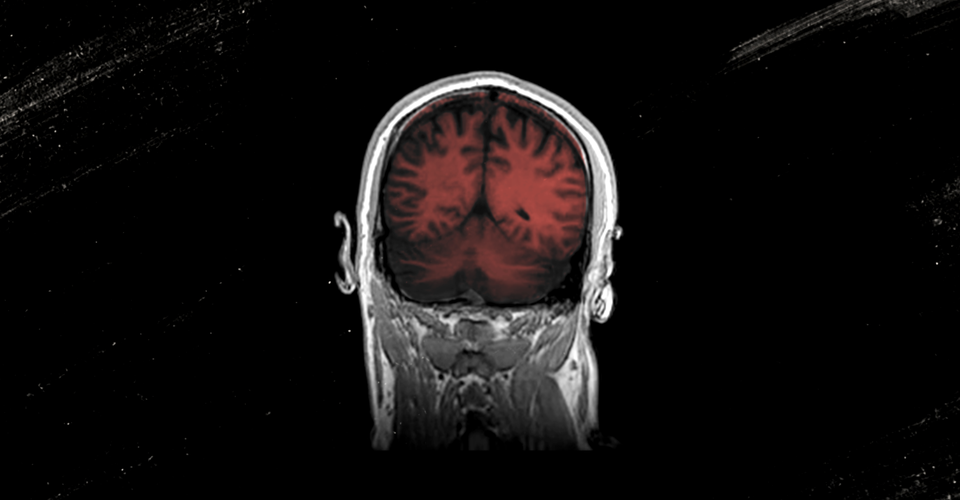“Covid-19是一个妄想症工厂”
35岁的冠状病毒幸存者利亚·布隆伯格(Leah Blomberg)不记得曾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病房,在那里她会在呼吸机上花18天的时间与生命作斗争。
布隆伯格告诉我:“我醒来时发现了一些我从未想象过的东西。”一名护士拿着锯子站在她的病床旁,砍掉了她的胳膊和腿。布隆伯格记得大喊救命。有一次,她试着摸她的脸,然后惊恐地意识到,她的头骨只有一半完好无损。
像布隆伯格这样的经历在ICU的患者中很常见。困扰最危重冠状病毒患者的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需要机械通气。使用呼吸机的患者中有80%患有被称为ICU精神错乱的迷幻状态,在此期间他们形成虚假的、往往令人恐惧的记忆。因为这些错觉记忆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刺激,它们比噩梦更生动--根据杰西·范德霍夫的说法,它们感觉“尽可能真实”。
范德胡夫因冠状病毒住院,并在ICU的呼吸机上呆了一周,他记得自己看到了自己的死亡。“我产生了幻觉,我会晕倒--真的很慢,”他告诉我。“我记得我特别有这样的想法,哦,我要死了,当我的脸撞到地上的时候,这会很痛的。”范德胡夫一度看到了自己的葬礼。“这真的很痛苦,”他说。“我记得在我的葬礼上见过我妈妈。”
许多ICU患者经历了与他们的死亡相关的妄想,通常以涉及酷刑或袭击的令人痛心的场景为特征。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ICU康复中心的心理学家吉姆·杰克逊告诉我,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在经历精神错乱的急性大脑功能障碍的同时,患者试图创造一种反映他们环境中非常真实的痛苦和压力的叙事。问题是,大脑会将现实转化为更可怕的东西。
杰克逊告诉我:“我们有精神错乱的病人,他们被带到医院的成像中心做核磁共振检查。”“当他们被推入核磁共振机时--非常恰当--他们确信自己正被移入烤箱,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核磁共振机与烤箱有些模糊的相似之处。”杰克逊在ICU康复诊所的工作中经常看到这种错觉。他还经常看到将涉及导管的手术误认为是性侵犯的患者。
“你不能告诉人们,‘这不是发生在你身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的肺部重症监护医生罗伯特·欧文斯(Robert Owens)告诉我。“这是他们记得的。所以它可能很难治疗。“。
虽然神志不清的神经科学原因尚不清楚,但它的发病很可能是由于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包括缺氧-大脑缺氧-以及镇静剂的使用。
研究大脑功能障碍和危重疾病的创伤内科医生梅尤尔·B·帕特尔(Mayur B.Patel)说,“(服用镇静剂的患者)温和、平静、平静的表情可能会被误认为睡着了,而实际上,他们的大脑着火了。”(Patel和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团队目前正在研究已故的ICU患者-包括那些死于冠状病毒的患者-以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大脑发生了什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乔·比恩弗努告诉我:“我们过去认为给病人服用镇静剂可以防止长期的创伤后现象。”“但事实证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情况似乎正好相反。”
最近重症监护的趋势是尽可能减少镇静剂。医生尽量避免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这类镇静剂被认为是特别容易使人神志不清的。但普遍存在的药物短缺使这一点变得不可能。最重要的是,许多冠状病毒患者需要长时间的通气,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镇静,而且往往更重。
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中心(Vanderbilt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肺部和危重护理教授韦斯·伊利(Wes Ely)表示,大流行迫使医生放弃了几乎所有可以减少神志不清的循证干预措施。因此,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ICU精神错乱的患病率急剧上升。
与伊利一起工作的杰克逊说,他特别担心在有冠状病毒患者的重症监护室里缺乏家庭探视。多项研究表明,陪护家庭成员通过提供舒适和将患者与现实捆绑在一起,显著减少了精神错乱。
杰克逊告诉我:“通常情况下,家庭成员会帮助这些患者了解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他们可以说,‘亲爱的,相信我,你实际上并没有被放进烤箱。我和你一起去了核磁共振中心。我一直在那里,确保你没有出事。‘“。
一些医院用来减轻精神错乱持久影响的另一个策略是ICU日记。家庭成员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撰写了一本个人日记,详细介绍了患者在医院的每一天。在病人出院后,记录帮助他们重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杰克逊说:“现在所有这些叙述都被扔出了窗外。”
家属探视的缺席,加上已经不堪重负的医务人员,以及延长镇静剂的使用,让许多医生担心ICU逗留对冠状病毒幸存者的长期后果。敲响警钟,声音最大的是伊利。
“如果你必须设计一个实验,让精神错乱变得尽可能严重,那么COVID就是它,”他告诉我。“COVID本质上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工厂。”
他有理由担心。精神错乱是ICU幸存者认知、身体和心理不良后果的强烈预测因子。ICU患者出院后可能经历的这一系列问题,称为重症监护综合征(PICS),影响到高达33%的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和50%在ICU停留至少一周的患者。四分之一的ARDS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比率与从战斗中归来的士兵相似。最终,精神健康症状和认知问题的结合阻止了许多ARDS幸存者重返工作岗位: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近一半的参与者在出院一年后无法重返之前的工作岗位。
“这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存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伊利说。
杰克逊认为,他的新冠状病毒患者的心理状况可能比其他ARDS幸存者更糟糕。他告诉我:“害怕死亡的动力,现在在COVID时代,害怕孤独死亡-我们认为,这导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现在布隆伯格出院了,她明白护士并没有真的想要杀她。但是这些知识并不会让记忆感觉更真实。除了与极度的肌肉无力作斗争外,布隆伯格还存在睡眠问题。“我很害怕,”她说,“在我看到那么可怕的事情之后。”
另一位冠状病毒幸存者菲奥娜·洛温斯坦(Fiona Lowenstein)告诉我,她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出院后将经历的心理痛苦的冲击。她说:“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的朋友、家人和我为康复而接受的采访都在公开庆祝我。”“但我觉得我有一个肮脏的小秘密,那就是我一点都不舒服。”
布列塔尼·洛尼斯(Brittany Lohnes)在2016年从ARDS中幸存下来,她也感受到了内部庆祝和痛苦之间的不和谐。“每个人都在说,‘你真是个奇迹。你活了下来。完全没有心理健康方面的跟进,“她告诉我。洛内斯与闪回、焦虑发作和严重的抑郁症作了一年的斗争,直到她决定找一位创伤治疗师。“老实说,对情感方面没有任何形式的善后照顾是最困难的部分,”她说。
许多ARDS幸存者告诉我,当冠状病毒患者出院时,他们感到深深的不安。阿曼达·格鲁(Amanda Growth)记得她在出院九个月后突然出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是如何让她措手不及的。“他们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以为我已经熬过去了,”她告诉我。首先是被插管的闪回-当两名护士按住她的手臂插入呼吸管时的挣扎。“如果你考虑这样的程序,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那都会被认为是酷刑,”Growth说。然后噩梦就来了。她说:“我一直在做噩梦,我一直在努力想要醒来。”“我刚刚到了一个我希望自己死在医院的地步。”
格鲁能够为她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寻求帮助。但她的康复需要一个漫长的接受过程。Growth说:“我们有一种看法,认为人们生病了,然后就会恢复过来,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你生命中的这一章会发生,在那之后的每一章都会改变。我担心(冠状病毒)幸存者会经历某种程度上的悲痛,不得不经历他们的生活已经改变的现实。“。
和Growth一样,在一场几乎致命的山地自行车事故中幸存下来的彼得·吉布(Peter Gibb)也经历了自杀的念头,他从重症监护病房(ICU)跟随他回家。他告诉我:“我很幸运,在英国的一家医院里有一家ICU后续诊所。”“你会被邀请回来,你可以谈论你所经历的一切,因为你的疾病危急阶段和你所感受到的一切之间存在着脱节。”
吉布漫长的康复之路激发了他创建ICU Steps的灵感,这是一个为受到危重疾病影响的患者和家庭提供支持的组织。由于第一手知道记录ICU日记的好处,他目前正在开发一种基于云的产品,他希望这种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地有冠状病毒患者的医院实施。
在美国,每年只有16家ICU后续诊所为500多万名新的ICU幸存者提供服务。其中两家最大的诊所-范德比尔特和约翰·霍普金斯-已经看到冠状病毒患者的涌入。
吉布说:“临床医生做了如此出色的工作,让我们达到了生存的地步。”“但是生存和找回我们的生活是两码事。”
我们想听听您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向编辑提交一封信,或写信给[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