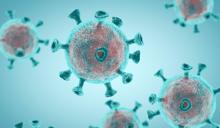年轻、健康的人正患上冠状病毒
在我生病的前一天,我跑了3英里,又走了10英里,然后像往常一样跑上楼梯回到我五楼的公寓,一边走一边扔衣服。
第二天,也就是4月17日,我成为数千名感染冠状病毒的纽约人中的一员。从那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住在纽约市,你知道这种病毒能做什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估计有2.4万名纽约人死亡。这是我们在过去20年里死于凶杀案的人数的两倍多。
现在我为其他地方的美国人担心。当我看到人群挤进阿肯色州一家新开张的大卖场,或数十人没有戴口罩挤进科罗拉多州餐厅的照片时,很明显,太多的美国人仍然没有意识到这种疾病的力量。
生病的第二天,我醒来时发现胸口深处好像埋着滚烫的焦油。除非我四肢着地,否则我无法深呼吸。我很健康。我是个跑步者。我今年33岁。
一小时后,在急诊室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医院的病床上,惊恐万分,手指挂在脉搏氧气机上。我右边躺着一个人,他几乎不能说话,却不停地咳嗽。在我左边的是一位年长的男子,他说他病了一个月,装了起搏器。他不停地向医生道歉,感谢他们对他的精心照顾。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停止对他的思念。
最后,奥德丽·谭医生向我走来,她亲切的眼睛从面罩、护目镜和面罩后面看着我。“有哮喘吗?”她问。“你抽烟吗?”有没有什么先天条件?“。“不,不,没有,”我回答说。谭医生笑了笑,然后摇摇头,几乎察觉不到。“我希望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她说。
我是其中一个幸运儿。我从来不需要呼吸机。我活下来了。但是27天过去了,我仍然患有挥之不去的肺炎。我用两个吸入器,一天两次。我不能不停下来走几个街区。
我想让美国人明白,这种病毒正在让原本年轻、健康的人患上非常非常严重的疾病。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流感。
即使是20多岁的健康纽约人也被送往医院。根据卫生部的数据,纽约州至少有13名儿童死于冠状病毒。我朋友29岁的男朋友病得比我还重,一度几乎不能穿过他们的起居室。
也许你不住在大城市。也许你不认识任何生病的人。也许你认为我们住在纽约是疯了。那没问题。你不需要像我们一样生活,也不需要像我们一样投票。但是请向我们学习。请认真对待这个病毒。
当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几乎不能打电话。我想说我读了一些书,但我没有。我是一名女新闻工作者,但我不能看新闻。
相反,我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健康而完整地沿着纽约海滨奔跑,850万邻居都在我身边。我想象自己正在做一些我还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结婚,买房子,当妈妈,养狗。
我盯着客厅窗户旁边的照片墙,一遍又一遍地向里面的人承诺,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我看了几十部电影。我重新发现了“空军一号”,并幻想如果哈里森·福特现在真的是总统会是什么样子。我熬夜做呼吸练习和播放“长泥”(Longmire),这是一个关于怀俄明州治安官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好人总是获胜。
我学到的一件事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家里处理症状时,几乎没有什么护理或建议,这令人震惊。
在德国,政府派出医务人员团队上门服务。在美国,初级保健是事后才想到的,大多数冠状病毒患者唯一能得到亲身护理的地方就是急诊室。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它是一种疾病,可能会导致几个月的严重症状,并在几个小时内从轻微转变为致命。
我得到的最好的照顾来自我的朋友。弗雷德是一名在纽约一家医院治疗病人的急诊室住院医生,他骑自行车上班时给我打来电话,不断地检查并询问我的症状。切尔西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一名医生助理,她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从肺炎中恢复过来。佐伊是我儿时的朋友,也是一名护士,她教我如何使用脉搏血氧仪,后来又教了我现在使用的哮喘吸入器。
通过他们,我成了一名业余专家。这是他们给我的建议。我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买一个血氧计,这是一个神奇的小设备,可以从指尖测量你的脉搏和血氧水平。如果你生病了,氧气降到95度以下,或者呼吸困难,就去急诊室。别等了。
如果你有胸部症状,假设你可能得了肺炎,然后打电话给医生或去急诊室,趴着睡,因为你的大部分肺实际上都在你的背部。如果你的氧气稳定,每小时换一次体位。做呼吸练习,很多次。看起来最适合我的是英国医疗系统的护士们首创的,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也分享了这一点。“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J.K.Rowling)分享了这一点。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还在倒卧,仍然不能跑步。但是我将能够做那些事情,甚至更多。现在,与老朋友的每一次谈话都会带来一股新的爱的热潮。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感觉就像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海洋,就想直接跳进大海里。
我的很多邻居都没能活下来。我知道是因为我听到救护车在深夜来接他们。来自这座城市英勇的急救部队的报告表明,对于这些纽约人中的许多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美国死于这种疾病的人数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医疗体系支离破碎。因为尽管所有种族和背景的人都在遭受痛苦,但在美国,这种疾病对黑人和棕色人以及土著人民的打击最大,而我们被视为牺牲品。
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不一定是死于病毒,而是因为这个国家辜负了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这就是我现在的悲痛,那就是内疚和愤怒。
有一位是60岁的伊德里斯·贝(Idris Bey),他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纽约市消防局的一名EMT教官,他在9·11事件后的行为获得了一枚奖章。11攻击。
30岁的拉娜·佐伊·芒金(Rana Zoe Mungin)是纽约市的一名社会研究教师,她的家人说,她在布鲁克林努力获得护理后去世。
有一位是28岁的瓦伦蒂娜·布莱克马,她是亚利桑那州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梦想着领导纳瓦霍民族。
他们是我在夜里仰卧时看到的面孔,努力做每一次深呼吸,为他们和我祈祷。现在,在我整洁的布鲁克林社区,每当我走出家门,在一片盛开的紫丁香和骑着滑板车幸福地呼啸而过的小孩子们中,缓缓步入温暖的春日中,我想到的就是这些美国人。
我希望冠状病毒永远不会来到你的镇上。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会为你祈祷的。
“泰晤士报”致力于向编辑发表各种信件。我们想听听您对这篇文章或我们的任何一篇文章的看法。这里有一些小贴士。这是我们的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