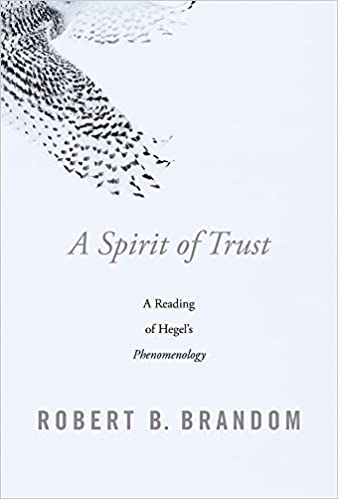哲学体系--评罗伯特·布兰登的“信任精神”
罗伯特·布兰登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的哲学家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他可以与从17世纪到19世纪曾经横跨地球,或者至少在研究中隐约可见的哲学巨人相提并论: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康德、黑格尔体系建设者,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现实,以及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和现实是可以解释的(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布兰登期待已久的书“信任的精神”就是这种古典风格的成就,在这个一丝不苟的专家时代,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成就。
在布兰登的哲学中,许多流派汇聚在一起,它来自C·S·皮尔斯和约翰·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来自分析哲学的许多流派,包括戈特洛布·弗雷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W·V·奎因;来自威尔弗里德·塞拉斯和约翰·麦克道尔的“匹兹堡学派”(布兰登本人在匹兹堡大学度过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以及,事实证明,它来自G·W·F·赫特根斯坦(G.W.F.Hittgenstein)的“匹兹堡学派”(Pittsburgh School)(布兰登本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匹兹堡大学度过的);以及,事实证明,它来自G.W.F.Hittgenstein。
但这本书,以及布朗德现在庞大的整体作品,远远不止是综合的:信任的精神相当于一个全面的、连贯的、原创的哲学体系,横跨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历史哲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哲学。布兰登在这些领域的参与是雄心勃勃的。尽管基调相当古板,但这本书展示了最好的大陆哲学的虚张声势的推测和解释学上的独创性,以及最好的分析作品的严谨。
根据他在后记中给出的自己的说法,自1980年以来,布兰登一直在匹兹堡的研究生研讨会上就他自己的哲学发展对黑格尔的解释。关于布兰登使用黑格尔和本书未出版部分的谣言已经在教授和研究生中流传多年。他的语言分析哲学在最广泛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应用,正如本书所捕捉的那样,总是含蓄的。
“信任精神”的基本理念是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随意性。他在1994年出版的“使其清晰”一书中最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语言意义以及真假本质上都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他的语义学语言是义务与禁止、权威与责任的语言。“一个判断被算作代表了某个被代表的对象,”他在一种典型性的表述中说,“只要该对象对其正确性负责,只要该对象对其正确性行使权威或作为评估其正确性的标准。”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一种特定的事物,或对它提出一种特殊的主张,都带有一系列理性的含义。说晴天的天是蓝的,不仅仅是用特定的话语来表示一个离散的事实,而且也是在承诺自己遵守句子隐含地表达或包含的整个逻辑关系的联系。无论你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你也致力于声称天空不是黄绿色的,你致力于声称天空是那种可以着色的东西(例如,与正义不同)。我们会认为那些坚持认为天空是蓝色但没有颜色的人是明显的非理性的,以及一个一贯忽视他的断言意味着精神疾病或不会说这种语言的人是完全不理性的。如果你声称天空是蓝色的,但不是彩色的,你不仅仅是在说错话--你是在表明你根本没有相关的概念(“蓝色”和“有色”)。至少,你违反了你的理性义务。任何人都有能力表达任何事情,这都是因为社会习俗使人们遵守这种理性的蕴涵和不相容的规则。在布兰登的公式中,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康德,尤其是维特根斯坦。
对于布兰登来说,某句话是否正确的问题,离不开关于什么是允许或必须说什么或相信什么的理性标准。布兰登说,这一“道义”的描述与黑格尔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例如笛卡尔和洛克)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通常将断言视为一种图画,并声称通过图画是否与现实世界的事实一对一地匹配来评估它的真实性。在黑格尔之前,西方哲学传统经常将断言视为一种图画,并声称通过图画是否与现实世界的事实一对一地匹配来评估其真实性。
这是对真相的代表性描述,类似于布兰登的论文导师(也是我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说的“自然的镜子”,罗蒂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抨击这一点。布兰登复杂的另一种选择是,我们的描述构成了一个由社会构成的理性承诺的系统,只有在社会上表达和实施的语言规则才能给我们的语言以一种
这听起来很像是要堕落到真理的连贯性理论,甚至是经常与罗蒂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语言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布兰登关心的是回答这样的批评,尽管不仅仅是拒绝它们。他断言事物本身和它们对意识而言是什么之间必要的同构;他声称宇宙本身在概念上是有序的,或者至少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不存在。在物质世界中,不仅在头脑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蓝色和完全黄绿色的。布兰登对人类智力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看法是复杂的,不能在这个空间中完全捕捉到,很少有哲学家比布兰登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更详细。
这也只是这本令人惊叹的书中提出并仔细探索的十几个环环相扣的基本命题之一。布兰登从根本上发展了原创立场,涉及从叙事理论到自由意志问题再到政治国家本质的方方面面。他通常将这些观点归因于黑格尔,尽管我一般会将它们归因于布兰登。然而,传统的对黑格尔的解释被这个方向所强化和挑战;布兰登恢复了黑格尔的杰作“精神现象学”的无数细节-例如,“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并将它们堆叠成一个完全连贯的系统。我们可以将不同之处归结为布兰登的黑格尔,他的系统性不亚于黑格尔本人,尽管他比黑格尔清楚得多;甚至连布兰登这位英雄主义的近距离读者,也称现象学的多个段落为“本体”。
布兰登对意义和真理的规范性描述在他以前的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特别是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但使用黑格尔的术语-尽管这看起来不太可能-澄清和丰富了这一立场,并将其与哲学史深刻地捆绑在一起。但随着书的继续,布兰登在黑格尔的帮助下,将语言意义的技术理论扩展为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宇宙的结构。语言的分析哲学,在布兰登手中,变成了宇宙(偶尔也是这样,比如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和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的作品)。
布兰登从黑格尔那里得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的意思,就像1700年口渴的人不可能知道,想要一些水,他们想要化合物H2O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概念的澄清,我们会更多地了解我们已经意味着的东西。这就要求意义只能追溯到完全确立。在黑格尔的名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降临时展翅”中,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什么或概念的内容是什么,只有当这个项目或概念凭借充分发展或明确的优点而完成时,我们才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或一个概念的内容是什么。进步历史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我们的概念结构中,我们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意思,从而接近真理。
例如,牛顿的物理学不仅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相矛盾,牛顿的物理学使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成为可能,甚至在爱因斯坦被超越的时候也被爱因斯坦采用。在这里,布兰登阐述了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牛顿物理学是错误的,因为它是通往真理之路上的必要阶段,我们仍在旅行。牛顿物理学是“真理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已经隐含在牛顿继承的词汇中(比方说力的概念);它存在于那些在历史上不断发展的概念中。要理解牛顿物理学在真理逐步展开中的地位,用布兰登相当令人惊讶的公式来说,就是“原谅”牛顿,因为它在通向更大真理的道路上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阶段。宽恕他,除了其他事情外,就是克制住不把他当作仅仅是在断言谎言而不屑一顾。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臭名昭著地将一种相似的宽恕精神延伸到凯撒和拿破仑等“世界历史”人物身上:也许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做坏事的坏人。但黑格尔声称,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控制我们的判断或愤怒,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进步历史上一个必要的时刻,推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前进。
事实上,布兰登似乎在争辩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任何人交流的可能性都要求我们练习这种追溯性的宽恕。他最终与黑格尔一起暗示,即使是最明显或最可怕的错误,也会被意义结构救赎,成为揭示真相或理解我们已经意味着什么的过程中必要的理性步骤。这开始看起来像是一种完整的道德和政治哲学,雷斯蒂
然而,布兰登将语言哲学扩展到全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否定的。例如,我并不完全清楚,根据布兰登的说法,是否真的有可能在不了解一切的情况下知道任何事情,也不清楚一旦我们本着“信任的精神”接近这些错误,他是否能排除倒退的、无用的或恶意的错误,使其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真的。事实上,这也是黑格尔的立场:我们每个人的智慧,包括所有明显的错误,都是上帝的一点智慧。但要把我们带到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布兰登的技术设备。上帝很少在“信任的精神”中明确地出现,尽管集体意识的形式以共同的语言实践为中心,这可能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的意思。但是神性确实时不时地浮现出来,布兰登指出上帝“不是(正如信仰认为的)一个客观的、独立的存在,而是[信仰]自己思想和实践的产物”,而且根据布兰登的本体论,上帝是真实的。他将语言理性的神化归功于黑格尔,但不仅仅暗示他自己也认可这一点。
如果有人想要攻击整件事,他可能会从结论上倒过来。如果这就是布兰登的意义理论最终的归宿--以对所谓错误的普遍宽恕的隐秘基督教精神,或者以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所谓必要结构的描绘,或者将我们的理性(如果有的话)视为神圣的-那么最初的规范意义理论肯定存在错误或有问题的地方。
正如在“罗蒂”中一样,布朗德关于意义和真理的理论,以及(因此)心灵和现实的理论都是无情的语言,尽管他试图在许多方面消除这方面的刺痛--比罗蒂做的要彻底得多--但他似乎没有一个原则性的位置来放置语言之外的现实;事实上,“语言之外的现实”这一概念只是作为某些语言实践的前提,而不是作为对我们是居住在物质环境中的有机体的平淡承认:“存在一种事物自身确定的方式的概念--也就是说,独立于它们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是理论和实践意识概念的基本结构要素。”这并不完全等同于断言确实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思考方式的世界。
此外,布兰登的立场过于理性主义;我不相信我相信蓝色的东西不也是黄绿色的义务,就像我的义务一样,不能无缘无故地伤害人。也就是说,理性规范的“道义”地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假设,而不是结果,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我们现有的实践所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例如,像极端反黑格尔的索伦·克尔凯郭尔那样)决心接受一个悖论,或者如果我只是对我已经相信的某些理性暗示漠不关心,我们怎么能证明这是“不允许的”呢?我会相信我喜欢的,非常感谢。
我还要指出,这本书重复得太多了。以黑格尔的方式,每一次对基本思想的重新概括都是为了通过重新语境化来丰富我们的理解。尽管如此,这本书可能已经损失了几百页或更多(该书的“结论”是对前600页的120页总结,在此过程中已经有了许多总结),这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当我完成“信任的精神”的长途旅行时,我的主要反应是感激,因为即使现在还能进行这样一个项目(更不用说如此出色地完成了),并羡慕能够产生这种项目的智力。索引本身肯定是一项艰巨的劳动。
1979年,就在布兰奇在罗蒂的指导下完成他的论文后,罗蒂认为哲学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证明,他强烈地向自己的学生暗示,在这一学科追求更高的学位是徒劳的。同意或不同意他的任何特定断言,布兰登的职业生涯在本书中第二次达到顶峰,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明,表明哲学,即使是在其最宏伟的系统野心中,毕竟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