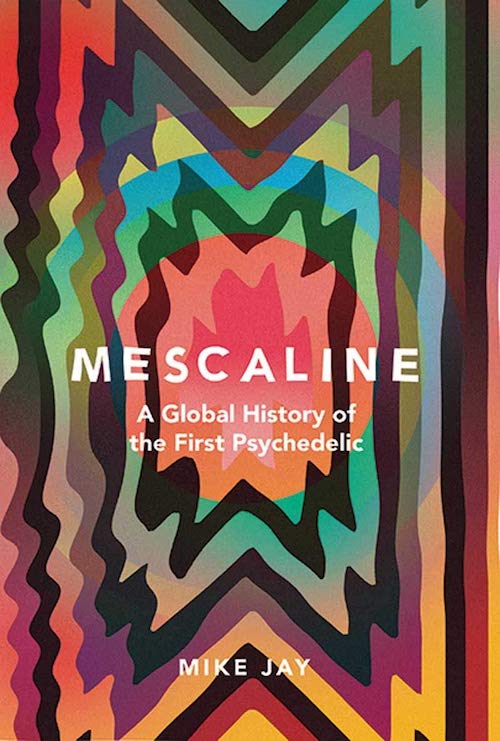梅斯卡林的生平,清醒地考虑
迈克·杰伊的新书“梅斯卡林:第一个迷幻人的全球历史”(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令人耳目一新的部分原因是,他对所谓的真理探索者和通灵者并不感兴趣。他拒绝把宗教狂喜、苦行僧或旅行者视为开悟的人。当然,这样的人经常牺牲物质上的舒适,达到可能会让人敬畏的程度。事实上,几年前在摩尔多瓦,我曾经骑着马去过老奥尔黑,在距离Chișinău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那里的东正教僧侣住在洞穴里。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经受住孤立、饥饿、寒冷、无聊,想必还有恐惧的能力,在当时我的脑海里肯定是令人敬畏的。许多关于扩展意识或改变思想的物质的写作都是为了唤起敬畏之情。即使是勇敢而科学深度的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当他通过迷幻之旅进行自己的搜索时,也不能幸免于敬畏(据他在2018年出版的《如何改变心意》一书中所述)。迈克·杰是免疫的。
这使得梅斯卡林可以避开所有对预言家和给予他们幻觉的物质的欢迎。不是诺斯替派侦探,杰伊不是在寻找不可捉摸的真相。他是个传记作家。所以这本书从身份的问题开始,他通过一张梅斯卡林分子的化学图展示了这一点。这提醒人们,在所有关于迷幻药物的争执背后,它们每个都只是碳、氢、氧和氮原子的一种配置-与我们一样。
至于生活史,首先是仙人掌。杰伊告诉我们,梅斯卡林天然存在于柱状圣佩德罗仙人掌属(Trichocereus),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安第斯山脉,以及墨西哥北部和美国西南部粗壮的仙人掌属Lophophora。西班牙征服者地区的许多植物都生产醉药,其中含有梅斯卡林的可能并不是最常用的。宗教裁判所找到了一种将这种陶醉视为非基督徒的方法,而佩奥特使用者,无论他们是在个人幻象中使用,还是在与萨满的治疗仪式中使用,还是在公共仪式中使用,都会被起诉。人们习惯于认为技术理性系统地追逐和镇压所有形式的松散和非生产性的实践,但纵观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这实际上只是一种试图消灭另一种的非理性。
然后,在分子生命历史的第二阶段,有了资本。19世纪80年代,底特律的Parke-Davis制药公司(当时称为Parke,Davis&Amp;Co.)委托探险队前往美洲。通过获得古柯叶取得了营销上的成功,并在1886年销售了第一种药物标准化兴奋剂:可卡因。一旦认真的人类学家让佩奥特仪式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帕克-戴维斯就急忙复制它在可卡因方面的成功,将佩奥特样本送到备受尊敬的植物学家和化学家手中。但到了1893年,杰伊告诉我们,它已经决定销售的不是一种标准化药物,而是一种仙人掌提取物,该公司含糊其辞地声称可以将其用作“强心剂”。
在德国莱比锡,化学家亚瑟·赫夫特从佩奥特(Peyote)中分离出一系列生物碱(其中一些由帕克-戴维斯(Parke-Davis)提供)。在1897年的自我实验中,他发现其中一种产生了归因于吃仙人掌纽扣的精神效果。他将他的生物碱命名为Mescaline(可能是因为当时人们对peyote和mescal仍有混淆,这是一种从毒豆中提取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在美国西南部的土著部落中都很常用)。
到了20世纪之交,随着纯化和标准化提取物的出现,梅斯卡林的传记与制药业本身的传记合并了。今天,制药行业作为有害技术的典范隐约出现在大众的脑海中:天才化学家设计奇特的分子,拥有微米和纳米技术的实验室合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化学物质,广告高手使用尖端的营销技巧销售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产品。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勇敢的新世界”式的。但Pharma有一个非常普通的起源:化学家们提取了长期以来一直以缓解人类多种形式的痛苦而闻名的植物,试图找出似乎对这种缓解负责的成分,提纯他们发现的东西,并以相对可预测的效果以标准剂量出售。于是出现了用于止痛和止咳的吗啡(来自鸦片),用于止痛的阿司匹林(来自柳树皮),用于嗜睡的可卡因(来自古柯叶),用于止咳的可待因(也来自鸦片)等等。梅斯卡林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
从1894年开始,通过赫夫特工艺生产的梅斯卡林由德国化工巨头默克公司销售。奥地利化学家Ernst Späth于1919年发表了一项新的合成,到1926年,默克的化学家们已经开发出
地点不是意外。海德堡大学是现象学发展的中心。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那里获得了医学学位,并在海德堡诊所接受过精神病学培训,他对了解精神障碍患者如何体验自己的意识产生了兴趣。雅斯贝尔斯转向哲学,于1913年加入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最初在心理学领域,后来专注于意识哲学。
雅斯贝尔斯对精神疾病的现象学方法吸引了一群精神病学家。随后举行了定期会议。海德堡夫妇的兴趣之一是Mescaline Rausch,这个词来源于词根,意思是“冲”(通常翻译为“陶醉”),但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狂喜”或被忘乎所以--一种酒神意识。周在这里的描述很吸引人。梅斯卡林会出现在现象学上对这种意识的追求中。
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是20世纪最有洞察力的意识思想家之一,在他1929年的文章“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张快照”中,他驳斥了药物可以“真正、创造性地战胜宗教启迪”的观点。他断言,毒品只能给“亵渎光明”提供一个“入门课”--对我们大多数人隐藏的现实的了解。他警告说,通过吸毒经历可以学到的教训是危险的,不是因为毒品对身体有害,而是因为经验允许的感觉可能无法根除。本杰明知道,正如杰伊指出的那样,文化训练我们生活在一个无论它是多么虚假的世界里。意识到一个不同的真相可能会使人无法继续生活。
毫无疑问,本杰明非常熟悉精神活性物质及其感知效果:在海德堡的工作开始后不久,他就被柏林的一小群激进的左翼神经学家兼精神病学家所吸引,这些人也对药物和意识感兴趣。这群人包括他当医生的哥哥格奥尔格;他哥哥的同事弗里茨·弗雷恩克尔(Fritz Fränkel)和恩斯特·若埃尔(Ernst Joël);他母亲这边的表亲,医生埃贡·怀辛(Egon Wissing);威辛的妻子格特(Gert);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本杰明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自我记录的大麻经历就是通过这些经历开始的,就像他在1934年用梅斯卡林进行的实验一样。Joël和Fränkel已经阐述了他们对药物增强体验的看法:他们称药物为“药物心理学”,而不是将药物用作治疗药物,而是暗示,通过使用“现象学、分析学和格式塔理论学派”的心理学方法,可以更彻底地实现“改变的精神生活”,也就是更优越的精神生活。
总而言之,海德堡的现象学精神病学工作和20世纪20年代柏林的革命精神病学工作使美斯卡林牢牢地跨越了二元性:它不一定是治疗功能障碍的药物,也不是工业化改变的自然界中增强意识的残留物;它可以帮助我们革命性地重新安排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方式。正如杰伊所说,吸毒可能既是“一种私人起义的形式,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工具”。
1933年,当纳粹上台时,精神病学的存在主义人文主义时代结束了。许多使用梅斯卡林的人都是犹太人。他们逃走了,但即使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下的人类意识也可能不再是关于个人的,而必须是关于沃尔克的。就不会扰乱意识了。那些精神状态与声称的人民福利或种族利益相冲突的人将通过纳粹主义治疗方法接受治疗,否则他们将成为数万名莱本森沃特·莱本斯(Lebens Lebens)中的一员,生活不配活下去,因此被暗杀。
在周传记的最后阶段,精神活性分子转移到了美国。它们变成了美国意义上的毒品:它们变成了工具。药物是用来通过治疗指定的疾病来达到健康(或“健康”)的。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医药产品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能会减轻我们的痛苦,但它们的必要性也与它们给混乱带来的秩序息息相关。大约一半的美国成年人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使用处方药。这些药物的存在证实了当代世界的障碍--抑郁、焦虑、慢性疼痛、边缘人格和注意力缺陷,并因此赋予了它们生命。
作为一种医药产品,美斯卡林并不能使自己在缓解任何精神病学批准的“障碍”方面具有市场价值,尽管它曾被短暂地作为一种拟精神病药物进行研究-一种模拟精神疾病的方法,以研究其他药物作为治疗药物的效用。但是,杰解释说,梅斯卡林在I中的作用
杰伊的书没有对美斯卡林的医学化提出异议。他在这本书里崇敬的是艺术。这本书对梅斯卡林和视觉体验之间的许多联系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包括艺术的制作和观看。艺术,也许只有艺术,可以挑战当代的时间条条框框:将时间分割成小时、分钟和秒,就像时间是火腿一样;将时间等同于生产力;将生产力转变为特权。我们习惯于认为科学会照亮黑暗。通常是这样的。但是梅斯卡林暗示了意识、自我和视觉之间的联系。杰伊总结道,梅斯卡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谱”使其“在西方文化中令人着迷、诱人和沮丧”。但对于原住民来说,与其“试图将其扭曲为预先设定的目的,它的传统使用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它,并围绕它塑造自己的世界”。
我从没试过梅斯卡林。但是,提醒人们美洲人民知道什么,以及现象学精神病学家发现的是什么,这是很有启发性的:世界仍然拥有秘密;无意识是一个宝库;“改变的精神生活”可能比诊断和治疗“疾病”更有意义。科学并不是照亮道路的唯一手段。我们现代人对我们自己的世界如此矛盾,需要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