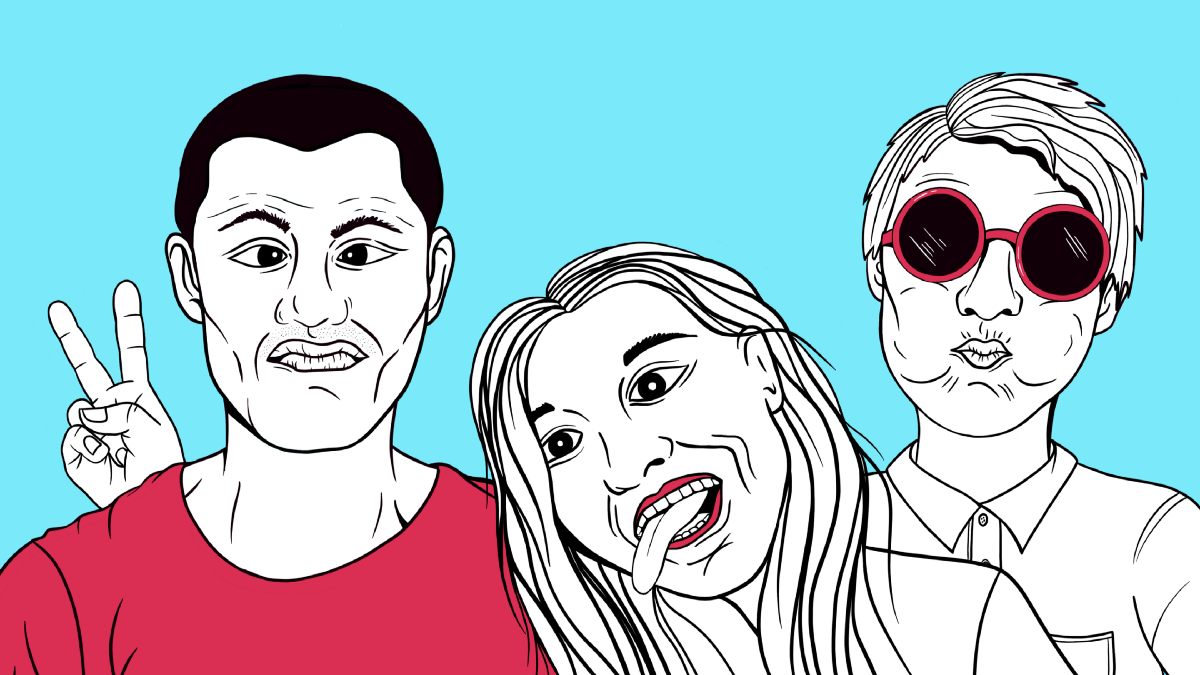共同创始人关系中潜藏的痛苦
联合创始人关系是大多数创业故事的核心。但就像大多数婚姻一样,痛苦和挣扎与快乐和合作一样多。通常更多。为什么没人谈论这件事?
我记得在冻雨中漫步在巴黎。那是2010年3月,巴黎的冬天刚刚过去。当我对着耳机谈论加州梦时,我浑身发抖。
托德和我几个月来一直在讨论重新开始的事情。我们第一次合作的尝试非常有趣,但很短暂。当我们都23岁的时候,我们在密西西比州安娜堡的公寓里开了一个汽车比对网站。
原计划是搬到西雅图,在那里建立业务,但托德爱上了一个名叫凯蒂的漂亮女孩,并认为搬出密歇根州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很有花园之州的特色。值得称赞的是,他确实娶了那个女孩,现在他们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因此,这是以一种发光的方式进行的。
我搬到洛杉矶是为了加入一家初创公司。然后在法国呆了几年,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把国际的东西从我的系统里拿出来,进行了几次疯狂的冒险。但我想念加州。我很想重新开始。因此,在我和托德第一次决定辞职创业六年后,我发现自己在巴黎走来走去,浑身湿透,试图说服他搬出密歇根州,带上他漂亮的妻子,和我一起在西海岸开始新生活和新公司。他和凯蒂决定搬家。
对于我们可能要建造的东西,我们没有太多的愿景。
我们的梦想不是打造下一个Facebook。我们的愿景是住在海边,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工作。
我们说服了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史蒂夫加入我们。史蒂夫是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软件工程师之一,他也很有才华,他同意加入我们的漫无边际的旅程,进入“下一个是什么”(What‘s Next)。
凯文将作为我们的第四位联合创始人加入,因为我们卖掉了第一个刚刚起步的项目,并将我们的第二个项目发展成最终成为Twenty20的项目。凯文因其从容不迫的性格和永不停歇的微笑而被称为“禅师”。但在最早的时候,只有我们三个人:托德、史蒂夫和我。这就是我要关注这篇文章的地方。
七年后,我发现自己是最初三个人中唯一还活到二十岁的人。当我们去年通过出售业务时,这种认识对我来说是令人心酸和痛苦的。
我们几乎在所有战线上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制造了一款供世界各地数十万人使用的产品。我们与世界上一些最好的投资者合作过。最终,我们在洛杉矶西区建立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和一座灯塔,让人们相信工作场所可以成为人类和个人成长的源泉。
但我们最初的使命是住在海滩边,和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起工作,但我们失败了。
我需要在这里提醒的是,我在这里真正了解的旅途只有我自己的一部分。托德和史蒂夫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且他们可能用非常不同的镜头来看待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我计划在发表之前与他们每个人分享这篇文章,以帮助消除任何严重的错误,但当然,这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错误(也许是奇迹),我们只有自己的头脑来解释和记录生活。但至少从我坐的地方看,第一年就开始换班了。
我们谁也没见过这件事做得对。我们从未在一家成功的初创公司工作过,也从未见过一家公司从头开始深思熟虑地运营。
我早年曾在几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担任过领导职务。他们是由善意的创始人运营的,但从未找到任何有意义的吸引力。这些经历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清晰的愿景,即早期的首席执行官如何帮助一家年轻的公司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三个人找到了去洛杉矶的路,洛杉矶是我们新公司商定的总部,我们租了我们的第一间办公室。我们为它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可以看到海景。说大也大吧。它由两个小房间组成,位于雷东多海滩的一座自助仓储大楼的后端。我们的办公室俯视着巨大的雷东多发电厂。从左到右,我们看到的95%是灰色发电厂。但是剩下的5%,那些极左翼和极右翼的光辉的蓝色长条,是我们自己的一小块美丽的太平洋。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正式的角色。但我们大体上同意,史蒂夫将负责工程、托德产品和市场营销,我将担任首席执行长,处理“所有业务事宜”。我们没有人真正知道所有的商业活动是什么意思,但我是唯一一个想要首席执行官一职的人。
我记得在第一年,作为CEO的责任让我感觉到了与我的联合创始人不同的感觉,而且往往是完全孤独的。
在我生命的头30年里,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一幅领导力的图景,暗示着领导者可以独自解决问题。领导者把问题解决在自己的头脑里,把焦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我想我在美国媒体雕刻的经典男性形象中亲眼目睹了这个形象,我也看到过我自己的父亲生活在这个形象中。无论它来自哪里,即使在早期,我也觉得我需要领导。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不愿把我的担忧、好奇心和情绪公开带给我的联合创始人,这极大地导致了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基础出现裂痕,最终导致了我们的毁灭。
如果说我在早期感到与我的联合创始人有隔阂,那么当我们决定筹集风险资本时,这种隔阂就会大大加剧。在第一年,我们的团队利用外部资金从最初的4名滚雪球般增加到了12名。我的注意力突然转移了,我想是永久性的,从关注内部转向关注外部。
在第一年,当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像一个团队。即使我发现自己经常在自己的脑子里,或者在焦虑中与世隔绝,我们还是坐在同一个小房间里,一起谈论着这么多工作。虽然我有很多希望能回到过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但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确实有一些神奇的东西。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坐在底特律的一家酒店房间里。凌晨4点因为某种奇怪的时差而起床,我发现自己在回忆那段时间时泪流满面。这些泪水让我很惊讶,因为那几个月让我感到焦虑不安。我想我已经错过了美好的时光。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公司将远远超出我们坐在发电厂旁边的小办公室里的预期。那次旅行将对我们三人曾经共享的亲密友谊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我认为,失去这些关系导致我屏蔽了太多早期建立业务的时间。
当我从巴黎搬回来的时候,我只想在海滩边做点小生意,在那里我可以每天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上班。
不出两年,史蒂夫就会彻底离开公司,而我和托德几乎不会说话。
2005年,史蒂夫和我作为洛杉矶一家初创公司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员工相遇。我们都是新来的,朋友也不多。我们并排坐在一间比我的大学宿舍还小的办公室里。我们成了好朋友。
史蒂夫是一位才华横溢、受过麻省理工学院培训的工程师,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有充分的理由,他可以在两周内建造出任何东西。
当托德和我开始谈论追逐梦想,搬到洛杉矶,一起开公司时,我们决定需要一位技术联合创始人。而史蒂夫是显而易见的选择。
当我们开始探讨合作的时候,我们同意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会面,给托德和史蒂夫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给我们三个人一些时间来思考想法。我们自驾游到密歇根州北部的海港斯普林斯,租了一间小木屋,然后吃了垃圾食品,玩了100场Catan游戏。
到周末,这件事就解决了。我们三个人打算一起开一家公司。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经历了疯狂的挣扎和错误的起步。我们开始了一个垃圾点子,8个月后把它卖了,赚了足够的现金再投资,开始新的事情。
两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在第一次推出Insta anvas(一个有趣而简单的产品,允许任何Instagram用户获得自己的在线画廊,将他们的作品作为画布壁画出售)上取得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吸引力。
Instaanvas突然出现,在没有营销的情况下,在几个月内迅速增长到10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能够迅速筹集到第一笔真正的风险投资。
有了这笔钱,就有了扩大团队的任务,并探索可预测的方式,在我们早期的病毒式引擎之外扩大收入。我们开始雇佣工程师。
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经营着我的第一家风险投资初创公司的非技术型CEO,工程学的世界简直就是一个黑匣子。多年来,在迈克尔·罗比内特(Michael Robinette)的耐心合作下,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帮助建立一种工程师能够茁壮成长的文化。但是,在2012年,我他妈的一无所知,我陷入了困境。
托德、凯文和我把工程招聘和所有工程管理的绿灯交给了史蒂夫。
一开始相当不错。除了我们雇佣的第一位工程师没有事先通知就辞职了,似乎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带走了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你不能胡编乱造。但在工程团队壮大了几个月后,我们开始听到对史蒂夫的抱怨。我们被毫不含糊地告知,史蒂夫必须离开,否则我们最好的工程师将辞职。
据我回忆,这是史蒂夫第一次管理,我非常后悔没有与他更密切地合作,帮助他为那次努力提供资源。我最好的猜测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史蒂夫可能非常适合做一名个人贡献者或架构师,但不太适合扩大早期工程团队和高增长初创公司的规模。尤其是对于一个不知道如何协助的CEO来说。
这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我仍然相信如果我有更多的经验和远见,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一条让他留在球队的途径。
托德和我带着史蒂夫共进午餐,笨手笨脚地请他考虑转换角色,支持我们引进一位更有经验的工程主管的愿望。想起那顿午餐,我的胃里就像个坑一样。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求他返还一部分股权(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将公司一分为三),以帮助我们支付招聘最高领导层所需的巨额拨款。
虽然我相信我们仍然通过艰难的变革为公司做了必要的事情,但我对失去史蒂夫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友谊感到心碎。7年后,我仍然对那次损失感到悲痛。
我知道史蒂夫在离开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的损失。这也让我很难过。
史蒂夫最后变得和蔼可亲,他可爱的性格也是如此。他走后一年左右,我们见面喝了杯啤酒。我们聊起了我们的友谊,从最开始在曼哈顿海滩那间小办公室里的日子到艰难的离别,以及从那以后我们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像那样的啤酒。
从2003年我们相遇开始,我和托德就是最好的朋友,直到2011年我们决定一起搬到洛杉矶。在2004年关闭了我们的第一家公司后,我们两人都渴望有另一次合作的机会。我们喜欢第一次尝试。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为他工作的日子;那些在我的安娜堡公寓开始我们自己的第一件事的日子是光荣的。我会坐在客厅的办公桌前,托德会坐在我旁边,停在我的餐桌旁。我认为那些日子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次品味,刻下了我们自己的命运。与我们所爱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的想法深深地引起了我们两人的共鸣。
在关闭那家公司到2011年开始与托德重新合作的这几年里,我非常怀念那种同志情谊和联系。在那几年里,我做了其他有趣的工作,但在这段经历中我感到孤独。
因此,当我们一起在洛杉矶定居,并承诺最终共同开始另一项业务时,我非常兴奋。
在洛杉矶的那些早期日子很有趣,回首往事,我脸上挂着微笑。我记得一起在赫莫萨海滩散步,集思广益,想着我们可能会做些什么。我们他妈的一点都不知道。各种创意,从豪华电影院、洗车到各种基于网络的企业,都进入了榜单。
即使是在最初的日子里,这部作品也从未拥有我们7年前第一次尝试合作时所珍视的嬉戏和轻快。
我想,在24岁的时候,工作仍然感觉很像是一种娱乐。我们没什么可损失的。我们几乎没有积蓄,住着便宜的公寓,而且我们都是单身。
31岁时,我们都结婚了。我们都完成了顶尖的MBA课程,并花了数年时间建立各自的职业生涯。
没过多久,托德和我就开始失去最初让我们走到一起创办公司的友谊。多年来,我们一直梦想着一起开一家公司,然后重新住在同一个小镇上。但我们很快就只在办公室呆在一起了。
我认为,随着业务的发展,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变得如此沉重,以至于我们不想把它带到我们的夜晚和周末,除非有必要。我确实记得有几次我们在一起吃饭时的尝试,我们承诺“不谈工作”;但这与创业前的友谊完全不同。
在我们提升了甲级联赛并将团队规模扩大到50多人后的一年里,我们遇到了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失去了信任和联系。不久之后,我们不再相信(或许也不记得)我们把彼此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我发现自己首先把托德视为我们的产品副总裁(或后来的人事部主管),而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他首先看到的是让他感到沮丧的CEO,而不是他最好的朋友。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些非常积极的改变。我们一起参加了联合创始人训练营,这给了我们一些空间来开始处理我们的关系面临的一些挑战。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共同的背景和语言,用来将这些对话带回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都开始与教练合作,他们帮助我们处理自己的经历和旅程。
我们都开始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让我们不快乐的部分经历是我们个人应受责备的方式。
我个人开始明白,我在信任方面有很大的问题,这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我从我的家人那里了解到,让别人让我感到恐惧并不总是安全的。在我童年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父母都在忍受着他们自己的痛苦。结果,我内化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占据空间是危险的,即使在信任的亲人中间也是如此。把我的焦虑或恐惧转向内心,依靠自己一个人去解决,要安全得多。
正如你可能预期的那样,我作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角色实现了这一点。随着赌注的增加,我的恐惧和焦虑也在增加。
如果我们失败了,我损失了所有这些人的钱怎么办?如果我让所有这些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失望了呢?
我把焦虑转向内心,它表现为抑郁和孤立。我最终会学会如何开始接纳其他人,包括我所爱的人和我的团队。但在早年,我内心的依赖给我和托德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我没有让托德陷入我所面临的恐惧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我在我们的谈话中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内心声音中,以至于不能成为他现在耐心的合作伙伴。我毫不怀疑我是否说过,“我在受苦。我恐怕……。我需要你的友谊“他会立刻提出的。在我们早期的大部分工作关系中,我缺乏那种语言和自我意识。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的工作关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的友谊甚至略有改善。我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托德和凯蒂邀请我在他们的客房里住几个星期,当我忙于思考如何重塑我的生活时,他们对我给予了亲切的照顾。但我们的友谊因公司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而变得紧张。
托德最终会选择在我(和Twenty20)广泛报道的大规模裁员期间离开公司。这次裁员和公司重组将标志着公司发展轨迹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团队将团结在一起,实现5倍的收入,并最终出售业务。但是,当我回想起那段时间时,失去托德总是给我留下一种特别痛苦的感觉。
当时,我们决定裁员我们的销售和客户管理团队,并将重点转移到自助服务收入上,托德是我们的人事部负责人。在我们处理规模早期阶段时,他在调整我们的文化、招聘和人员运营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真的在这个角色中茁壮成长。
当我们计划裁员时,我们的团队将从55人减少到12人,我要求领导团队评估他们自己至少在明年留任的决心。我知道,如果裁员后有任何关键领导离职,团队可能会螺旋式上升。如果我们想要拯救公司,我们需要留住的团队之间的稳定和凝聚力。
我以为我们的另一位领导可能会离开,但我从来没有想到托德会离开。然而,在我要求领导团队评估他们留下来的决心的第二天,托德请我吃早饭,并告诉我他该离开了。他的心思放在提升团队规模上。他知道,如果他留下来,将意味着更少的人工作,更多的产品工作。他的心已经不在那份工作上了。
我认为托德有勇气评估什么对他和他的家人是正确的。并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性的方式公开地与我分享这个决定。非常符合他美丽的天性。
几天后,在我们经历了裁员,正在重新组建团队之后,托德有了另一种想法。我们已经把托德离开的决定告诉了剩下的团队。但看到球队重新组建,看到我努力推动我们前进,他告诉我,他正在为离开是否意味着放弃球队和抛弃我而苦苦挣扎。
直到今天,这种忠诚和关怀让我对托德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的品格和友谊。尽管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切,尽管他相信离开可能正是他和他的家人所需要的,但他并不想放弃球队。他也不想抛弃我。
我们最终决定是托德离开的合适时机。我很高兴我们做到了。而不是因为它对公司有或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是因为他的离开标志着我们重新发现友谊的开始。
我不知道我们的友谊是否会像一起创办公司之前那样。但不管怎样,作为人类,永恒性并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做到的状态。谁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在一起工作,我们的友谊会如何发展。现在是“不同的”了。但它也是丰富的,有质感的,充满了共同的经历。而且它还在不断涌现和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就共同建设Twenty20的时间进行了多次交谈。对于这次旅行,我们彼此表达了很多感激之情。我们探讨了彼此伤害对方、让对方失望的方式。我们分享了我们的成长和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