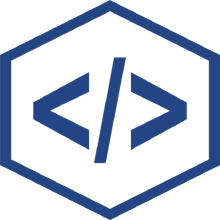开源领域的文化战争正在打响
也许你还记得埃里克·S·雷蒙德(Eric S.Raymond)在他令人难忘的文章“大教堂和集市”(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中的表现,或者他对程序员“不要表现得像个失败者”的建议,或者他对枪支的热情。无论如何,这位传奇的开源程序员和评论员最近短暂地回归了他在1998年与人共同创立的组织“开源倡议”(Open Source Initiative)。2月24日,他在OSI的电子邮件名单上宣布,缺席多年的“天马行空的联合创始人出现了”。到2月28日,在谴责了他认为正在感染该组织的“他妈的政治混账”和“低俗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因违反行为准则而被从名单中除名-行为准则的存在也受到了他的抨击。同样是在上个月,雷蒙德的OSI联合创始人布鲁斯·佩伦斯(Bruce Perens)因为一场显然无关的软件许可纠纷而撤回了会员资格。
这些事情并非毫无关联,真的。它们是被不同地称为“开源核心的文化战争”和“伟大的开源变革”的一部分。这些争议涉及这场运动的核心法律技术,这些技术有几十年的历史,被称为“自由软件”或“开源”:软件许可证,特别是那些将专有代码转化为公共产品的软件许可证。手头的冲突引发了关于伦理和经济学的问题,开源机构认为这些问题早就得到了回答,可以永远放在一边。哦,正如程序员史蒂夫·克拉布尼克(Steve Klabnik)顺便提到的那样,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我个人认为性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第一个自由开放许可证的发起人,去年因同情已故亿万富翁和猥亵狂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言论而辞去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职务。Creative Commons创始人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的声誉也因捍卫爱泼斯坦的推动者之一而受到打击。也许这一切都设置了一种情绪,增强了紧张程度。在一个约95%的GitHub贡献者认为自己是男性的世界里,这场文化战争中的几个主要党派不认为是男性,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
对于游击队来说,一直潜伏在开放源码代码库中的bug可能最好概括为中立。OSI的开放源码定义禁止对“努力领域”、商业模式和技术堆栈等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自由软件基金会这样说:“为了任何目的,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运行程序。”只要代码保持自由和开放,用户-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在做什么或如何赚钱方面都不应该受到许可证的限制。这种观点认为,任何这样的限制都是一种滑坡。在短暂返回OSI的电子邮件列表时,雷蒙德引用了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想要保护自己的自由的人,即使是他的敌人也必须保护自己不受压迫;因为如果他违反了这一职责,他就建立了一个先例,这将影响到他自己。”限制别人,它会回来困扰你。
在第一条战线上,有道德源码运动,Ruby开发者和模型视图文化贡献者Coraline Ada Ehmke的所作所为,Raymond最近最糟糕的尖酸刻薄就是针对他的。道德来源建立在一波又一波的科技工人反对他们的老板与五角大楼和ICE等公司签订合同的浪潮上。ethical Source提供了自己对OSI的反定义,概述了一种允许开发人员限制其软件的特定使用的许可证类型。例如,少数合规的许可证禁止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或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标准。这一承诺让程序员安心,也许是一个更道德的世界;危险是一团糟的不可执行的许可证,这些许可证的禁令变得无法跟踪。
第二个挑战是经济方面的。这一直是开源领域的一个痛处,开源在很大程度上将其经济外包给了一些公司,这些公司可能会为正在建设的项目贡献员工时间或拨款。这些公司也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奖励,留下了许多贡献者提供他们的无偿空闲时间-一种不平等的可用资源。新的律师努力,如Heather Meeker的POLYFORM项目和KyleE.Mitchell的License Zero,提供了旨在支持某些流行商业模式的许可菜单。代码仍然是“可获得的源代码”-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它,并在一定的条款下使用它-但有一些限制,以防止一些公司拿走它并从其他公司的工作中获利。一份POLYFORM许可证只允许小企业免费使用该软件;大公司必须付费。不过,批评人士再次担心,所有许可证都会自由开放,最终会堆积如山的限制和限制公有资源。
让我回到性别问题上来。从技术文化中熟悉的“精英管理”理想的角度来看--而且非常恶毒
你越是通过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开源--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那些二十年前的确定性就会越是开始瓦解。我们需要看到这些裂缝才能制造出更好的工具。
人们经常把开源作为一种共用资源来谈论,但是如果你回去阅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关于全球共用的数字化前实践的研究,你会发现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她没有将自己的工作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但她仍然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奥斯特罗姆承认,划定边界是普通人的基本做法--界定谁是成员,以及公地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她还发现,一个健康的公地依赖于参与者在改变其规则和规范方面拥有发言权,这与倾向于统治开源的终身独裁制度大相径庭。如果开放源码能更好地听取先于它的公众化的遗产,项目不会仅仅选择许可证,它们将从采用治理结构和找到一个地方来管理资金开始。他们会计划经济和道德上的自决-自治是奥斯特罗姆强调的另一个原则-而不是把这些事情外包给公司突发奇想。
无论如何,开源贡献者应该想要破解这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他们编写的软件,这是很自然的。尽管开放源码已经取得了这些成就,但还有很多东西是它没有做到的。“Linux桌面之年”已经从期待变成了笑话,除非你把谷歌的Android和Chromebook计算在内。开放的网络已经关闭。监控驱动的企业平台之所以积累了力量,是因为开源,而不是尽管如此。开源开发人员之间仍然存在的惊人的同质性证明了他们的项目缺少的才华和生活经验。
如果开源的早期架构师感到新一代要求更高的威胁,那很可能是进步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