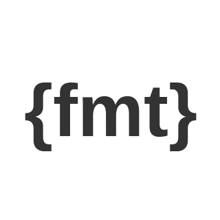为什么现代世界如此丑陋?
我们可以对现代世界做出一个伟大的概括,那就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丑陋的世界。如果我们带着250年前的祖先参观我们的城市和郊区,他们会对我们的技术感到惊讶,对我们的财富印象深刻,对我们的医学进步感到震惊-并对我们设法制造的恐怖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在大多数方面,比过去先进得多的社会设法建造了比人类所知的任何东西都更令人沮丧、更混乱和更令人反感的城市环境。
要想走出这个悖论,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起源。丑陋的原因至少有六个:
从建造伊始,人们就认识到建筑师的任务不仅是使一座建筑能够使用,而且要使它变得美丽。这将涉及一系列超越纯粹物质需要的策略。以美的名义,建筑师可能会在窗户上加一条彩色瓷砖,或者在门上加一排雕刻的鲜花,他们可能会试图在正面创造对称,或者仔细地确保窗户在每一层都变得成比例地变小。
即使这是一座实用的建筑,比如渡槽或工厂,建筑师也会努力给它一个最令人愉悦的外观。罗马人知道抽水系统可能和寺庙一样漂亮,维多利亚早期人认为即使是工厂也可以拥有优雅的乡村别墅的一些美学特性,米兰人知道购物中心可以承载大教堂的一些雄心。在罗马人知道,抽水系统可能像寺庙一样美丽,维多利亚早期的人认为即使是工厂也可以拥有优雅的乡村别墅的一些美学特性,米兰人知道购物中心可以承载大教堂的一些雄心壮志。
但是当建筑到达现代时,美这个词就成了禁忌。现代运动的设计者们开始向他们现在所说的所有以前的“美化”动作的娘娘腔、浪费和伪装发起一场战争。奥地利现代主义者阿道夫·卢斯在一篇名为“装饰与犯罪”(1910年)的文章中认为,用任何“漂亮”的东西来装饰一座建筑是对建筑师真正职业的罪恶--他现在用纯粹的功能术语重新定义了这一职业。卢的现代主义同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提出,只有没有装饰的建筑才是“诚实的”,所有关于美的想法都是对建筑真正使命的背叛,建筑的真正使命只是创造防水的功能结构。正如现代主义宣称的那样:“形式必须服从功能”--换句话说,建筑的外观永远不应该由美的考虑来塑造,最重要的是基本的物质目的。
一开始,这似乎令人振奋-但却是一种解放。19世纪产生了一些过度装饰的建筑,美化冲动已经到了颓废的地步。
与此同时,许多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特别是那些为富有客户建造的建筑-极其优雅,感觉新奇而干净-就像在吃了太多巧克力蛋糕后吃了猕猴桃一样。形式服从功能的格言似乎即将在世界上释放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新型建筑。
不幸的是,这个梦想很快就变得糟糕起来。当房地产开发商听说这位艺术先锋现在正在推广功能主义概念时,他们欣喜若狂。从最高尚的人那里,最卑鄙的动机都得到了认可。这些开发商将不再需要在任何与美容有关的事情上花费任何资金。对称的,鲜花的,漂亮但略贵的材料可能会消失。这一切都可以尽可能地快速、丑陋和廉价;毕竟,这不是伟大的建筑思想家们曾建议的吗?
很快,这个最初是一个有趣的利基想法变成了广大郊区和商业区的正当理由,甚至连表面上的魅力都没有。棚子和粗制滥造的箱子比比皆是。
无论如何,现代主义者甚至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都不诚实。他们可能会提出,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功能”,但实际上,像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或密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这样的伟人对他们建筑的每一个元素都感到苦恼。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秘密地对视觉魅力感兴趣。他们只是想把自己描绘成衣冠楚楚、严谨的工程师类型,从而引起轰动;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艺术家。然而,紧随其后的房地产开发商忽略了这一细微差别。他们的建筑没有优雅地修剪整齐。他们要糟糕得多:草率、卑鄙和丑陋。只是现在,因为现代派大师的话,显然没有人能指控他们玩忽职守。美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散发着精英主义和模糊不清的味道。没有人能再抱怨这个世界失去了美,而不是听起来头脑迟钝。
现代性之所以变得丑陋,是因为它忘记了如何阐明美最终是一座建筑的必需品,就像一个正常运作的屋顶一样。我们已经失去了用来描述我们痛苦的词汇。
现代世界的丑陋在于第二个智力上的错误:没有人知道建筑中什么是有吸引力的。
在前现代世界,人们普遍认为,关于是什么让建筑物令人愉悦,有精确的规则。在西方,这些规则被编纂成一种被称为“古典主义”的教条。由希腊人创造并由罗马人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定义了1,500多年来优雅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从爱丁堡到查尔斯顿,从波尔多到旧金山,西方各地都出现了可辨认的古典形式。
然后,渐渐地,双方爆发了一定程度的礼貌分歧。一些人开始提出其他风格的理由,例如从中世纪开始的哥特式建筑方式。其他人则提出支持伊斯兰建筑,或者支持中式、阿尔卑斯山或泰式风格的论点。各式各样的建筑开始出现在西方各地,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如何建造才是最好的辩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辩论以一种智力上极其尊重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这恰好引发了一些非常糟糕的实际后果。根据法令,在视觉品味方面,没有人能真正赢得这场争论。所有的品味都值得倾听。没有客观标准这回事。建筑的吸引力显然是一个多方面的主观现象。
这再一次让房地产开发商耳目一新。突然间,没有人被允许用“丑陋”来形容一座建筑。毕竟,品味仅仅是主观的。你和你的朋友可能不喜欢一个新的选区,即使是民主党的大多数人也可能不喜欢它,但这只是个人的判断,不是什么重要的法令,你可能需要听一听。
城市变得越来越丑,但没有人被允许说有“丑”这样的东西。毕竟,品味不就是非常非常私人的事情吗?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很清楚,建筑师最不需要的就是“独创性”--就像一个木匠或砖匠不需要独创性一样。建筑师的工作只是把一座建筑设计成与一个地区的所有其他建筑大致相同的样子,并礼貌而准时地完成;当然不是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或者引起轰动。因此,大多数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都非常相似。你不能真的说出谁做了什么建筑,这无关紧要(就像谁烤了一条面包也不是特别重要一样)。建筑是美丽的、客观的、重复的。
但在20世纪初,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浮出水面:建筑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着独特的愿景,需要用所有的想象力来表达,以安抚不安的创造精神。要求一位建筑师与其他人融为一体,就像要求诗人打出税号一样令人窒息。
对于某些建筑师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解放,但整个社会为这个创造性的释放付出了巨大的集体代价。突然间,建筑师们开始竞相创造最奇特、最令人震惊的形式--似乎是为了证明它们的独特性和价值。众所周知,一个人不能通过建造庄严低调的建筑来成名,而要靠愤怒和奇特。
这个世界忘记了“创意”在建筑中是不受欢迎的,就像它在面包店或脑外科手术中一样不受欢迎。人们在这里不是为了不断的震惊和惊讶,而是想要可预测的规则和和谐。我们失去了说,我们真正渴望的是看起来有点像他们一直以来的样子的建筑;人们永远不必怀疑是谁做的建筑。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生活在组织严密、排列整齐的街道和广场上--不是因为有人认为这里特别有吸引力(尽管确实如此),而是因为它很方便。当你不得不徒步出行,或者最多骑马出行时,把东西放在一起是值得的。此外,它更安全,因为入侵者随时可能发动攻击,用城墙包围你的城镇是至关重要的,这进一步推动了一切东西在里面安排得井井有条,比如一个紧凑的餐具抽屉或工具箱。
但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随着20世纪20年代汽车的普及,使用空间的压力干净利落地消失了。人们现在可以懒洋洋地躺在地上,也可以懒洋洋地躺在地上。高速公路可以在塔楼、小片灌木丛和零星的仓库之间蜿蜒行驶。我们当中那些紧张而精确的人喜欢东西整齐地排列,当照片稍微歪斜或刀叉与盘子的距离不相等时,他们会感到不安,他们变得越来越悲伤。
建筑师曾经别无选择,只能用自然和当地的材料建造。这有两个好处。首先,一般说来,用天然材料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建造一座丑陋的石头或木制建筑;一开始很难在它们里面建造很高的建筑,所以你的有碍观瞻肯定会有一定的谦逊。木材和石灰石、花岗岩或大理石固有的有机美减弱了形式层面上的任何错误。
其次,如果耶路撒冷建在一种石头上,而巴斯建在另一种石头上,如果它们看起来不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定位,并将我们与特定的地方联系起来。但现代性引入了玻璃和钢铁,可以很快形成宏伟的大型建筑,这表明,拥有当地的建筑将像拥有当地的电话或自行车设计一样愚蠢。这场争论再次忘记了人性。当我们说一座建筑看起来“可能在任何地方”时,我们不是在赞扬它的全球野心,我们是在表达对一座建筑的渴望,它能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在哪里。
世界变得如此丑陋,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足够有力的论证,对视觉领域的关注不是精英的消遣:它属于精神健康。最尖锐的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决定了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一个退化的环境中,无论我们的物质生活多么安全和丰富,我们的精神都会沉沦。我们从我们周围的建筑“谈论”中得到暗示。如果他们谈到优雅和魅力,善良和光明,我们的心情会很愉快,如果他们看起来像是威胁和恐吓我们,我们会感到羞辱和恐惧。现代性几乎不尊重我们的脆弱。它想象过,只要屋顶不漏水,我们就可以住在丑陋无比的楼房里,而不会失去生存的意志。
谦卑地说,我们不能把我们建造的丑陋世界归咎于贫困。过去,金钱最终会让所有人都拥有美丽,这曾是一种令人放心的假设。但现代性给我们上了更黑暗的一课:最终造就好建筑的是明智的想法,我们建造一个丑陋的世界是出于愚蠢,而不是缺乏资源。
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我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本愚蠢的书或一首歌可以放在书架上,不会打扰任何人。一座哑巴建筑将会污损地球,让所有必须看它300年的人心烦意乱。仅凭这一点,建筑就是最重要的艺术,而且(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我们在学校里从来没有学过任何东西。
由于我们缺乏教育,我们不追究我们的管理班级的责任。我们不知道如何在政治上表达我们对丑陋的厌恶。我们被教导如何说我们想要一个更富裕的世界,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甚至一个更绿色的世界。我们仍在为如何叫嚣我们也迫切想要一个更美丽的世界而步履蹒跚。
现代性的承诺是让所有人都能廉价获得最重要的东西:可爱的食物或衣服、假期或药品不再只是富人的专利。工业技术将为每个人带来质量。但矛盾的是,由于我们无法清晰地思考,我们都渴望的一个关键因素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排他性。我们唯一不能批量生产的东西就是漂亮的建筑。
因此,那里漂亮的建筑,其中大部分建于1900年之前,在游客的重压下被严重超额认购并倒塌-剩下的少数几条令人愉快的街道比贵族时代鼎盛时期的任何时候都要昂贵。我们让舒适大众化,我们让美变得令人震惊地排外。挑战在于记住我们对美的渴望--并与阻碍我们行动的力量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