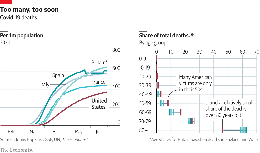为什么美国军方通常惩罚不当行为,而警方经常团结一致
许多美国军方成员公开否认特朗普总统赦免爱德华·加拉格尔(Edward Gallagher)的决定,这名前海豹突击队突击队成员因2017年在伊拉克杀害一名十几岁的囚犯而被判有罪。
从应征士兵到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加拉格尔被指控犯下的战争罪几乎在整个指挥链上都受到了一致的谴责。事实上,是加拉格尔的海豹突击队同事报告了这位前突击队成员的行动。
这种坚持要让其他服役人员为不良行为负责的态度,使军队与警察截然不同。
当警方被发现在逮捕期间杀死了一名手无寸铁的嫌疑人或过度使用武力时,警方通常会为这些行为进行辩护。根据1998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项研究,举报不当行为的警察通常被排斥为“老鼠”,并被拒绝晋升。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所谓的“蓝色沉默墙”--拒绝“告发”其他警官--是当今美国警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然而,士兵和警察每天都为他们的团队冒着生命危险。那么,如何解释这两支军队对不良行为的不同态度呢?
作为一名军事律师和学者,我研究了美国军事伦理的这一独特方面。
美国军事文化强调组织忠诚,而不是个人忠诚。当加拉格尔的海豹突击队同事报告他时,他们正在做海豹突击队被教导要做的事情:他们把机构的利益放在个人之前。
例如,众所周知,海军陆战队的自豪感来自于成为这个备受尊敬的部队的一部分。与其他海军陆战队的个人关系是次要的。
对个人不当行为的责任写入了美国军事法。根据“统一军事司法法典”,不能仅仅因为上级命令实施犯罪行为就避免犯罪行为的责任。只有合法的命令才能被执行。
“士兵是推理代理人,”一家军事法庭在1991年的“美国诉金德案”(U.S.v.Kinder)中解释道,在该案中,一名杀害平民的士兵被判谋杀罪,理由是他的上级这样做的命令显然是非法的,应该得到报告。
“要求一名士兵按照上级军官的吩咐去做,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谬论,”裁决的结论是指的是二战后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
当然,并不是每个士兵都遵守规则。美国军方掩盖了暴行。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包括1968年越南美莱大屠杀,在那次屠杀中,妇女和儿童被杀害。2003年,美国士兵严重虐待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在押人员。
但根深蒂固的军事道德通常会让军人对那种在警察部门掀起“蓝色沉默墙”的团体抱有戒心。
警探弗兰克·塞皮科使蓝墙的威力声名狼藉。在20世纪60年代为纽约警察局工作时,Serpico观察到他的同事们正在进行敲诈勒索行动,并为了好玩而拳打脚踢嫌疑人。当他揭露腐败时,他在同事们精心策划的设置中脸部中弹。
正如前巴尔的摩侦探乔·克里斯托(Joe Crystal)在2011年了解到的那样,这种道德在今天仍然存在。克里斯托是巴尔的摩警察局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在告诉他的上级,一名同事残忍地殴打了一名戴着手铐的嫌疑人后,他被降职、威胁和骚扰,直到他辞职。
“如果你告密,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根据克里斯特尔2011年对司法部提起的诉讼,他被告知未能保护他免受报复。
研究显示,警方不愿举报同事的原因是警察暴行事件的政治化,以及警方普遍认为,执法部门以外的人都不了解他们的危险工作。警察监督员发现,警察对被平民和公职人员评判感到沮丧,他们不会面临生死攸关的决定,当事情出错时,警察往往会团结一致。
军方也对政治干预军事事务持谨慎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它认真对待内部正义的原因。
国防部是唯一被允许运行自己的内部刑事司法系统的政府组织-这是一项既显着又脆弱的特权。
民事司法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对军方的司法系统持怀疑态度。法院过去常常担心正当程序,特别是军事指挥官不正当影响审判结果的能力。1969年,最高法院严格限制军事法庭的管辖权。
最高法院在“卡拉汉诉帕克案”中写道:“军事法庭作为一个机构,在处理宪法的微妙之处时出奇地无能。”
这项裁决将军事司法系统限制在处理纯粹的军事违法行为上,比如放弃他们的职位或行为不服从。像谋杀和强奸这样的严重指控必须在民事法庭受审。
在国会和美国律师协会进行了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加强军队的正当程序之后,最高法院于1987年恢复了军事法庭的管辖权。
今天,军事司法程序应该不受政治干预,即使是总司令也是如此。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支持这位前突击队成员,将加拉格尔的军事法庭变成了媒体的奇观,几乎可以肯定,他影响了审判的结果。加拉赫除了一项指控外,所有罪名都被无罪释放,并被判处有期徒刑。
总统还惩罚了负责加拉格尔军事法庭审判的检察官,吊销了他们的服役奖章。
当我是加州国民警卫队的军事司法部长时,我审判了几十个军事法庭,判定士兵犯有盗窃罪、殴打罪和强奸罪。
我通常可以让士兵们对我坦诚相待,即使说出真相意味着揭露朋友或上级的渎职行为。他们对军队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有信心,我觉得--一种理解,即如果他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就会安全。
在后加拉格尔时代,这仍然是真的吗?或者,一堵“伪装的沉默墙”会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