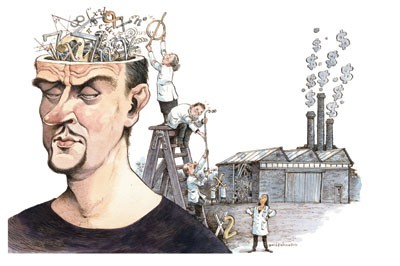数学的意外影响
彼得·罗利特(Peter Rowlett)介绍了7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说明理论工作可能会导致实际应用,但它不能被强迫,它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读过一个笑话,讲的是有人发明了电插头,不得不等待插座的发明才能把它插进去。谁会在不知道用途的情况下发明如此有用的东西呢?数学经常表现出这种惊人的品质。在试图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时,研究人员经常发现,他们需要的工具是数学家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前开发出来的,他们没有前景,也不关心适用性。工具箱是巨大的,因为,一旦一个数学结果被证明令学科满意,它就不需要根据新的证据重新评估或反驳,除非它包含错误。如果这对阿基米德是正确的,那么今天也是如此。
数学家开发出其他人看不到的主题,或者将想法推向抽象,远远超出了其他人会停下来的地方。一边喝茶,一边与一位同事聊天,讨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对美术馆的每个点进行观察所需的最少固定警卫人数,我概述了基本的数学知识,指出它只适用于二维平面图,在三维情况下会崩溃,比如美术馆有夹层的时候。“啊,”他说,“但如果我们搬到5D,我们就能适应……”这种没有明显方向或目的的扩展和抽象是该学科的基础。适用性不是我们工作的原因,而大量不适用的东西有助于我们的学科的美丽和壮丽。
近年来,研究人员一直面临压力,要求他们在开展工作之前预测工作的影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09年10月22日)援引时任英国研究理事会主席艾伦·索普(Alan Thorpe)的话说:“我们必须向纳税人证明,这是一项投资,我们确实希望研究人员考虑他们的工作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同样关注研究提案的更广泛影响(见“自然”杂志,465,416-418;2010)。然而,预测影响是非常有问题的。最新的“国际数学科学评论”(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2010年)对英国研究的质量和影响进行了独立评估,该报告警告说,即使是最具理论性的数学思想“也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有用或具有启发性,有时是在它们出现几十年后”。
没有办法预先保证纯数学以后会有什么应用。我们只能让好奇心和抽象化的过程发生,让数学家痴迷地把结果带到他们的逻辑极端,把相关性远远抛在脑后,等着看哪些话题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否则,当未来的挑战到来时,我们手头就不会有合适的看似毫无意义的数学题了。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向英国数学史学会(包括我自己)询问了一些关于数学意外影响(除了现代密码学中的数论,或者操作计算机的数学在建造计算机时就已经存在,或者虚数成为飞行飞机的复杂计算所必需的)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是7条;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bshm.org.。彼得·罗利特。
著名的是,爱尔兰数学家威廉·罗文·汉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在1843年10月16日走过都柏林布劳汉姆桥(Brougham Bridge)时萌生了四元数的想法。他把方程式刻在桥的石制品上,以此纪念这一时刻。汉密尔顿一直在寻找一种将复数系统扩展到三维的方法:他对这座桥的见解是,有必要改为移动到四维才能获得一致的数字系统。复数采用a+ib的形式,其中a和b是实数,i是−1的平方根,而四元数具有a+bi+cj+dk的形式,其中规则是i2=j2=k2=ijk=−1。
汉密尔顿在他的余生中一直在推广四元数的使用,因为数学本身就很优雅,对解决几何、力学和光学中的问题也很有用。他死后,火炬由爱丁堡大学自然哲学教授彼得·格思里·泰特(Peter Guslee Tait,1831-1901)传递。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Lord Kelvin)在谈到泰特时写道:“我们为四元数进行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战争。”汤姆森同意泰特的观点,他们将在他们重要的合著“自然哲学论文集”(1867年)中使用四元数,只要它们有用。然而,他们完全没有出现在最后的手稿中,这表明汤姆森并没有被说服相信他们的价值。
到19世纪末,矢量微积分已经使四元数黯然失色,20世纪的数学家们普遍追随开尔文而不是泰特,认为四元数是一个美丽但可悲的不切实际的历史注脚。
因此,当一位教授电脑游戏开发的同事问学生应该选择哪个数学模块来学习四元数时,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问题。事实证明,它们对于涉及三维旋转的计算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们比矩阵方法有各种优势。这使得它们在机器人和计算机视觉以及更快的图形编程中不可或缺。
如果泰特最终赢得了与开尔文的战争,他无疑会很高兴。150年后,汉密尔顿对他的发现将带来巨大好处的期望在游戏行业实现了,据估计,这一行业在全球的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
1907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等价原理是广义相对论发展的关键一步。他的观点认为,加速度的影响与均匀引力场的影响是无法区分的,这取决于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之间的等价性。爱因斯坦的基本见解是,重力以时空曲率的形式表现出来;重力不再被视为一种力。物质如何弯曲周围的时空由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式来表示。他在1915年发表了他的通论;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
1854年,伯恩哈德·里曼(Bernhard Riemann)在他精彩的康复讲座中,通过发明流形的概念,介绍了现代微分几何的主要思想-n维空间、度量和曲率,以及曲率控制空间几何性质的方式。流形本质上是形状的推广,比如球面或环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做微积分。黎曼远远超出了欧几里得和非欧几里德几何的概念框架。他预见到他的多面体可能是物理世界的模型。
为将黎曼几何学应用于物理学而开发的工具最初是格里加里奥·里奇-柯巴斯特罗(Gregario Ricci-Curbastro)的工作,始于1892年,后来与他的学生图利奥·利维-西维塔(Tullio Levi-Civita)一起扩展。1912年,爱因斯坦求助于他的朋友、数学家马塞尔·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利用这一张量微积分,用数学形式阐明了他深刻的物理洞察力。他使用了四个维度的黎曼流形:三个用于空间,一个用于时间(空间-时间)。
当时的习俗是假设宇宙是静态的。但爱因斯坦很快发现,当他的场方程式应用于整个宇宙时,没有任何静态解。1917年,为了使静态宇宙成为可能,爱因斯坦在他原来的场方程式中加入了宇宙常数。亚历克桑德·弗里德曼(Aleksander Friedmann)在1922年对爱因斯坦在宇宙学背景下的场方程式的研究中提出了相信宇宙爆炸起源的理由。爱因斯坦不情愿地接受了宇宙扩张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在1931年删除了这个常数,称它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1998年,数学突然出现在新闻中。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的托马斯·黑尔斯(Thomas Hales)证明了开普勒猜想,表明蔬菜水果商堆放橙子的方式是包装球体的最有效方式。自1611年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一位蔬菜水果店主在电视上说:“我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和纳税人的钱。”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头脑中与那个蔬菜水果商争论:今天,球形包装的数学使现代通信成为可能,成为信道编码和纠错码研究的核心。
1611年,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提出蔬菜水果店的堆放效率最高,但他无法证明这一点。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即使是最简单的包装圆圈的方法也只是在1940年由拉兹洛·费斯·托斯证明的。同样在17世纪,艾萨克·牛顿和大卫·格雷戈里就接吻问题进行了争论:有多少球体可以接触到没有重叠的给定球体?在二维情况下,很容易证明答案是6。牛顿认为在三维情况下,12是最大值。的确如此,但直到1953年库尔特·舒特和巴特尔·范德沃登才给出了证明。
奥列格·穆辛(Oleg Musin)在2003年证实,4维空间的接吻次数为24次。在5个维度中,我们只能说它位于40到44之间。然而,我们知道8个维度的答案是240,早在1979年,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德鲁·奥德利兹科和尼尔·斯隆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样的论文有一个更奇怪的结果:24个维度的答案是196560。这些证明比三维的结果更简单,并且与两个密度令人难以置信的球体堆积有关,它们分别称为8维的E8格子和24维的水蛭格子。
这一切都很神奇,但它有用吗?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戈登·朗(Gordon Lang)的工程师认为是这样的。朗正在为调制解调器设计系统,并忙于收集他能找到的所有数学知识。
他需要通过嘈杂的信道(如电话线)发送信号。自然的方式是为信号选择一组音调。但是接收到的声音可能与发送的声音不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一列数字来描述声音。然后很容易找出哪些可能已经发送的信号最接近接收到的信号。然后,信号可以被认为是球体,有噪声的回旋余地。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发送的信息,这些球体必须包装得尽可能紧密。
在20世纪70年代,朗使用E8封装开发了一种具有8维信号的调制解调器。这有助于打开互联网,因为数据可以通过电话发送,而不是依赖专门设计的电缆。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兴奋。曾帮助朗理解数学的唐纳德·科克塞特(Donald Coxeter)表示,他“对自己美丽的理论被以这种方式玷污感到震惊”。
1992年,两位物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简单的装置,可以将分子水平上的热波动转化为定向运动:布朗棘轮。它由一个处于闪光不对称场中的粒子组成。巴黎工业物理与化学学院的Armand Ajdari和巴黎居里研究所的Jacques Prost解释说,打开和关闭电场会诱导定向运动。
1996年,我们中的一个人(J.P.)发现了帕隆多悖论,该悖论从数学上捕捉到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并将其翻译成一种更简单、更宽泛的语言:博彩游戏。在悖论中,赌徒在两个博弈之间交替,从长远来看,这两个博弈都会导致预期的损失。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在它们之间切换,一个人可以产生一个预期结果是积极的游戏。帕隆多效应这个术语现在用来指两个组合事件的结果与单个事件的结果非常不同。
目前正在研究帕隆多效应的一些应用,其中混沌动力学可以结合起来产生非混沌行为。例如,这种效应可以用来对病毒性疾病爆发中的人口动态进行建模,并提供了降低股价波动风险的前景。此外,它在理查德·阿姆斯特朗(Richard Armstrong)2006年的小说“上帝不会投掷骰子:神曲”的情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16世纪,吉罗拉莫·卡达诺是一位数学家和强迫症赌徒。对他来说,可悲的是,他把继承和赚取的大部分钱都挥霍光了。对于现代精算学来说,幸运的是,他在16世纪中期写下了被认为是现代概率理论的第一部著作--Liber de Ludo aleae,最终在1663年出版了一本合集。
在这一理论创立大约一个世纪后,另一位赌徒谢瓦利埃·德·梅雷(Chvalier de Méré)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一直在提供一种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打赌他可以在四轮骰子中掷出六分之六,并且在这场游戏中做得很好。他以一种似乎明智的方式改变了比赛,打赌他可以在24轮中用两个骰子投出双6。他计算了两场比赛的获胜几率相等,但发现从长远来看,他在玩第二场比赛时赔钱了。他很困惑,向他的朋友布莱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寻求解释。帕斯卡在1654年写信给皮埃尔·德·费尔马(Pierre De Fermat)。随后的通信为概率论奠定了基础,当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得知这一结果时,他写下了第一部关于概率的出版著作--“de Ratiociniis in Ludo Aleae”(出版于1657年)。
在17世纪后期,雅各布·伯努利认识到概率论可以比机会游戏更广泛地应用。他写了“阿斯猜想”(他死后,于1713年出版),巩固和扩展了卡达诺、费马、帕斯卡和惠更斯的概率工作。伯努利建立在卡达诺发现的基础上,即只要掷出足够多的公平的六面骰子,我们预计每个结果都会出现大约六分之一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把一个骰子掷六次,我们就不应该指望每个结果只出现一次。伯努利给出了大数定律的证明,即样本越大,样本特征与母体的特征越接近。
保险公司一直在限制他们销售的保单数量。由于保单是基于概率的,每售出一份保单似乎都会招致额外的风险,人们担心,这种风险的累积效应可能会毁了一家公司。从18世纪开始,公司开始销售尽可能多的保单,因为正如伯努利大数定律所显示的那样,交易量越大,他们的预测就越有可能是准确的。
1735年,当伦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向哥尼斯堡的人们证明,他们不可能在一次旅行中穿越他们所有的七座桥时,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一种距离无关紧要的数学。他的解决方案只依赖于了解桥梁的相对布置,而不是它们有多长或陆块有多大。1847年,约翰·本尼迪克特·列宁(Johann Benedict Listing)终于创造了拓扑学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个新领域,在接下来的150年左右的时间里,数学家们一直在努力理解它的公理的含义。
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拓扑学被当作一种智力挑战来追求,并不指望它是有用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形状和尺寸很重要:一个甜甜圈和一个咖啡杯不一样。谁会在乎抽象的11维空间中的5维洞,或者曲面是单面还是双面呢?即使是拓扑学中听起来很实用的部分,如纽结理论,它起源于试图理解原子结构,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被认为是无用的。
在20世纪90年代,拓扑学的应用突然开始出现。起初很慢,但到现在为止势头越来越大,似乎很少有领域不使用拓扑。生物学家学习纽结理论来理解DNA。计算机科学家正在使用辫子-沿着同一方向运行的交织的材料链-来建造量子计算机,而走廊里的同事们则使用同样的理论来让机器人移动。工程师们使用单面莫比乌斯带来制造更高效的传送带。医生依靠同源理论做脑部扫描,宇宙学家用它来理解星系是如何形成的。移动电话公司使用拓扑结构来识别网络覆盖中的漏洞;手机本身使用拓扑结构来分析他们拍摄的照片。
正是因为拓扑没有距离测量,所以它才如此强大。同样的定理也适用于任何打结的DNA,不管它有多长或来自什么动物。我们不需要为大脑大小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脑部扫描仪。当手机的全球定位系统数据不可靠时,拓扑仍然可以保证手机接收到信号。除非我们能建立一个不受噪音影响的健壮系统,否则量子计算是行不通的,所以辫子是储存信息的完美选择,因为只要你摆动它们,它们就不会改变。下一步拓扑将出现在哪里?
伦纳德·欧拉(Leonard Euler)和其他人在18世纪用一系列正弦和余弦函数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在振动弦的研究和天体力学中。但正是约瑟夫·傅立叶(Joseph Fourier)在19世纪初认识到了这些级数在热传导中的巨大实用价值,并开始发展出一套普遍的理论。此后,发现傅立叶级数有用的领域迅速增加,包括声学、光学和电路。如今,傅立叶方法为大部分科学和工程以及许多现代计算技术奠定了基础。
然而,十九世纪早期的数学不足以发展傅立叶的思想,而出现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对当时的许多伟大思想提出了挑战。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新的数学。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勒琼·狄利克莱特(Gustav Lejeune Dirichlet)给出了第一个清晰而有用的函数定义,伯恩哈德·里曼(Bernhard Riemann)在19世纪50年代和亨利·勒贝格(Henri Lebesgue)在20世纪创建了严格的积分理论。无穷级数收敛的含义被证明是一种特别狡猾的动物,但这一点逐渐被分别在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工作的奥古斯丁-路易斯·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和卡尔·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等理论家驯服。在19世纪70年代,乔治·坎托向抽象集合论迈出的第一步是通过分析两个具有相同傅立叶级数的函数如何不同而产生的。
这条数学轨迹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形成的最高成就是希尔伯特空间的概念。这是以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的名字命名的,它是一组元素,可以根据一套精确的规则进行相加和相乘,具有特殊的性质,可以回答傅里叶级数提出的许多棘手问题。在这里,数学的力量在于抽象的程度,而我们似乎已经把现实世界抛在了脑后。
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赫尔曼·韦尔(Hermann Weyl)、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和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认识到这个概念是量子力学的基石,因为量子系统的可能状态就是这样一个希尔伯特空间的元素。可以说,量子力学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学理论。没有它,我们的许多现代技术-激光、计算机、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