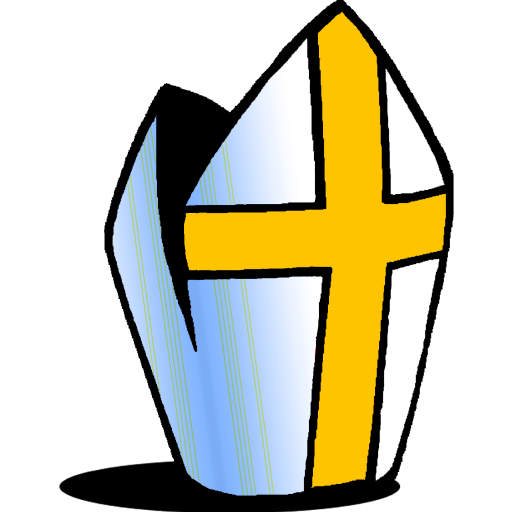7月4日
[我已经转发了很多次了,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所在。]。
1992年炎热的夏天,我为洛杉矶的联邦法官罗纳德·S·W·卢(Ronald S.W.Lew)工作。7月的一天早晨,他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说,把你的外套拿来。我有点担心我会被领出去,于是抓起我的夹克衫,跟着他走出了房间,走到了走廊。我看到他已经在那里召集了他的两个法律助理和另一个夏日外出人员。我们交换了疑惑的目光,跟着他进入了老斯普林街法院的装饰艺术法官的电梯,然后进入了洞穴般的司法停车场。他把我们塞进他那辆一尘不染的凯迪拉克里,一句话也没说就开出了车库。
不到十分钟,我们就来到了洛杉矶最大的VFW哨所之一。成群结队的人穿着周日最好的衣服,鱼贯而入大楼。很明显,他们是一家人--抱着婴儿,跑来跑去的小孩子,年轻和中年的父母。在每个家庭群体中都有一个男人--一个穿着军装的老人,许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弯腰,但他们都有着属于VFW大厅的男人的气度。他们都是菲律宾人,我稍后会知道的。他们的子孙都是菲律宾裔美国人;他们不是。现在还不行。
卢法官是美国大陆第一位华裔地区法院法官,他从后备箱里抓起长袍,轻快地走进VFW大厅,身后跟着他的外貌和书记员。我们在门厅停了下来,他把我们介绍给一些VFW官员,他们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穿上长袍,从一扇门的窗户往外看,看到数百人坐在大厅里,兴奋地交谈,孩子们挥舞着小美国国旗和横幅。VFW的一名官员在他耳边低声说,他点点头,说我会先见到他们。办事员和我的同事们正在和一些移民局官员聊天,所以他招手叫我。我跟着他穿过一扇门,来到一间小接待室。
在那里,在一间装饰华丽的昏暗房间里,我们发现了八位老人。这些太虚弱了,站不起来。三个人躺在担架上,几个人坐在轮椅上,两个人有氧气罐。其中一个人的袖子是空的,而不是右臂。几个亲戚喜气洋洋地站在每个人旁边。卢法官一个接一个地向他们宣读入籍誓词--靠近他们,有时会触摸他们的手,大声说话,这样他们就能听到他的话,就像执行极端仪式的牧师一样。他们微笑着,握住他的手,带着明显的自豪,尽可能大声地宣誓。一些人哭了。我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其中一人说,不是带着愤怒,而是带着梦想成真的语气说,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哦,他们是如何等待的。这些人出生在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响应美国的号召,为我们而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要求菲律宾人参战,向他们承诺美国公民身份和退伍军人福利作为回报。20万人参加了战斗。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他们经受住了日本占领下的残酷条件,打了一场英勇的游击战,在某些情况下还在巴丹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
1946年,国会违背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承诺。为我们和他们的家人战斗的菲律宾士兵没有得到承诺的公民身份,更不用说福利了。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来到了这里,他们的孩子出生时就是美国公民,有些人甚至通过任何移民都可以获得的程序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其他许多人,记住了这个承诺,要求遵守它。然后他们就等着。
他们等了44年,直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直到1990年,国会才最终解决了我们荣誉上的这一特殊污点,并授予他们公民身份。(他们承诺的福利甚至直到2008年才付诸表决,当时我看到的大多数幸福的人都去世了。)
所以才有了这个七月的入籍仪式。在卢法官将那些病得太重或身体虚弱而无法站在主仪式上的退伍军人归化后,他很快登上了主厅的舞台。一阵疯狂而欢乐的寂静降临,数十名退伍军人站起来宣誓。许多人哭了。我一直有东西进我那该死的眼睛里。当卢法官宣布他们为公民时,他们的家人欢呼着拥抱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孩子们像疯子一样挥舞着小旗帜。
我有机会向一些家庭表示祝贺,并听到他们向卢法官致意。我听到了非常满意的表情。我听到更多关于他们等了多久的评论。但在这一天,我没有听到苦涩的声音。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痛苦,也许在其他日子里,他们会沉迷于此。在这一天,他们终于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在没有忘记他们所遭受的错误的情况下,他们相信一个更多地是错误的总和的美国。在没有忘记40多年的不公正的情况下,他们相信一个有潜力超越其不公正的美国。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原谅了1946年背叛他们、玷污他们服务的国会,或者原谅了后来的国会和政府软弱或漠不关心地纠正这一错误。我想我不能指望他们这样做。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宽恕了美国的罪孽,他们都爱着罪人,显然,他们为成为她的公民而感到无比自豪。
我非常感谢卢法官带我参加了那个仪式,并认为我很荣幸能看到它。每到七月的第四个月,我都会想起这件事,而且比这还要频繁。它提醒我,人们在这个国家的手中经历了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不公正,但他们对此感到自豪,并决心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被林肯所说的我们本性中的更好的天使所感动,他们相信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共同想法,而不是放弃纠正错误的斗争。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