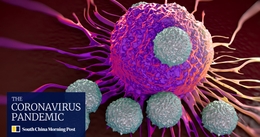冠状病毒正在攻击纳瓦霍人,“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人类,让它可以入侵。”
当一个家庭成员去世时,我们迪内人(西班牙征服者称之为纳瓦霍人)会向我们当地的广播电台发出通知,让社区里的每个人都能知道。通常情况下,宣读死亡通知-死者的名字,他们的年龄,他们住在哪里,以及他们的母系和父系氏族的名字-不超过五分钟。过去很少听到年轻人死亡的消息。但在过去的一周里,我在KGAK AM 1330电台收听了45分钟的死亡通知。死者的年龄从26岁到89岁不等,大多数死者都是30多岁、40多岁或50多岁。
我很震惊。3月份,通过亚利桑那州的拿撒勒基督教复兴,病毒进入了我们的社区。他们从纳瓦霍民族各地带来了满载人员的货车和大巴来参加集会,然后所有这些货车和大巴都把他们和病毒一起送回了各自的社区。由于医疗设施没有准备好,有人立即死亡。已经有300多名纳瓦霍人死于新冠肺炎,而且这种疾病还在蔓延。
我是一个Diné讲故事的人,也是传统的守护者。我一个人住在奇奇塔的Hogan,一座传统的八角形木屋,意思是“橡树生长的地方”,以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甘贝尔橡树命名。该社区的正式名称为Vanderwagen,位于新墨西哥州盖洛普以南23英里处。大流行于4月下旬到达该地区。5月1日,新墨西哥州州长启动了骚乱法案,封锁了盖洛普的所有出口,以阻止病毒的传播,只有居民才能进入。封锁延长到5月11日。第一周并没有那么糟糕,但后来我们开始没有食物和水了。
范德瓦根部分地区的地下水自然会受到砷和铀的污染;无论如何,我们中几乎没有人有钱打一口井。通常,我的兄弟和侄子用250加仑的水箱运水,水箱在皮卡车的后部。在盖洛普,他们有一口马力很大的油井;你付5美元硬币,把软管放进油箱,然后加满油。你把它拖回家,倒进你的蓄水池,你的房子里就有水了。没有盖洛普,人们开始缺水-即使我们被告知要经常洗手。
我的霍根有电,但没有自来水。我的兄弟们给我拿来了水,他们把水放在一个75加仑的桶里。我喝这些水,用它洗澡,但我也花5美元买了5加仑的水,以防我需要额外的水。我通常每天用一加仑的水,做任何事情--做饭、喝水和洗碗。我的曾祖母曾经说过,“不要习惯喝水,因为总有一天你会为它而战。”我已经学会了靠很少的钱生活。
我们的社区里有很多癌症,也许是因为铀。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健康问题,我认为这使得这种病毒在我们中间如此具有生命力。我们有很多糖尿病,因为我们吃得不好,还有很多心脏病。我们有酗酒。我们的自杀率很高。我们有你能想到的每一种社会弊病,而COVID已经使这些漏洞变得更加明显。我认为它是一只以我们为食的怪物-因为我们已经为它的入侵创造了完美的人类。
盖洛普重新开张几天后,我开车去那里寄信。每家快餐店-麦当劳、肯德基、温迪、汉堡王、熊猫快递、塔可钟,都位于一条街上-在免下车餐厅有很长很长的车在等着。这是在一个糖尿病发病率如此之高的社区。也许在他们社区的非常小的商店里没有任何食物可用,但我也认为这场流行病引发了许多通常隐藏的情绪反应。在去范德瓦根的高速公路上,有一家卖酒的便利店。停车场完全停满了,每个人都在买酒。有一种焦虑和恐慌的感觉,但我也认为很多纳瓦霍人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相处,因为没有真正好的、全面的、任何形式的精神实践来支撑他们。
COVID揭示了当你把一个民族从他们的根上赶走时会发生什么。以一个迪内青少年为例。她会穿纳瓦霍语,但她没有语言、文化或信仰体系告诉她做迪内意味着什么。她的祖母在五岁时被带到印度事务局(BIA)的寄宿学校,一直呆到18岁。在学校里,他们告诉她,她的文化和修行是魔鬼的,她需要彻底否认它们。她的语言无效:“你有纳瓦霍口音,你的英语必须说得更流利。”她母亲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我们的语言消失了,文化和传统习俗消失了。那也是打屁股和殴打进入迪内文化的时候。那些孩子在BIA学校忍受着那些可怕的纪律方式,这成了他们的弟子。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35年来,我一直试图告诉他们,你们来自美丽的文化。你来自哥伦布到达美洲时正在蓬勃发展的数百个部落中的一个;我们有一个可行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它是基于与这片土地捆绑在一起的精神实践而建立的。大约500年前,西班牙征服者顺着格兰德河进入北美寻找黄金。他们手持发现主义,这是教皇颁布的一份可怕的法律文件,批准对非基督教领土的殖民。然后在19世纪中期,开拓者从东海岸带着他们对命运的信仰,他们在道义上有权殖民这片土地。当他们的马车向西移动时,平原印第安人被迁出并保留了下来。当你的修行基于你所居住的土地,而你被赶出别人会称之为她的寺庙、清真寺、教堂或大教堂的地方时,那就是你的灵性首先受到攻击的地方。
我父亲那边的曾祖父被俘虏,并被带上了我们所说的通往萨姆纳堡的长途跋涉。最初,大约有1万名迪内被围捕,许多人在那次步行中死亡,这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具体取决于他们被带去的路线。由于内战,他们在萨姆纳堡被监禁了四年,并于1868年获释。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母亲那边的曾祖父从切利峡谷的基特·卡森上校手中逃脱,带着他的山羊向北旅行。就在我的曾祖母逃离西班牙奴隶制的时候,他回到了这个地区。奴隶制是由西班牙人引入这里的--这从来没有被提及过。出生在萨姆纳堡的孩子被带进西班牙家庭,成为奴隶。
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感染了西班牙流感,这是入侵我们社区的众多病毒之一。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我们不知道这会发生:我们没有钱,但我们有绵羊形式的财富。政府介入,在减持计划中宰杀了我们的羊。他们说羊在侵蚀土地,但我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羊让我们自给自足,他们不能允许这一点。我们在羊群周围修行。每次我们发展了自给自足和可行的修行,他们就毁了它。我母亲说,他们挖了很深的战壕,把羊群赶到一起,然后宰杀了它们。
20世纪40年代的一场肺结核疫情夺走了我母亲的父母。我的曾祖母是一名治疗师和草药医生,她把我的母亲藏起来,不让政府特工抓走迪内的孩子,把他们送到BIA寄宿学校。我的母亲成了一名牧场主,一位多产的织布工,一位会说这种语言的漂亮女人。她不太会说英语。她去世,享年96岁;我的曾祖母去世,享年104岁。现在,在我们奇奇达的社区里,已经没有传统的治疗师了,年龄最大的是我的曾祖母,她已经78岁了。我是唯一一个传统的迪内故事家。
既然我们在谈论美国的种族问题,我们也需要谈谈流离失所的美洲原住民部落。在纽约州北部有一个易洛魁人的保留地-总共21平方英里。易洛魁人最初生活在多少土地上?谁住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那宾夕法尼亚州呢?那么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所有州呢?你在占领谁的土地?亚伯拉罕·林肯在圣诞节后第二天下令屠杀38名达科他州人,就在他签署解放宣言的同一周;他们称他为诚实的亚伯。他们不谈论事物的黑暗面,我认为这就是COVID揭示的黑暗面。我们看到一名警察把全身重量放在一个黑人的脖子上。突然每个人都说,哇!我们进化到什么程度了?
在我看来,COVID在世界各地揭示了许多真相。如果我们对真理一无所知,它现在就会被揭示;如果我们忽视了真理,那么它现在就会被揭示。这个事实就是差距:健康、福祉和人类价值的差距。现在真相已经被揭露了,我们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