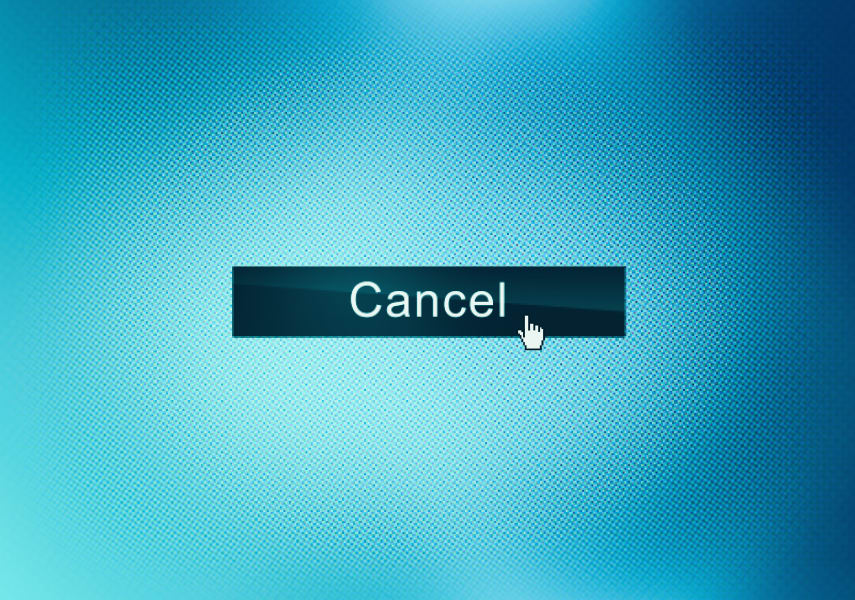如果不是“取消文化”,那是什么文化?
本文摘录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内容涉及哈珀的信,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未遂取消,以及上周发生的其他事件:
新革命要求他们下台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上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像乔姆斯基、斯泰纳姆,甚至平克这样的人都是在六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成熟起来的,这场运动塑造了几代人的学术界和流行文化。这些人是在节拍诗歌、反战游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和“毕业生”(The Graduate)等电影中长大的,他们用一个词概括了他们父母那一代人的抱负-“塑料”(Plastic Tics)-代表了这些新教育工作者不想要给学生的一切。
这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成长于一个赋予女性、男女同性恋者、黑人和棕色人赋权的时代,也是普遍的人类精神赋权的时代。早在1989年“交叉性”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之前,60后的自由主义者就已经了解到政治压迫和智力压制的交织本质。
60年代的骚动揭示了无知的习俗和学术正统观念之间的明显关系,前者把女性关在家里,后者把同性恋关在壁橱里,后者压制了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等人的研究,他们的工作将把从女性性高潮到双性恋的一切都带出了地牢。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博士因告诉“好父母”,他们“本能地想为孩子做什么”而出名,这比一个世纪以来那些告诉他们不要亲吻或抱孩子的无知育儿书籍(主要是由高资历的男性写的)要好。
从《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野兽》到比莉·霍利迪的《奇怪的水果》,那么多被禁的东西,都被证明是具有启发性的。当时席卷美国的革命的活跃原则是,一旦愚昧被征服,我们就可以自由地庆祝我们共同的人性。
这条信息成为伟大的艺术绝非偶然。从爵士乐和摇滚乐到抽象画和贡佐新闻,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爆炸性的惯例。各种背景的人都喜欢随着新音乐跳舞,或者嘲笑理查德·普赖尔(Richard Pryor)被禁的喜剧(同样,当海外持不同政见者对着“大师”和“玛格丽塔”的复制品咯咯笑时,苏联国家也出现了裂痕)。人们普遍渴望和平、爱情、宽恕和幽默,这让人们走到了一起。没有人需要被鞭子驱使去传递这个信息。人们与生俱来对它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在越南和伍德斯托克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它成为了文化霸权。
这与今天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能够通过制作甚至是方块的音乐来向全国其他地区兜售他们的信息,反动派也无法抗拒,那么觉醒的革命就会适得其反。它花了大部分时间构建一个令人费解的压迫词汇,并对那些要么不理解,要么不喜欢的平庸无产者怒不可遏。
它的其他主要特征似乎完全缺乏幽默感,对在壁橱里寻找骷髅的热情无穷无尽,对告密和体面委员会的热爱,对隐喻的恐惧(清醒时的文化是100%的字面意思),狂热的集体主义斥责(《房间里的书》是本周的《毁灭四个老人!》),以及对在非政治背景下上床的清教徒式的不信任。《觉醒版的色情》正在为英国《卫报》撰写一篇文章,内容是《射精》的摩天大楼是如何成为顺规性主导地位的象征。他们让青少年反性爱联盟看起来像齐柏林飞艇。
问题不是“取消文化”是否存在。问题是,如果不取消,这种文化会是什么?
本文节选自今日的订阅者专用帖子。要阅读整个帖子并完全访问档案,您可以订阅每月5美元或每年5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