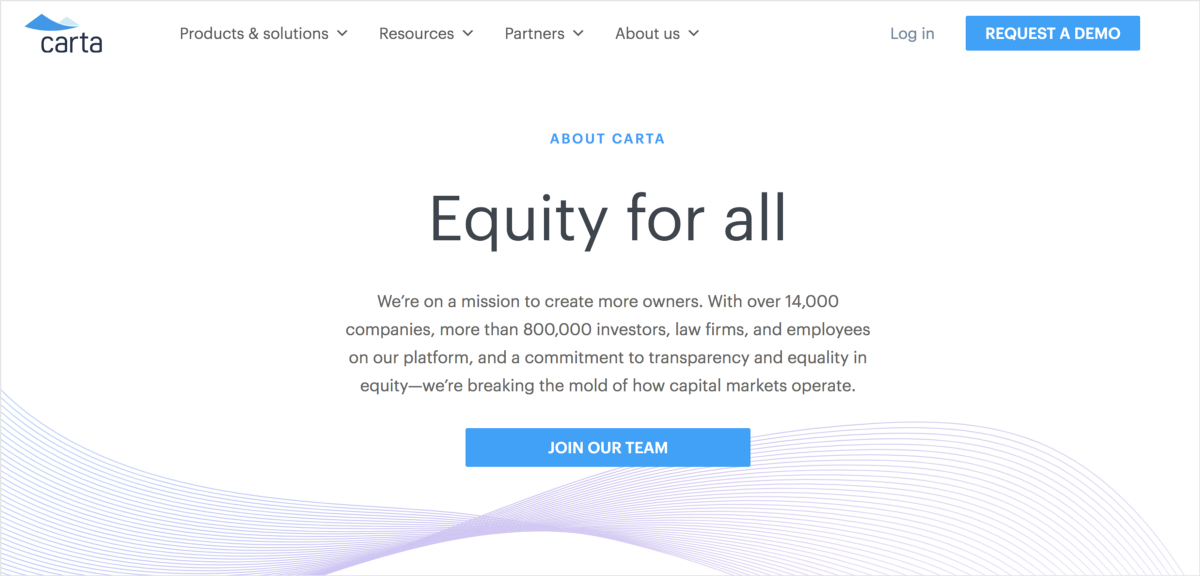人人平等?
今天,我起诉了卡塔。我的诉讼指控性别歧视、报复、违反公共政策的非法解雇、违反加州同工同酬法案,以及未能采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歧视、报复和骚扰。我的代理律师是Levy Vinick Burrell Hyams LLP的莎伦·维尼克(Sharon Vinick),她是一名律师,她的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捍卫女性权利,她是第一个起诉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未能为啦啦队员的工作支付公平薪酬的律师。
越来越清楚的是,“使命驱动”的硅谷公司往往建立在虚伪的谎言之上,但正如我在诉讼中声称的那样,Carta将这一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质疑我是否应该分享我的故事。如果别人的情况更糟,我应该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
我直言不讳地反对在Carta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是非法的、不公平的、破坏性的和深深的伤害。如果作为一名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很有挑战性,那么我无法想象对其他人来说是什么样子。我敢肯定情况一定更糟。可悲的是,我的故事并不少见,我真的很幸运能有足够的安全感来分享我的故事并提起诉讼。我认为,重要的是要阐明这些经验,以推动科技领域在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方面的积极变化。
Carta是一家制作股权管理软件的初创公司。它现在的估值超过30亿美元,已经从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光速风险投资公司(LightSpeed Ventures)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顶级投资者那里筹集了超过6亿美元。但Carta并不是简单地将自己定位为一家软件公司。Carta声明“致力于公平透明和平等”,并肩负着“创造更多所有者”的一般使命。事实上,Carta暗示这是一场整个全球革命的先兆。
在领导SaaS初创公司Asana、Astro和Ticketfly的市场部门期间,我熟悉股权薪酬及其好处-Asana被认为是今年计划上市的最有前途的公司之一;Astro被Slake收购;Ticketfly被Pandora和Eventbrite收购。作为这些早期团队的一员,我必须驾驭和理解股权的复杂性,并亲眼目睹了创业公司所有权的回报。因此,我不仅被Carta的产品和前景看好的增长潜力所驱使,而且我也相信他们让股权和所有权更加透明的目标,并为成为Carta的代言人而感到兴奋。这个机会似乎是我的经验和激情的完美结合。
我于2018年初接受了这一职位。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正如我在诉讼中声称的那样,我会意识到,Carta不仅只是另一家“男孩俱乐部”初创公司,而且它甚至没有在自己的墙内体现自己的理想。
以大多数标准衡量,我在Carta的任期都被认为是成功的:我建立了一个品类定义的品牌,帮助Carta的收入翻了两番,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了一支25人以上的营销团队。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吸引了三家公司过去的四名队友和Carta内部的四名内部调动,同时确保在营销中建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文化。正如我的诉讼所称,虽然Carta的营业额很高,但我的团队的自然减员是公司中最低的之一。
但最有意义的是,我领导了Carta揭露科技领域“股权差距”的努力。作为我的品牌营销战略的一部分,我制定了两份旗舰年度行业报告(2018年9月和2019年11月)。公平的股权做法现在已经成为该公司众所周知的目标。
我们与女性领导的投资团体#Angels合作,发布了我们的第一份性别平等差距报告,名为“差距表”(The Gap Table)。我们的报告揭露了风投支持的公司在股权薪酬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作为战略的一部分,我建议亨利透明地沟通Carta自己的股权差距状况,以及公司和行业中其他与性别相关的差距。因此,在2018年报告发布后,Carta的首席执行官亨利·沃德写道:
在硅谷,女性拥有9%的员工和创始人股权。其余91%为男性所有。女性占持股员工的35%,但只拥有20%的股权。它从一开始就开始了--女性创始人占所有创始人的13%,但她们持有6%的创始人股权。不幸的是,卡塔也不例外。我们的400名员工中只有30%是女性。我们的执行团队中有一名成员是女性。我们的七个董事会成员中没有一个是女性…。我很尴尬,因为我们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是高管团队中的“那个”女人,我支持--当时甚至相信--亨利希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的愿望。在这篇帖子中,亨利还宣布,他将在2018年底之前增加一名女性进入Carta的董事会:
加州即将要求上市公司至少有一名女性独立人士。我们将在今年年底前增加我们的第一位女性独立董事。我认为其他初创企业也应该效仿。对于任何全由男性组成的董事会,如果有五名或五名以上的董事,一名董事会成员应该下台,为女性独立董事腾出空间。
我为这份报告的积极影响以及它给予Carta的重要媒体和业界关注而感到自豪。第二年,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开始让股权差距问题成为主流,就像其他困扰科技业的问题一样:工资差距、极度多样化和歧视,仅举几例。
Carta的生意蒸蒸日上,我们的品牌获得了更多的认可。此后不久,我们又筹集了8000万美元的资金。
在宏观层面上,尽管有许多机会这样做,但Carta没有履行这一承诺,成为变革的一部分。正如我的诉讼细节所示,在我任职期间,近20人在高管团队中穿梭,但团队中没有额外的女性,也没有任何有色人种。尽管在2019年5月由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牵头的E系列融资3亿美元,但我们仍然没有增加一名女性进入董事会(但我们确实增加了马克·安德森)。据我所知,他们还没有增加一名女性进入董事会。
2018年夏末,Carta对其工资和股权薪酬进行了内部审计,审计时间定在差距表报告发布的时间。Carta发布了一篇关于这一过程的博客,并解释说,Carta的内部分析清楚地表明,公平没有得到适当的分配,女性获得的公平比男性少。这篇文章写道:“Carta有40%的女性接受了股权调整,而男性只有32%;总体而言,这影响了公司约35%的员工。”
至于我的薪酬,审计不仅发现我每年少付了5万美元,而且我最初的股权赠款是支付给可比员工(均为男性)的股权的三分之一。考虑到这一巨大的差异,我预计这些股票将具有追溯力,以反映我的开始日期。然而,这些股份的授予并没有回溯或加速,以说明我任职前六个月的情况。我要求回溯或加速这些选项的请求被拒绝。正如我在诉讼中声称的那样,我很失望地得知,Carta只在适合他们的情况下才关心公平。
在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公司的问题上,我并没有保持沉默。我想,作为一名高管,我可以引起内部变革。我认为Carta的内部实践会赶上我们在外部建立的声誉。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正如我在诉讼中指控的那样,我说的越多,我的高管同行对待我的情况就越糟糕。
例如,在我们的E系列推销组中,有一张幻灯片试图将单纯的工资收入等同于“奴隶制”,并包括了实际在田里干活的人的插图。我反复解释说,这是不恰当的、引发的和冒犯的。尽管我很担心,但为了我们的筹款努力或向公司进行内部演示,投球台从未改变过。我被我们的首席战略官Sumeet Gajri和Henry本人斥责,因为我试图在一个大型技术会议上移走这张幻灯片。在这样的经历和改善我们自己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多样性的整体平淡无奇的承诺之间,我终于泪流满面地谈到,我对高管场外缺乏多样性感到多么尴尬。
被忽略了,我仍然希望事情可以好转,但我越来越对宪章的情况感到不安和困惑。正如我在诉讼中声称的那样,我问亨利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晋升为首席营销官(甚至高级副总裁),因为我领导营销团队一年多了,已经是高管团队的一员,而且实际上是在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我已经看到两个相关工作经验明显较少的人被提升到C级职位。
在回答我的升职请求时,亨利告诉我,“你离升职”还差得远呢。他还评论了我的“风格”,并告诉我,虽然我是“公司里最聪明的五个人之一,并且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但我与高管团队中的其他成员相处得并不像他们那样融洽。”这一评论让人觉得特别值得怀疑,因为我是高管团队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
正如我在诉讼中指控的那样,高管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均为男性)似乎是根据他们可衡量的成就而获得晋升和头衔,而不是基于亨利对自己个性的主观看法。
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尽管如此,我仍然继续积极工作,以消除我的疑虑。正如我在诉讼中声称的那样,我直接向亨利和人力资源部表达了对薪酬差距、性别歧视文化以及公司内部缺乏多样性和包容性努力的担忧。这些投诉导致了额外的报复。
与此同时,我一直专注于建设我的团队,并教育整个行业有关公平股权做法的知识。作为我们2018年性别平等差距报告的后续行动,我希望我们不仅发布另一项数据研究,而且要用一个简单但强有力的信息开始一场运动:公平的公平就是桌上的赌注。我的愿景是创建一个完全独立的倡议-桌上竞猜-包括一个活动,将迅速启动一个由声音、专家和技术员工组成的新社区,团结在这个问题上。
进入11月,我和我的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推出2019年报告和Table Stakes活动。以任何可能的标准衡量,Table Stakes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数十家顶级商业出版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报道,到旧金山400多人的活动,聚集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声音,这次活动给了我希望,尽管我在Carta的经历,我们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
正如我在起诉书中所说,我的薪酬低于处境相似的男性,公平待遇低于处境相似的男性,当资历较差的男性被提拔时,我一再拒绝晋升,我的“风格”受到性别歧视和主观批评(尽管我表现出色),我对性别歧视的抱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敌意回应。
性别歧视和报复性虐待最终以亨利在一次一对一的会议上长篇大论地斥责我而告终,在那次会议上,他反复称我为“混蛋”,因为我的诉讼细节。在这次会议期间,亨利和我讨论了餐桌抢购活动的成功。然后,令人费解的是,亨利的语气和评论突然改变了,这与现有的讨论主题无关。正如我的诉讼所称,亨利说,“我们有麻烦了。你违反了Carta的不混帐政策。“。正如我在诉讼中声称的那样,以下是他在会议期间说的其他一些话:
“你就像一个酒鬼,需要承认自己的问题,并从混球中全面康复。”
“我担心,对于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不做个混蛋。”
“你过去拿过通行证,因为你是个女人。”
“下周再来,承认你已经准备好康复了,否则就离开公司。”
我目瞪口呆。我发现亨利的性别歧视、敌意和残酷的言语攻击令人震惊和羞辱,特别是因为最近在不到两周前,“餐桌挑战”取得了成功,而且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亨利的书面负面反馈。
在亨利发脾气期间,正如我的诉讼所指控的那样,我保持冷静,但我试图为自己辩护-针对我不确定的事情-因为没有给出表现不佳的例子。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禁止混蛋政策”(因为它不存在)。我和他谈到了我在加尔塔面临的挣扎。我甚至试图通过解释有多少人第二次为我工作或调到我在Carta的团队,来让他相信我不是混蛋。
被迫辞职时,我认为我的表现将不言而喻,我可以用我的声音在Carta内部推动变革。近两年后,我悲哀地意识到这种方法是多么天真和无效。
亨利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中的不专业行为是他最后一次报复,也是最后一根稻草。正如我在诉讼中指控的那样,亨利在我工作期间的行为,他拒绝提拔我,当我抱怨性别歧视时他对我的敌意,以及他对我风格的性别歧视言论和所谓的讨人喜欢的问题,让我别无选择,只能终止我的工作。
两天后,我给亨利发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见下图)。他在8分钟内做出了回应。正如我在诉讼中指控的那样,他没有否认我是被迫辞职的,也没有质疑我对他在会议上的评论的描述。我不认为他被惊呆了。他想让我离开。
正如我在诉讼中指控的那样,我认为亨利的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迫使我辞职:考虑到公司的核心信息,以及高管团队和董事会中缺乏女性和多样性,直接解雇我对Carta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像许多人一样,我对世界的现状以及一个理应走在创新前沿的行业的状况深感悲痛。对我来说,站在创新的前沿并不涉及歧视或偏见。
我已经找到了应对和前进的最佳方式是将我的精力投入到一些项目中,所有这些项目的目标都是帮助科技行业中代表不足的人在谈判桌上获得一席之地,在谈判桌上有发言权,当然,获得同工同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