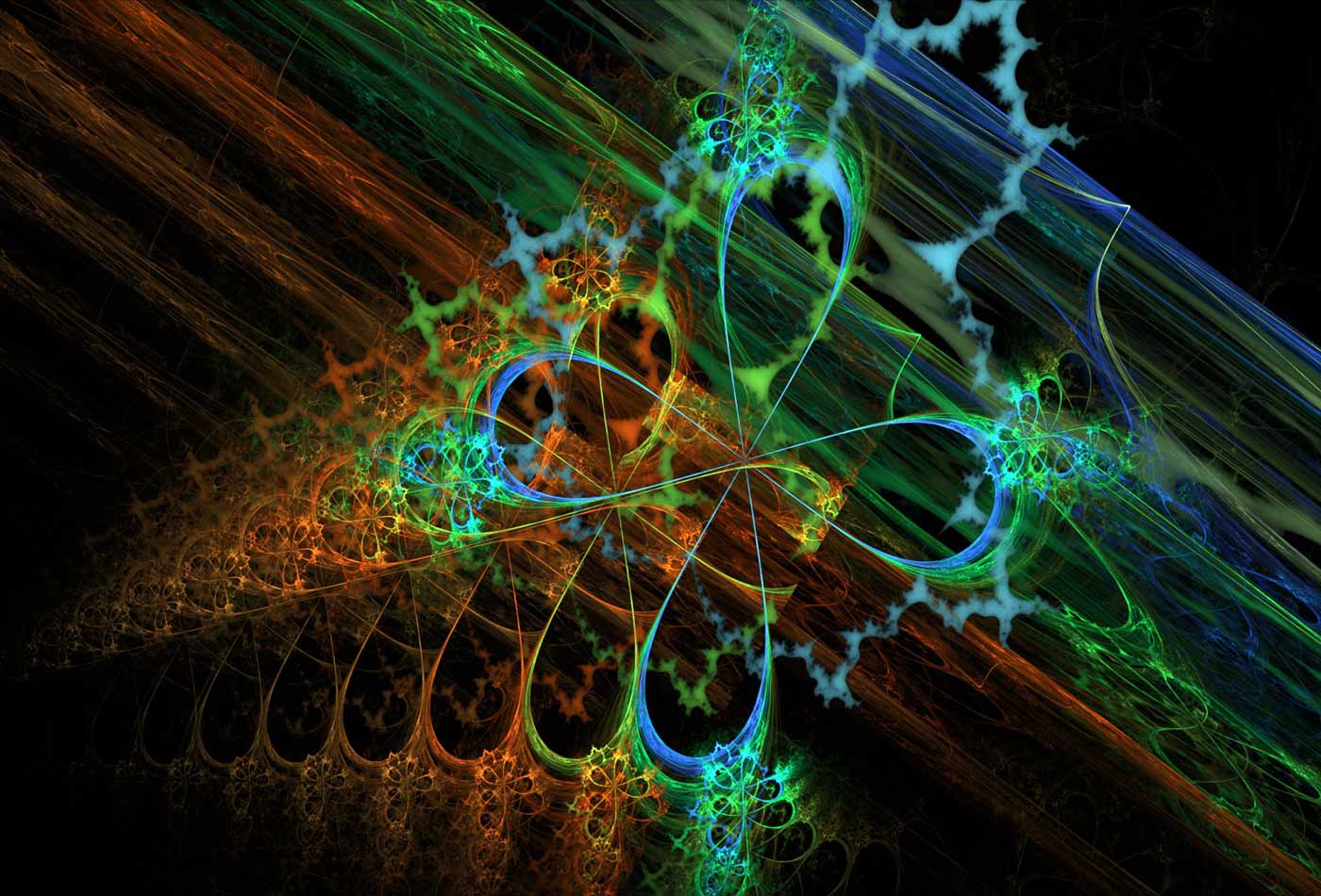开放式:最后一个重大挑战(2017)
虽然开放式可能是发现智能的一种力量,但它也可能是人工智能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AI)是计算机科学面临的重大挑战。毕生的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为它的追求提供了动力。然而,今天,它最雄心勃勃的愿景仍然没有实现:尽管进步仍在继续,但没有任何与人类竞争的通用数字情报在我们的触手可及之处。然而,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正是我们从“重大挑战”中所期待的-这将需要巨大的努力在漫长的时间内实现-很可能是值得等待的。还有其他重大挑战,比如治愈癌症,实现100%可再生能源,或者统一物理学。有些领域有一整套重大挑战,比如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23个数学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给整个20世纪带来了挑战。然而,不同寻常的是,有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明和我们对自己的理解,而只有最小一部分的研究人员知道这一点。尽管这听起来有多么不可思议,但这正是今天面临开放式挑战的情况。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关心它的解决方案了,尽管它是最令人着迷和最深刻的挑战之一,实际上有一天可能会得到解决。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希望帮助修复这种令人惊讶的脱节。我们将解释这一挑战是什么,如果解决了它的惊人影响,以及如果我们激发了您的兴趣,如何加入到这一探索中来。
挑战:数十亿年前出现了第一种生命形式,很可能是类似于单个原核细胞的东西。虽然我们不知道它起源的全部故事,但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数十亿年里,这个不起眼的细胞不知何故辐射到了我们今天欣赏的地球上各种生命中。沿着这条宏伟的道路,细胞开始以阳光为食,出现了更复杂的真核细胞,第一次交配发生,第一批多细胞生物开始增殖(大约10亿年前)。然后,大约5亿年后,在一场被称为寒武纪大爆发的壮观的创新浪潮中,几乎所有主要的动物群体都出现了。随着这些群体进一步多样化到我们今天所知的物种,植物在整个土地上以近乎无限的多样性展开。最终,陆地动物由鱼类繁育而来,地球上的生物在海面上繁衍生息。所有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都出现了,每一种“动物”实际上都是数百万到数万亿真核细胞的集合,参与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舞蹈-每一种动物也都嵌入了更高层次的生态舞蹈,即捕食者、猎物、交配和繁殖。一路上,奇妙的发明,有些超出了今天所有人类工程学的能力,标志着前进的道路-光合作用,鸟类的飞行,以及人类智能本身只是几个这样的胜利。这个史诗般的故事被称为进化论,但这样一个谦逊的词很难公正地评价这一令人敬畏的成就。
问题是,“进化”听起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或者像重力一样的物理力量,但地球上生命的繁衍表明,这是多么严重地低估了它的本质。进化更像是几千年来释放出来的创造性天才,而不是物理过程。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想想看,从计算上看--地球上的进化就像是发明了整个自然界的单一算法的一次运行。如果我们今天运行一个机器学习算法,如果它给我们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或者几个,我们会很高兴,但然后它就结束了-问题要么解决了,要么没有解决,程序就完成了。但地球上的进化是惊人的不同-它似乎永远不会结束。诚然,“从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词,但数十亿年来持续不断的创造力几乎是我们可能从未见过的。所以,是的,我们称它为进化,但它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算法,一个不知疲倦地在不可理解的时间跨度内创造出越来越大的复杂性和新颖性的过程。
事实上,还有另一个术语抓住了单个过程的概念,这个过程创造了几乎永恒的天文数字复杂性-我们称之为“开放式”。自然界中存在的开放式是现代科学最大的谜团之一,尽管它出人意料地很少受到关注。我们的教科书把进化论描述得好像它是被理解或解决的,但在现实中,虽然我们可以填写很多细节,但它最令人震惊的属性-它的开放性-充其量也只是被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你从计算机科学家的角度来看,你会很容易地看到,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对这个属性的最终解释将是一些深刻而有力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谜,因为到目前为止,就像人工智能一样,开放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想像一下,如果我们真的能编写一个真正的开放式算法。其影响将是非同寻常的。你对新的建筑流派、新的汽车设计、新的计算机算法、新的发明感兴趣吗?那么不断地生成它们又如何呢?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呢?无穷无尽的新形式的音乐和艺术,永远展开而不会变得枯燥的视频游戏世界,在你的电脑里出现的宇宙完全是独特的,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自然的力量就是创造的力量,它完全封装在开放式的神秘中。这些梦想听起来也像我们对人工智能的一些渴望,但如果它们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那么它们恰恰是人工智能仍然不专注的领域(有如此多的精力投入到寻找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事实上,开放式甚至可能是一条通向人工智能的道路,或者是通向人工智能的道路-毕竟,最初设计我们智力的是大自然中的无限制进化。但这只是它众多创意中的一个。因此,开放式当然与对人工智能的追求重叠,但这是一种更广泛的追求,一种捕捉机器内部创造力量的尝试。地球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自我生成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的一小部分。
这个愿景不是童话故事。事实上,作为一项重大挑战,开放式最令人兴奋的方面之一是,它看起来显然是可以实现的。例如,在许多情况下,实现产生式系统(即,生成各种工件的系统)可能比手工设计生成的工件(如智能)本身更容易。换句话说,虽然几万亿连接的大脑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但进化过程本身可能更容易描述或实现。因此,也许我们可以真正弄清楚它,并确定它的必要条件-甚至可能很快就会有。
然后您可能会想,问题首先是什么--如果问题这么简单,那么为什么它仍然没有解决呢?原因之一是,由于偶然的历史原因,这一特殊的重大挑战根本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结果是很少有人(更不用说才华横溢的人)知道它了。它缺乏应得的精神份额。但这并不是全部解释。另一点是,与许多重大挑战一样,事实证明,它的核心解决方案比最初看起来要狡猾得多。
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开放式虽然可能很简单,但却包含了一种思维把戏,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进化的所有假设。关于选择、生存、健康、竞争、适应的整个故事--这些对于分析来说都是非常有说服力和启发性的,但它不太适合于综合:它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个过程真正写成一个有效的开放式算法。要找出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开放式的原因(从而能够编写具有类似能力的算法),可能需要一种与我们过去完全不同的进化叙事。这就是它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虽然它的程序可能很简单,但需要一个激进的新视角来破案。重要的是,进化本身只是许多可能的开放式实现之一。例如,人类的大脑似乎展示了它自己的开放式创造力,所以很可能一个开放式的过程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底物中出现,包括在深度学习中。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建议重现大自然的全部辉煌。这有什么意义呢?大自然已经在这里了。相反,这里的潜力在于引入一个通用的永无止境的创造性算法,在您想要的任何领域。这个假设是,我们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只是一整类可能的开放系统的一个实例。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出于某种原因,自然是它唯一可能的实现,但为什么会这样,没有明显的解释,就像我们得出结论说,鸟类是唯一可能实现飞行的东西一样。这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个体之间的互动(或者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可能称之为“候选者”的东西)、选择、繁殖等等--从根本上看似乎是通用的。通用的开放式算法应该是可能的,这应该会让许多寻找具有巨大潜在回报的挑战的聪明人感到兴奋。这里还有让爱因斯坦或沃森-克里克团队将他们的名字铭刻在科学史上的空间。
由于来自自然进化的灵感,到目前为止,开放式算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进化算法上,尽管可以肯定的是,非进化过程(如产生新想法的单个神经网络)可能表现出开放式属性。然而,由于历史演变的焦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引用
事后看来,生命世界类似于微型地球生态系统模拟的趋势可能在不经意间让这个领域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狭窄。乍一看,这些生命世界似乎只是试图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与地球相比的)模拟来复制地球上的一些微小的生态行为。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该领域没有吸引到应有的兴趣。但在开放式的背景下,生活世界并不是真的要研究一个小的生态相互作用。相反,它们的目的是用来透视如何引发无限制的复杂性爆炸这一深刻问题。它们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爆炸只限于类似地球的模拟--回想一下,开放式大概是一种广泛的可能系统的属性。只是在这一领域的早期,生命世界和地球(最初出现开放式现象的地方)之间的简单类比使它们成为研究此类现象的一个方便的选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开放式确实可以在生活世界之外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该领域更雄心勃勃的希望不是创造一个单一的开放式世界,而是按需创造开放式,一种可以应用于任何东西的无处不在的创意平台。
1992年,马克·贝道(Mark Bedau)着眼于超越一种系统,着眼于更高的科学严谨性,引入了一套名为“活动统计”的测量方法,旨在衡量此类系统表现出的开放式程度。有了这个工具(甚至一度被用来测量文化进化),研究人员能够证明一些生活世界产生了开放的动态,至少根据活动统计数据是这样的。例如,Alistair Channon的world Geb得分很高,据说“通过”了活动统计测试的最高门槛。
但是,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无论测试结果是什么,任何观看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系统仍然与自然相去甚远。是的,你可以看到生物学会互相追逐或生长得更快,但除此之外,鲜有明显的兴奋之情。这一结果引发了一些关于开放式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的辩论-贝道的测试不知何故遗漏了真正的问题?毕竟,门槛应该很高。这场辩论与其他新兴领域的类似辩论类似,例如人工智能中关于智能定义的辩论。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我们可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语义争论的泥潭,这不会增加什么价值。2015年,艾米丽·多尔森(Emily Dolson)、安雅·沃斯蒂纳(Anya Vostina)和查尔斯·奥弗里亚(Charles Ofria)采取了有趣的视角,试图确定开放式进化不是什么,这说明了正面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也许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接近于界定其本质特征。其他反映开放式的关键因素的历史观点包括拉塞尔·斯坦迪什在2003年强调新颖性的产生,以及卡洛·马利在1999年强调增加复杂性。
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可能存在有趣的开放式程度(这一观点确实被贝道的测试所接受)。也就是说,开放式不仅仅是一个二元的非此即彼的命题。虽然我们更有可能通过目标远大来获得尽可能深刻的洞察力,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实践中,即使是捕捉到开放的有限方面的制度和思想,也仍然可以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并在通往全面、永无止境的创新的道路上教会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
测量或定义开放式的部分问题在于,它的解释可能部分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对创新的欣赏(这是开放式的关键)可能与特定的观点或背景相关。我们对某些设计印象深刻,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欣赏它们的功能,但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导致设计用处降低(或者甚至可能只是在情感上不那么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印象深刻,即使设计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只有在世界上有山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攀登山顶,自行车换挡上山的能力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创新,所以在不考虑其背景的情况下,还不清楚世界上是否有内在的创新衡量标准。虽然科学家似乎常常对任何一种主观性过敏,但也许有办法在不牺牲科学严谨性的情况下,敞开心扉拥抱主观性。例如,我们仍然可以尝试将感人等主观概念正式化(在肯·斯坦利(Ken Stanley)和乔尔·雷曼(Joel Lehman)的著作中)。开放式中的主观性是一个有趣而微妙的问题,斯坦利在其他地方也写过很长的文章,但重点是衡量开放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要做好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