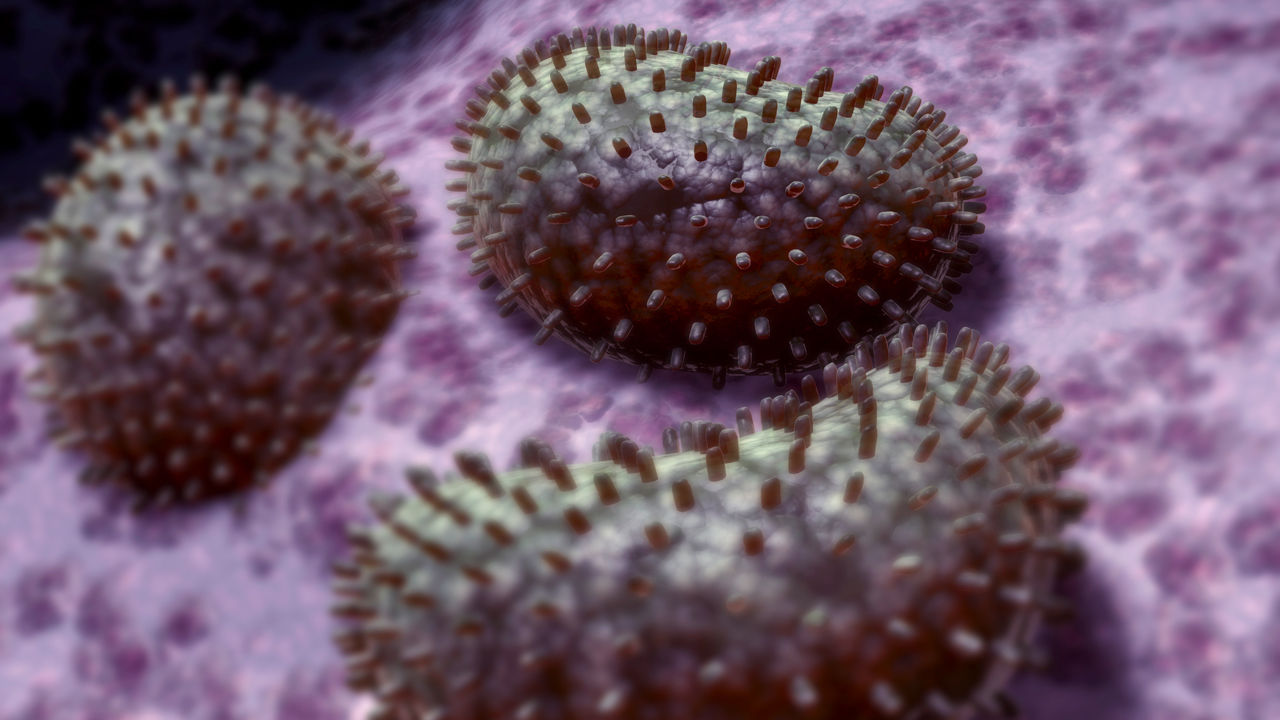古老的微生物军备竞赛强化了免疫系统,但也让我们变得脆弱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最近举行的一次关于传染病进化的研讨会上,病理学家尼西·瓦尔基(Nissi Varki)指出,人类患有一长串致命疾病-包括伤寒、霍乱、腮腺炎、百日咳、麻疹、天花、脊髓灰质炎和淋病-这些疾病不会影响猿和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所有这些病原体都沿着同样常见的途径闯入我们的细胞:它们操纵称为唾液酸的糖分子。数以亿计的这种糖存在于人体每个细胞的外表面,而人类体内的唾液酸与类人猿体内的唾液酸不同。
瓦尔基和一个国际研究小组现在已经追踪到,在我们遥远的祖先出现分子脆弱性后,进化可能是如何争先恐后地构建新的防御措施。通过分析现代人的基因组和我们已灭绝的表亲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古代DNA,研究人员检测到我们的免疫细胞在至少60万年前在这三种类型的人类的祖先身上发生了一次突然的进化。
正如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的“基因组生物学与进化”上报道的那样,这些基因变化可能增强了人体对利用唾液酸进化而来的病原体的防御能力-但也造成了新的脆弱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指出,人类独特的唾液酸本身曾经是抵御疾病的一种防御手段。雅典佐治亚大学的微生物学家克里斯汀·希曼斯基(Christine Szymanski)说,这一进化传奇生动地说明了人类和微生物之间的竞争,她不是合著者。“这给了我们一个人性化的视角,让我们了解如何不断变化才能跟上步伐。”
这场进化军备竞赛的竞技场是糖萼,一种保护所有细胞外膜的糖衣。它由从细胞膜发芽的分子森林组成。唾液酸位于最高的枝条顶端,也就是被称为多糖的糖链,它们植根于膜深处的脂肪和蛋白质上。
考虑到它们的重要性和绝对数量,唾液酸通常是入侵病原体遇到的第一个分子。人体细胞包被一种唾液酸,N-乙酰神经氨酸(Neu5Ac)。但猿和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也携带一种不同的N-羟基神经氨酸(Neu5Gc)。
200多万年前,根据多分子时钟方法,六号染色体上CMAH基因的突变使人类祖先不可能再产生Neu5Gc;相反,他们制造了更多的另一种唾液酸,Neu5Ac。这篇新论文的合著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帕斯卡尔·加格纽克斯(Pascal Gagneux)说:“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对人类细胞的表面进行了一次古老的彻底改头换面。”鸟类、一些蝙蝠、雪貂和新大陆猴子都分别进行了相同的进化变化。
该论文的资深作者、尼西·瓦尔基的配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内科科学家阿吉特·瓦尔基(Ajit Varki)说,这种变化可能是为了防御疟疾。感染黑猩猩的疟疾寄生虫不再能够与我们红细胞上改变的唾液酸结合。
但在接下来的100万年左右,随着Neu5Ac成为一系列其他病原体最喜欢的门户,这种突变成为了一种负担。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学学术研究和培训中心组织的传染病研讨会上,研究人员描述了多种疾病是如何进化成使用Neu5Ac进入细胞或逃避免疫细胞的。
免疫细胞体细胞唾液酸细胞膜抑制激活糖萼寄生虫病毒Siglecs细菌。
冠状病毒似乎也不例外。Ajit Varki说:“大多数冠状病毒通过两个步骤感染细胞-首先识别丰富的唾液酸作为其结合位点,以获得更好的立足点,然后寻找更高亲和力的蛋白质受体,如ACE2,”Ajit Varki说。“可以把它想象成最初的握手或介绍,在一个人可以要求约会之前,这是必需的。”两份预印本显示,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在与ACE2受体结合以刺穿人类细胞之前也与唾液酸对接。
在过去的研究中,Ajit Varki和Gagneux提出,细胞的改造和Neu5Gc的丢失甚至可能促成了我们人类属一个新物种的起源。如果只含有Neu5Ac唾液酸的女性与仍表达Neu5Gc的男性交配,她的免疫系统可能已经排斥了该男性的精子或由此发育的胎儿。研究人员推测,这种生育障碍可能在200多万年前帮助将人类种群划分为不同的物种。
但是唾液酸的变化也引发了病原体和我们祖先之间新的军备竞赛。在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扫描了6名尼安德特人、2名丹尼索瓦人和1000名人类的DNA,并观察了数十只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他们发现,进化上的变化“显著改变了”一类蛋白质-唾液酸结合免疫球蛋白类型凝集素(Siglecs),这种凝集素通常位于人类免疫细胞表面,识别唾液酸。
Siglecs是分子哨兵:它们探测唾液酸,看它们是我们身体熟悉的部位还是外来入侵者。如果Siglecs发现了受损或丢失的唾液酸,它们就会发出信号激活免疫细胞,激发炎症大军攻击潜在的入侵者或清理受损的细胞。相反,如果唾液酸看起来是我们细胞的正常部分,其他抑制性的Siglecs就会抑制免疫防御,从而不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见上图)。
研究人员在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中发现了13个Siglecs中的8个基因组DNA的功能变化,这些Siglecs编码在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19号染色体上的CD33基因簇中。这一进化热点只发生在Siglec基因变体中,而不是发生在染色体上附近的基因中,这表明自然选择有利于这些变化,想必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对抗针对Neu5Ac的病原体。
第一作者、现供职于肯塔基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纳兹尼恩·汗(Naazneen Khan)说,猿类没有表现出这些变化。鉴于这些突变在古人类中的存在,这场进化的爆发肯定发生在60万年前我们的谱系分化之前,但在200多万年前人类CMAH基因发生突变之后,可能是在直立人中,直立人被认为是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祖先。
大多数Siglecs都是在免疫细胞上发现的,但在这篇新的论文中,研究小组报告说,几种经历了进化变化的人类Siglecs在其他类型的人类细胞中也有表达,包括在胎盘、宫颈、胰腺、肠道和大脑中的一些。Nissi Varki认为,Siglecs的出现可能是与感染这些组织的病原体进行激烈斗争的副作用。
虽然最近突变的Siglecs保护我们免受病原体的侵袭,但它们也可能导致其他疾病。一些基因改变的Siglecs与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哮喘和脑膜炎)有关。研究人员认为,改变后的Siglecs可能会持续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不会抑制对我们自身组织的免疫反应;它们甚至可能使一些人更容易患上严重的新冠肺炎身上出现的失控炎症。
其他研究人员说,这项工作强调了广泛的进化论原理。“这很好地说明了…。自然选择并不总是追求最优的解决方案,因为最优的解决方案一直在变化,“德国汉诺威医学院的糖生物学家Rita GERARDY-Schahn说,她没有参与这项新的工作。“短期内对自然选择最有利的可能是明天的错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