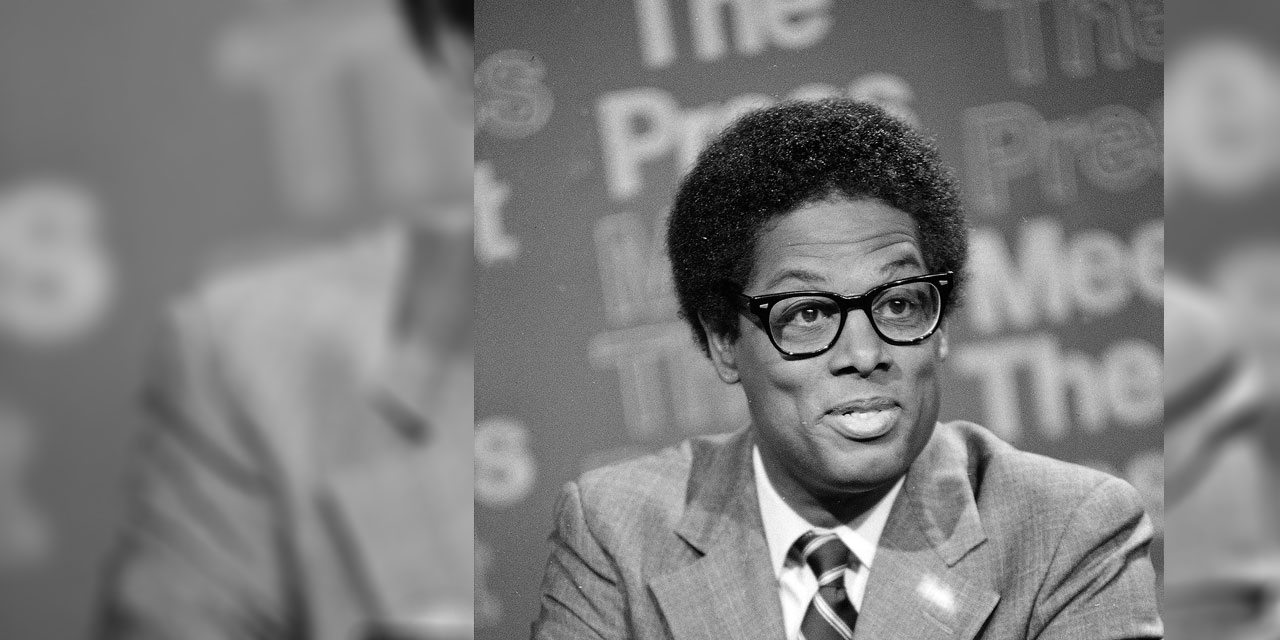托马斯·索威尔,不墨守成规的人
以他对经济学、政治理论和思想史的贡献来衡量,托马斯·索威尔跻身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列。然而,索威尔在这样的思想家中很少见,他从未在读者中激起一种被凌驾于人之上的感觉。正如凯文·威廉姆森(Kevin Williamson)所说,索威尔“在严肃的学者中是最罕见的:直言不讳。”从1991年到2016年,他的全国性辛迪加专栏为清晰的写作设定了标准,尽管他报道的主题往往很复杂。索厄尔曾经说过:“太多的学者写得好像通俗易懂有损他们的尊严,有些人似乎认为逻辑是对他们言论自由的违宪侵犯。”如果学者生来就是不必要的复杂散文,那么编辑往往会助产它。索威尔曾经打趣地说,编辑可能会把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变成可怕的东西,比如“问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考虑一下索厄尔对“稀缺性”这一经济学概念的清晰而简短的解释。“‘稀缺’是什么意思?”他在门外汉的教科书“基础经济学”中问道。“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加起来比原来的要多。”索威尔的散文不仅没有毫无意义的复杂性,第一人称视角也是如此。除了在他的回忆录“个人奥德赛”中,“我”或“我”这个词很少出现在他的30多本书中。
对他的批评者来说,索威尔的写作风格是严厉的。但对于他的粉丝基础-其中包括不同的人物,如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摆脱了如今经常被认为是文化评论的自我陶醉的废话。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领先的公共知识分子平克称索威尔为历史上最被低估的作家。就韦斯特而言,2018年他在推特上向数百万粉丝发布了几句索厄尔的名言。
索威尔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50年-一封写给现已停刊的“华盛顿星报”的信,敦促取消该市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在此期间,他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唯一迹象是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萌芽。对索厄尔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似乎解释了太多”,包括他自己的“严峻经历”。当时,索厄尔是一名20岁的高中辍学生,白天当书记员,晚上上课-这种情况实际上标志着他在十几岁后期失业和一度无家可归的情况有所改善。
索威尔的经历并不总是那么惨淡。虽然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但他仍然记得自己的早年童年是快乐的。他是在没有电和热水的房子里由他的姑婆抚养长大的-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北卡罗来纳州黑人的典型。当时,索厄尔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很穷;毕竟,他们“拥有周围人所拥有的一切”。他也没有意识到在吉姆·克罗时代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白人对他来说“几乎是假想的”。事实上,当得知大多数美国人不是黑人时,这是“令人震惊的”。
1939年,索威尔全家搬到哈莱姆区后,他的世界急剧扩张。这是詹姆斯·鲍德温(比索威尔年长6岁)的哈莱姆区,提供的服务中有公共图书馆,9岁的索厄尔被吸引到这里,还有斗殴,他别无选择,只能经常参加。“有一段时间,”他回忆说,“安全地回家吃午饭成了一种折磨,以至于一个朋友会把他的夹克借给我作为伪装,这样我就可以在别人发现我之前逃走。”
当他回到家时,他的麻烦也没有结束。年复一年,他与姑婆的关系每况愈下,在他进入纽约市最负盛名的公立高中斯图文森(Stuyvesant)后,关系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一场不合时宜的疾病,加上繁重的工作量,使功课变得难以应付。不久,索威尔就完全逃课了,尽管他和养母正在自相残杀:她扔掉了他珍爱的艺术用品;他砸碎了她最喜欢的花瓶;她以莫须有的罪名报警;他威胁要离开家。
冲突不断升级,直到达到实际暴力的边缘。在他的回忆录中,索威尔讲述了痛苦的高潮:
“这要持续多久,托马斯?”有一天她问我。
“直到有人崩溃,”我说。“而且不会是我。”
“你这个撒谎的伪君子!”我说,然后开始大骂一通,没有留下任何想象的余地。
她气疯了,抓起一把锤子往后拉,想把它扔出去。我离她太远了,拿不走,所以我说:“扔吧--不过你最好别打偏了。”
她气得发抖,更甚于恐惧,放下了锤子。后来,她似乎终于明白了我们关系的现实,我们简直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敌人。
索厄尔很快就获得了解放,并为无家可归的青年找到了收容所。“现在我很清楚,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依靠,”他意识到。“我自己。”除了身上的衣服,他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段旅程将把他带到海军陆战队、常春藤盟校,以及劳工部的白宫。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索威尔的生活可能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传记片或纪录片的原材料。相反,他的故事相对默默无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索威尔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多年后,最终落到了自由意志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某个地方-这一取向在好莱坞绝对不受欢迎。但他也没有把他的人生故事挂在袖子上,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很多人看重的是“亲身经历”,而不是逻辑论证。罗宾·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在她的畅销书“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中建议,当与黑人谈论种族问题时,白人应该避免沉默或情感孤僻-但也要避免争吵。(例如,她认为“我不同意”和“你误解了我”这两个词是禁区。)。显然,对于白人来说,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热情地同意黑人说的任何话。相比之下,索厄尔坚持认为他的作品“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或适用性”,而不是“因[他的]个人生活而增强或减少”。
然而,他拒绝将“生活经验”作为证据的替代品,这不应与经验无关紧要的观点混为一谈。事实上,索厄尔的作品有时确实反映了他生活中的一些插曲-通常是痛苦的插曲。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他的儿子约翰·索威尔(John Sowell)。约翰出生时很健康,看起来很正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变得很明显,有些地方不对劲。在大多数孩子开始说完整句子的年龄过后,约翰几乎不会说一句话。对于局外人,甚至对索厄尔当时的妻子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精神残疾病例。然而,索厄尔并不信服。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约翰的聪明才智不同寻常:例如,他可以在会走路之前就能撬开儿童锁。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有一次,他在下棋过程中打翻了一个棋盘,把所有的棋子都放回了原来的位置。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智力迹象,他甚至连最简单的单词都不能理解,这就更加令人费解了。然而,当约翰在四岁左右慢慢开始说话时,希望来了,当他长大成为一个适应良好的年轻人时,最后的平反到来了。
几十年后,在他的儿子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索威尔开始解释这个谜题。其结果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说话晚的儿童现象进行了学术研究,这些儿童异常聪明,但并不自闭症。根据这项原始研究,以及轶事、数据和历史,索威尔写了两本书:1997年的“说话迟钝的孩子”和2001年的“爱因斯坦综合症”。第二位-以历史上最著名的晚期谈话者的名字命名-赢得了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称赞,称其是“对人类知识的无价贡献”。但是,除了像平克这样的儿童心理学专家和晚谈者的父母之外,这些书几乎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他们代表了一项非凡的成就:在一个学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时代,一个学者在一个他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的领域开创新天地,这是非常罕见的。
索厄尔的经济学书籍,也就是他接受培训的领域--他于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构成了他成就的核心。其中最重要的是1980年首次出版的“知识与决策”(Knowledge And Decision)。这本书的灵感来自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945年的经典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使用”。与哈耶克有关的知识不是爱因斯坦发现的那种永恒的科学知识,也不是政府机构收集的官僚知识,而是实用知识-比如,在特定社区的特定街角经营熟食店,或者在气候多变的特定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所需的那种知识。这种知识既是转瞬即逝的(上周是正确的,本周可能不是),也是本地的(在一个街角是正确的,在下一个街角可能就不是了)。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拥有太多。
如果分布在数百万不同头脑中的这些知识的总和能够被实时收集并传达到一个单一的头脑中,那么中央计划者就可以像大师指挥管弦乐队一样指导经济。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哈耶克的洞察力是,无论如何,价格机制都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锡突然变得稀缺-无论是因为储量被破坏了,还是因为发现了锡的新用途-不需要中央规划者来让消费者减少使用这种金属。人们甚至不需要知道为什么锡变得更加稀缺。除了锡价格上涨之外,没有其他信息,数百万人将减少对锡的使用,就好像受到了一股无所不知的力量的指挥。换句话说,在没有价格的情况下,需要不可能的知识和有意识的协调的东西,两者都不需要。
哈耶克的散文在哪里结束,索威尔的杰作就从哪里开始。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不仅是关于知识(在哈耶克的意义上),也是关于我们基于这些知识做出的决定-在经济、政治、战争和许多其他方面。在一个每个人的知识都等同于无知海洋中的一个斑点的世界里,索威尔的论文认为,“最根本的决定不是做出什么决定,而是由谁来做决定。”虽然决策者可能会谈论目标--结束贫困、减少种族主义、传播民主等等--但他们实际上所能做的就是开始这一进程。因此,当我们面对“谁来决定?”的问题时,我们不应参考某一机构的优越目标或道德品格,而应根据不同决策者所面对的诱因和约束来作答。
强调制衡的“美国革命”提供了索威尔理论付诸实践的经典例子。索威尔写道,根据“来自经验的知识”,开国元勋们假设人类基本上是自私的,并创建了一套激励和约束系统,以阻止自私的领导人做可怕的事情。相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基于“对人的本质的抽象推测”,采取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是完美的,而政府是完美的工具。根据索威尔的说法,这两场革命的不同后果并不是偶然的。
决策者之间更普遍的选择是让政府与市场对立。然而,对索威尔来说,“市场”是“一种误导性的修辞手法”。许多人“提到‘市场’,就好像它是一个与政府平行的机构,也是政府的替代机构。”实际上,“市场”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现有的制度中进行选择,或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喜好做出新的安排”。例如,住房需求“可以由‘市场’通过每个人选择的一千种不同方式来满足--从住在公社到买房、租房、搬到亲戚家里、住在雇主提供的住处等等。”市场安排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什么让它们团结在一起,又将它们分开
黑暗讽刺(通常是某些政府计划的结果)是索威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基础经济学中提到的一个事实是典型的:作为大萧条期间支持农民努力的一部分,联邦政府在1933年购买了600万头猪并将其销毁-当时数百万美国人正在努力养活自己。当然,现代官僚机构很难逃脱嘲笑。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常识导致许多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因为众所周知,病毒主要通过咳嗽传播。然而,几个月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建议人们不要戴口罩-只是在大流行几乎达到顶峰后才推翻了他们的建议。与面临市场考验的企业主不同,这些组织中没有人一定会付出代价。
“视觉的冲突”(1987)代表了索威尔将自己的思想与他们的对立面进行对话的最大努力。他通过观察一个奇怪的事实开始了这本书:可以预见的是,人们会在看似毫无共同之处的政治问题上站在相反的一边。例如,了解某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以某种方式可以让你预测他们对富人征税、枪支管制和堕胎的看法。人们很容易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仅仅是政治上的部落主义。但索厄尔认为,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对社会世界有两种基本的思考方式,对人性的两套基本假设,以及两种相互冲突的“愿景”,大多数政治分歧都是从这两个“愿景”而来的。他将其命名为受限视觉和自由视觉。
受限的视野是知识和决策的基础。它认为,人类与其说是完美的,不如说是有缺陷的;与其说是知识渊博的,不如说是无知的;比起利他主义,人类更容易自私自利。好的机构将人性的悲剧性事实视为既定事实,并创建激励结构,这种结构在不要求男人和女人成为圣人或天才的情况下,仍能带来社会期望的结果。哈耶克描述的价格机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对中央集权持怀疑态度,因为掌握它的人会自私自利,甚至更糟。更重要的是,在狭隘的视野中,传统和社会习俗是可信的,因为它们代表了无数代人积累的智慧。
至于无拘无束的视野,如果人类有缺陷、自私和无知,那不是因为我们天性中不可改变的事实,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恰好是这样安排的。通过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教育体系、法律和其他制度,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世界--包括那些据称由人性决定的方面。通过通常由中央当局执行的开明的公共政策,曾经被认为不可避免的邪恶被揭示为社会结构或过时思想的产物。在这一愿景中,传统不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而是按照现代观察家的判断,根据它们的合理性(或缺乏合理性)而生或死。
索威尔写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哲学家们所说的颠倒解释--要解释的现象。以贫困为例。许多人观察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理解地想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贫困。但在狭隘的视野中,真正的问题是财富为什么会存在。“几千年来,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我们认为的贫困水平一直是常态。需要解释的不是贫困的起源,“索威尔在他最近的”财富、贫困和政治“一书中写道。“需要解释的是那些创造并维持更高生活水平的东西。”在个人事务上,他也会很快注意到一个错误的解释。“86岁早已过了通常的退休年龄,”他在专栏的最后一期中指出,“所以问题不是我为什么要辞职,而是我为什么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它们在观察社会世界时所处的解释位置。索威尔在“冲突”中写道:“自由视野的信徒寻求战争、贫困和犯罪的特殊原因,而受限视野的信徒寻求和平、财富或守法社会的特殊原因。”
索威尔对种族不平等研究的巨大贡献是颠覆了主导主流思想一个多世纪的解释。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一个由具有同等天生潜力的群体组成的公平社会里,我们应该在财富、职业地位、监禁和其他许多方面看到种族平等的结果。种族差异无处不在,这要么被视为种族群体不是天生就具有同等潜力的证据,要么被视为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20世纪初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