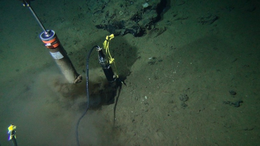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我是如何重新发现宗教的
当我在写“大卫与歌利亚”一书时,我去温尼伯见了一位名叫威尔玛·德克森的妇女。
30年前,她十几岁的女儿坎迪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了。这座城市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一周后,坎迪斯的身体在距离德克森家四分之一英里的一座小屋里被发现。她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威尔玛和她的丈夫克里夫被叫到当地警察局,并告诉了这个消息。坎迪斯的葬礼在第二天举行,随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该省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那里,因为坎迪斯的失踪吸引了这座城市的注意力。
“不管是谁杀了坎迪斯,你对此有何感想?”一名记者问德克森夫妇。
克里夫说:“我们想知道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分享一份似乎在这些人的生活中缺失的爱。”
威尔玛紧随其后。“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找到坎迪斯。我们找到她了。“。她接着说:“在这一点上,我不能说我原谅这个人,”但在这一点上,重点是这个短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做过可怕的事情,或者感觉到了去做的冲动。”
我想知道德克森一家是从哪里找到力量说出这些话的。一个性掠夺者绑架并谋杀了他们的女儿,克里夫·德克森(Cliff Derksen)可以谈论与凶手分享他的爱,威尔玛(Wilma)可以站起来说,“我们一生中都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或者有过这样的冲动。”在这样的时刻,两个人在哪里能找到宽恕的力量呢?
在一本名为“大卫与歌利亚”的书中,这似乎是一个相关的问题。毕竟,圣经对大卫和歌利亚决斗的描述的寓意是,我们关于权力和力量所在之处的先入之见是错误的。
歌利亚似乎令人敬畏。但在圣经文本中有各种各样的暗示,事实上,他并不是他看起来的那样。为什么他要由服务员护送到谷底呢?为什么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大卫显然不打算用剑打他?医学专家甚至猜测,歌利亚一直患有一种名为肢端肥大症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导致异常生长,但也经常有视力受限的副作用。
如果歌利亚不得不被带到谷底,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应大卫,因为他只能看到他前面几英尺的地方,那该怎么办?换句话说,如果让他看起来如此庞大和令人敬畏的东西,也是他最脆弱的原因,那该怎么办呢?
在我研究的第一年,我收集了这类悖论的例子--我们关于优势或劣势的直觉被证明是颠倒的。为什么这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阅读障碍?为什么这么多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童年时失去了父母?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教育中看重的一些东西--比如小班和名牌学校--既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同样多的坏处?我阅读研究,与社会科学家交谈,埋头于图书馆,认为我知道我想写的是哪种书。然后我遇到了威尔玛·德克森。
德克森一家住在离温尼伯市中心不远的一个不起眼的社区的一间小平房里。威尔玛·德克森和我坐在她的后院。我想我内心的某部分希望她变得圣洁或英勇。她两者都不是。她说话简单而轻声。她解释说,她是门诺派教徒。她的家人,像许多门诺派教徒一样,来自俄罗斯,在那里,那些信仰他们的人在逃往加拿大之前遭受了可怕的迫害。门诺教徒对迫害的反应是认真对待耶稣关于宽恕的指示。
“门诺派的整个哲学就是我们宽恕,然后继续前进,”她说。这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温尼伯警方花了20多年时间追查杀害坎迪斯的凶手。起初,威尔玛的丈夫克里夫曾被警方中的一些人视为嫌疑人。这种怀疑的重担沉重地压在了德克森夫妇身上。威尔玛告诉我,她一直在与愤怒和报复的欲望作斗争。
他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圣人。但是,他们的传统和信仰中的一些东西使德克森一家有可能做一些英勇而圣洁的事情。
我从不提前计划我的书。我从中间开始,试着从那里蒙混过关。当我遇到威尔玛·德克森(Wilma Derksen)时,我终于明白了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我一直在阅读的社交沉默中,在我讲述的关于诵读困难、企业家和教育的故事中。借用皮埃尔·索瓦奇(Pierre Sauvage)的那句妙语,我对“精神的武器”感兴趣--来自内心的奇特而令人费解的力量。
当我向一位朋友讲述我去德克森家的经历时,他寄给我一段塞缪尔前书16:7中的语录。这句话完美地抓住了我对大卫和歌利亚的理解,现在它出现在了这本书的第一页: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也不要看他的身高、因为我弃绝了他.因为耶和华看不像凡人。他们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
“大卫与歌利亚”的最后一章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小镇勒尚邦发生的事情。最后几章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构成了阅读这本书的体验。我把勒尚邦的故事放在最后,因为它解决了精神武器的巨大谜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很难看到它们的原因。
勒尚邦是法国的一个叫做Vivarais Plateay的地区,这是一个靠近意大利和瑞士边境的偏远山区。许多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是持不同政见的新教团体(主要是胡格诺派)的家园,在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勒尚本成为非常开放的抵抗中心。
当地的胡格诺派牧师是一个叫安德鲁·特洛克姆的人。在法国沦陷给德国人后的那个星期天,特洛克姆在布道中说,如果德国人强迫勒尚邦的居民做任何他们认为违反福音的事情,这个小镇就不会太顺从。因此,勒尚邦的小学生拒绝每天早上向法西斯敬礼,因为新政府已经下令他们必须这样做。占领统治者要求教师签署效忠国家的誓言,但Trocme在勒尚邦管理学校,并指示工作人员不要这样做。
不久,逃离纳粹的犹太难民听说了勒尚邦,开始出现寻求帮助。Trocme和镇民们收留它们,喂养它们,隐藏它们,并偷偷地将它们带过边境-公开藐视纳粹法律。有一次,当一位政府高官来到镇上时,一群学生实际上给了他一封信,信中明确而诚实地表明了该镇对占领下的反犹太人政策的反对。
信中说:“我们觉得有义务告诉你们,我们当中有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但是,我们没有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与福音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的同志,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在另一个宗教,接到驱逐甚至检查的命令,他们就会违抗命令,我们会尽力把他们藏起来。“。
勒尚邦人民从哪里找到反抗纳粹的力量?在同一个地方,德克森一家找到了宽恕的力量。他们用精神的武器武装起来。在17和18世纪的100多年里,他们一直受到国家的无情迫害。Hugeunot的牧师被绞死和折磨,他们的妻子被送进监狱,他们的孩子被抢走。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躲在森林里,如何逃到瑞士,并秘密地进行他们的服务。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团结在一起。
他们看到的几乎是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最恶劣的迫害。他们发现了什么?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有能力对抗那个州的士兵、枪支和法律。在众多关于勒尚邦的书中,有一本是安德鲁·特洛克姆的妻子玛格达写的一句不同寻常的台词。当第一个难民出现在她的门口时,在1941年漫长的冬天,在战争最惨淡的地方,玛格达·特洛克姆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说不:“我不知道这会很危险。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没人想到这一点。她或勒尚本的其他任何人从未想过,他们在与纳粹军队的战斗中处于任何不利地位。
但这里有一个谜团:勒尚邦的胡格诺教徒并不是1941年法国唯一虔诚的基督徒。在那几年,法国有数百万虔诚的信徒。他们信仰上帝至上,就像勒尚邦人一样。那么,为什么很少有基督徒跟随勒尚邦人民的脚步呢?按照这个故事经常被讲述的方式,乐冠军的人被塑造成英雄人物。但他们并不比德克森一家更英勇。他们只不过是一些人,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在哪里:上帝的力量。
法国的其他基督徒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犯了我们可能犯的错误。他们通过观察外表来估计行动的危险--当他们需要观察内心的时候。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还有多少法国犹太人可能从大屠杀中获救?
我在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的父母每天早上都抽出时间来读圣经和祈祷。我的两个兄弟都很虔诚。我嫂子是门诺派牧师。我有一种与家里其他人不同的经历。我是唯一一个搬离加拿大的人。我甚至是唯一一个离开教会的人。
当我住在华盛顿特区时,我参加了华盛顿社区团契,但一旦我搬到纽约,我就不再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团契。我经常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会偏离家人走过的路呢?
我现在明白的是,我是那些不欣赏精神武器的人之一。我一直是那种被可量化的和有形的东西所吸引的人。我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我不认为我能做到胡格诺派在勒尚邦所做的事。我会数一数双方的士兵和枪支的数量,然后得出结论,这太危险了。我一直相信上帝。我已经领会了基督教信仰的逻辑。我很难看到的是上帝的力量。
我把这句话用过去式是因为我坐在威尔玛·德克森的花园里时发生了一些事。在历史书中读到信仰赋予人们力量是一回事。但是,在一所非常普通的房子的后院里,遇到一个原本非常平凡的人,却成功地做了一些完全不寻常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他们的女儿被谋杀了。德克森夫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站起来,谈论通向宽恕的道路。“我们想知道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分享一份似乎在这些人的生活中缺失的爱。”
也许我们很难看到精神的武器,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哪里看,或者是因为我们被更响亮的物质优势的说法分散了注意力。但我现在已经见过他们了,我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