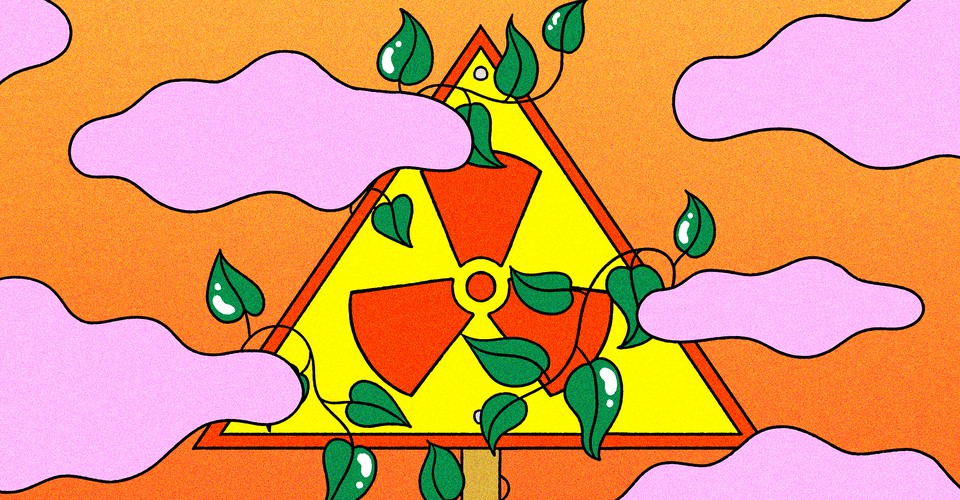森林大火正在释放切尔诺贝利的辐射
树木现在覆盖了禁区的大部分,气候变化使它们更有可能被烧毁。
2003年5月15日凌晨,我风平浪静,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巨大废墟以西3英里处,瓦西尔·约先科(Vasyl Yoschenko)正围着30年前种植的一片苏格兰松林忙碌着。这些树细长,间距很小,但他足够瘦,可以很容易地在它们之间移动,采集生物质和垃圾的样本。就在树的另一边,他修修补补地摆弄着他放在地上的斜格子水平盘子,上面覆盖着超细的布料,旨在吸收他们路上遇到的任何东西。
下午三点左右,尤先科刚刚调整完他的监测设备,第一股浓烟从松树的另一边滚滚而来。消防员正在焚烧一个大小和形状与足球场大致相当的区域的边缘。这些人戴着口罩,穿着迷彩裤,穿着卡其色衬衫,头上盖着布巾,有计划地放火焚烧树林。火焰跃起5英尺高的树干,冲到一些树的顶端,并喷出一缕缕浓烟。
乌克兰放射生态学家约申科(Yoschenko)计划进行受控燃烧,以研究放射性颗粒在火灾中的表现,他知道头顶上盘旋的核污染所代表的风险。他小心翼翼地滑到森林边缘,戴上防毒面具,开始拍照。这很危险吗?尤先科耸耸肩:“不太喜欢。我们很幸运,风向没有改变。“。
森林强烈燃烧了90分钟,释放出铯-137、锶-90和钚-238、-239和-240。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消防员和约先科就可能暴露在切尔诺贝利核工人年辐射限值的三倍以上。
“这太疯狂了,”乌克兰国立生命与环境科学大学的林业教授塞尔吉·齐布采夫(Sergiy Zibtsev)说。“那个地方真的被污染了。约先科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新的科学--就像玛丽·居里一样。
约先科的科学大火预示着切尔诺贝利的未来。从那时起,该地区的气候变暖和干燥,其野火-大部分由纵火和其他人类活动引发-变得更大、更频繁。正如Yoschenko和他的同事在2003年记录的那样,每一场火灾都会释放放射性核素;每一场火灾都会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欧洲主要城市引起人们的担忧。但没有人像今年4月烧毁的那场大火那样烧毁了这片土地。它们比1986年灾难以来的任何一次都要大得多,燃烧了几个星期,烧毁了近165,600英亩土地,最后降雨淹没了它们。
2000英里外的挪威的监测仪检测到大气中铯的含量增加。基辅笼罩在浓烟中。媒体报道估计,火灾附近的辐射水平比正常水平高出16倍,但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实际释放了多少:约申科、齐布采夫和其他迫不及待地进行实地测量的人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而被限制在家里。8月通常是切尔诺贝利火灾季节最糟糕的月份,今年,公众的焦虑情绪正在加剧。这场世界上最严重的核灾难留下的破坏正在与气候变化的灾难相撞,后果深远。
这是横跨乌克兰北部1000平方英里的森林、草原和沼泽的丰富马赛克。2013年,我参观普里皮亚特时,和其他许多参观者一样,我被废弃的家庭农舍震惊了,空窗上长出了树枝,孩子们在匆忙疏散的普里皮亚特市一个社区中心的墙上跳舞的画像让我震惊,他们的缺席仍然萦绕在他们的心头。但我也看到了点缀着幼小松树的草原,风吹过的黄褐色的谷头变得狂野,一只白尾鹰在发电厂冷却池上空翱翔。在一片土生土长的白桦树林里,我站在晨光中,它在明亮的白色树干上打磨树叶。我被迷住了--直到我的剂量计开始颤动。我后来意识到,如果我在那里逗留一个小时,我将暴露在超过人类安全标准100倍的辐射水平中。
从广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我们正在了解辐射对人体的可怕、挥之不去的影响。从切尔诺贝利无人居住的景观中,我们正在了解生态系统如何应对同样的无形侮辱,以及如何从这种无形的侮辱中恢复过来。
周游世界,看看海洋、草原、森林、沙漠、冰冷的两极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多读。
在1986年4月26日灾难后的混乱中,苏联官员疯狂地工作,以遏制从核电站4号反应堆喷出的辐射。为了保护公众健康,他们疏散了几乎相当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大小的区域。从那时起,只有那些获得许可的人才能进入这个隔离区,乌克兰人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疏离区。乌克兰法律规定,在辐射消散之前,没有任何东西-没有黑莓,没有蘑菇,没有放射性核素-离开该区域,考虑到钚-239的半衰期为2.4万年,这是一个长期的提议。
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一个巨大的、长期的生态实验室。在禁区内,科学家们正在分析一切,包括游荡回来的狼和驼鹿的健康状况,以及辐射对谷仓燕子、田鼠和分解森林凋落物的微生物的影响。现在,随着野火的恶化,科学家们正试图确定这些遭受重创的生态系统将如何应对又一次前所未有的破坏。
切尔诺贝利不是一片容易被烧毁的风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核电站建在欧洲最大的沼泽普里皮亚特沼泽(Pripyat Marshes)的西南边缘。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多水的地形几乎无法穿透;洪水让它一次有几个月无法通过,沼泽迷失了方向,持续不断的入侵者。较干燥的地区种有桦树、白杨、其他阔叶木和一些松树。19世纪末,这些森林被清理出来,用于集约化农业。但即使是最有事业心的农民也很难在沙质土壤上种植小麦和其他作物。
1922年乌克兰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后,政府将土地归还给森林,砍伐森林以获取生产玻璃和伏特加的燃料。但是,苏联林农没有自然地混合物种,而是种植了一排又一排均匀分布的苏格兰松树,在一片高度管制的森林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软木生产区。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些定期砍伐的松树种植园覆盖了现在的切尔诺贝利隔离区400平方英里的面积。
1986年摧毁核电站的爆炸改变了该地区的所有生命,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命。爆炸的直接影响造成31人死亡,仅在乌克兰就有多达15万人死于辐射暴露。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将再增加4.1万人;其他估计将超过100万人。这场灾难颠覆了那些幸存下来的人的生活:强制疏散35万人,迫使普里皮亚特的居民离开他们新建的城市,农民放弃他们的田地,伐木者到其他地方找工作。
受到核爆炸打击最严重的森林是一个松林,它直接矗立在最致命的碎片的路径上。松树对辐射极为敏感,死前就变成了铁锈橙色,工人们给这个种植园起了个绰号叫“红林”。作为遏制放射性物质的努力的一部分,他们用推土机将其推倒,将树木掩埋在500多万平方码的表土中,并用一英尺多的沙子覆盖了该地区。然后他们给它重新种上了松树。随着新树的生长,土壤中的辐射抑制了一种酶,这种酶对经典的单干针叶树形状有贡献,导致了一大片看起来怪异的、茂密的矮松树。
隔离区的其余森林都被简单地遗弃了。管理停止了,让高度工业化的森林以自己的速度以自己的方式进化。松树开始悄悄进入污染较少的农田。桦树和其他对辐射不太敏感的本土物种开始在较热的地区定居,慢慢取代了苏联林农如此青睐的苏格兰松。在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之前,森林覆盖了大约30%的隔离区,现在它们覆盖了大约70%。
灾难发生后不到两个月,苏联官员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旨在研究辐射对农业和生态的影响。1991年苏联解体后更名为乌克兰农业放射学研究所,我们掌握的有关受污染食品和放射性核素动态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在这里开发的。2012年,当我到达位于基辅西南郊区的研究所时,我被领着穿过一个雄伟的圆形大厅,在那里,美丽华丽的地板上松散的瓷砖为我提供了一种敲击的伴奏,我一遍又一遍地点击。当时47岁的瓦西尔·约申科(Vasyl Yoschenko)正在会议室里等待,在一张长桌周围踱来踱去,摆弄着眼镜。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左眼飘忽不定,这让他看起来有点鲁莽。
1986年春天,尤先科还是苏联军队的一名士兵,驻扎在莫斯科以东60英里处,“当然是为了防御美国,”他带着讽刺的笑容告诉我。灾难发生一个月后,当他的服役结束时,他很兴奋地回到基辅:“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尤其是在春天,所以想象一下我服了两年兵役后的感受。”相反,他发现了一座空荡荡的城市。街上唯一的人就是那些被雇来冲走他们的人。Yoschenko恢复了他的学业,1989年完成了硕士学位,并立即进入放射研究所工作。现在有了博士学位,他当时肩负着一个笨拙的头衔,即放射生态监测、数学建模和剂量学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为我简化了一下:“我研究辐射。”
该研究所最重要的早期任务之一是估计整个隔离区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在会议室里,尤先科指着两份装框的文件,上面覆盖着从淡绿色到尖叫的橙色的多边形颜色。这些地图制作于1997年和2000年,是第一批绘制灾难期间降雨的锶、钚和其他放射性核素矿床的地图。该研究所所长瓦列里·卡什帕罗夫(Valery Kashparov)与约申科等人发现,三分之二的污染物以及几乎所有的钚和锶都保留在乌克兰的土壤中。这让一些科学家大吃一惊,他们曾认为放射性核素会迅速进入地下水位,或者在爆炸产生的不稳定风中散落到世界各地。取而代之的是,高达96%的放射性核素活性被限制在最上面的10厘米土壤中。
在过去的30年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将切尔诺贝利的东西保留在了切尔诺贝利。但乌克兰禁止放射性核素移动的堂吉诃德式法律并不包含这些放射性核素。它们被正常运作的生态系统所控制。
从核电站爆炸出来的气体和碎片落在树木、草、其他植物和真菌上,覆盖着放射性核素;多达90%的污染是在松树和其他针叶树的树冠上捕获的。当它们的针落到地上时,它们就成为森林凋落物的一部分,慢慢地驱散了它们带入土壤表层的放射性核素。几年后,树木开始吸收这些放射性元素;因为铯和锶是钾和钙的化学类似物,约申科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毫无戒心的树木如何将它们当作营养物质,将它们吸收到根部并转移到树干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铯和锶在树木的针叶中积累,它们再次落到地面,成为森林凋落物的一部分。
没有树木或其他永久的地面
生存和控制辐射的能力现在正受到日益恶化的野火的威胁,气候变化加剧了野火的恶化。“森林在健康上是我们的朋友,在燃烧时是我们的敌人,”林学教授齐布采夫(Zibtsev)说。当切尔诺贝利的树木燃烧时,它们将储存的放射性核素以可吸入气溶胶的形式发送到高空。不像1986年那样,污染来自覆盖核电站周围约660平方英里的树木,而不是像1986年那样从单一来源爆炸。
灾难发生25年后,齐布采夫和其他人预测,如果隔离区的森林完全被大火烧毁,基辅居民死于癌症的风险将会增加,政府将需要对90英里外生产的食品实施禁令。尽管目前不太可能发生如此大而强烈的火灾,但最近的火灾规模足够大,足以造成类似的问题。Zibtsev说:“如果切尔诺贝利森林被烧毁,污染物将迁移到邻近地区之外。”“我们知道这一点。”
现年59岁的齐布采夫又瘦又瘦,浓密的灰色平头看起来总是完全长大了。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1986年夏天在户外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基辅。他患上了白内障,他怀疑是由辐射暴露引起的,尽管官方从未将其归因于此。两年后,来自德尼普罗州立大学(Dnipro State University)的森林生态学博士齐布采夫(Zibtsev)有机会在受辐射的森林中进行研究。他的父母担心他的安全,拒绝允许。他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没有必要拿我的健康冒险去研究放射性核素在临时废物储存点的迁移。”
他的事业停滞不前。“你不会拒绝这样的好机会,但我拒绝了,”他说。取而代之的是,他绘制了4号反应堆以西150英里(约合150公里)处的森林污染地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辐射释放的随机模式在那里沉积了放射性核素,使他暴露在他试图避免的危险中。1993年,另一个监测切尔诺贝利森林的提议出现了,这一次齐布采夫接受了。在接下来的五个夏天里,他收集了土壤和植被样本,随后进行了放射性核素的痕量分析。他在那里发现的辐射高于爆炸发生后不久的水平,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观察结果,直到约申科2003年的试验性烧伤解释了这一点:1992年,大火烧毁了1.25万英亩的土地,撕裂了树冠,并将炽热的灰烬倾泻到隔离区各处,这是灾难发生以来第一次失控的大火。
齐布采夫在2005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富布赖特奖学金时,了解到美国西部灾难性的野地大火。“如果那件事发生在这里怎么办?”他想知道。“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乌克兰。”齐布采夫开始唤起国际社会对火灾和辐射安全的兴趣。他在2007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表示,不仅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处于危险之中,其他国家的“遥远人群”也处于危险之中。他开始通过地区东欧火灾监测中心协调旨在提高野火管理能力的项目,该中心是他于2013年在全球火灾监测中心和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的保护下成立的。
2015年,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连串火灾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其危险的关注。到那时,废弃的森林里已经挤满了易燃的枯树,当开发区外的农民放火焚烧他们的田地-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农业做法-附近的树林很快就起火了。从4月到8月,禁区内有37,066英亩的土地被烧毁。Zibtsev和他的同事后来报告说,火灾期间该地区的辐射释放几乎是正常水平的10倍,切尔诺贝利和白俄罗斯森林的辐射水平在2015年几乎翻了一番。
由于担心欧洲上空可能发生火灾辐射泄漏,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聚集在切尔诺贝利的消防部队的悲惨状况。在隔离区,消防员监测1986年灾难前建造的摇摇欲坠的瞭望塔冒出的烟雾。通道正在恶化,经常被倒下的树木堵塞。尽管Zibtsev帮助设计了一个燃料中断系统,在植被中创造了缺口,但绝大多数从未建成。在隔离区拥有管辖权的三个机构之间几乎完全缺乏协调,这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齐布采夫说,面对政府不稳定、经济混乱以及与俄罗斯长达六年的战争,乌克兰官员没有精力、财力或政治意愿专注于切尔诺贝利的火灾。
在我2012年访问期间,消防员尼古拉·奥西延科(Nikolay Ossienko)带我参观了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帕里谢夫消防站(Paryshev Fire Station),这是隔离区的七个消防站之一。一队抛光良好但老化的4乘4英寸的消防车停在紧挨着一座木制建筑的棚子里,这座木制建筑被认为是
近年来,美国林业局的一个项目在禁区内安装了五个火灾探测摄像头,为切尔诺贝利消防员提供了保护装备和呼吸装置,并制定了火灾管理计划,以协调灭火工作。齐布采夫说,这非常有帮助,但并没有解决设备短缺的问题。今年4月,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教授蒂莫西·穆索(Timothy Mousseau)设置了相机陷阱,用来监控野生动物,拍摄了人们用湿抹布救火的照片。“没有衬衫,没有口罩,没有手套,只是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徘徊,试图把它扑灭,”他告诉我。
今年4月的大火烧毁了禁区23%的面积,是该地区有记录以来最大的烧伤,几乎是2015年火灾规模的4.5倍。大火烧毁了距离被毁的核反应堆不到三英里的树木,核反应堆现在被拱形的钢制裹尸布包围。
尽管大火使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暴露在危险的辐射水平下,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对该地区和其他地区居民的风险相对较低。但正如Zibtsev指出的那样,个人健康是许多因素的组合-食物、水、生活质量-任何辐射暴露的增加,无论多么微小,都会增加现有的压力。在他的办公室里,当他列举各种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时,他移动着面前桌面上的一个小盒子,离边缘越来越近。当他接受放射治疗时,它摇摇晃晃,准备掉到他的膝盖上。“太多的压力会加速死亡,”他说。
大火还给切尔诺贝利的生态系统带来了另一种压力,这显然是人类给他们从核灾难中恢复的漫长过程带来的一种痛苦。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由人类活动引发的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