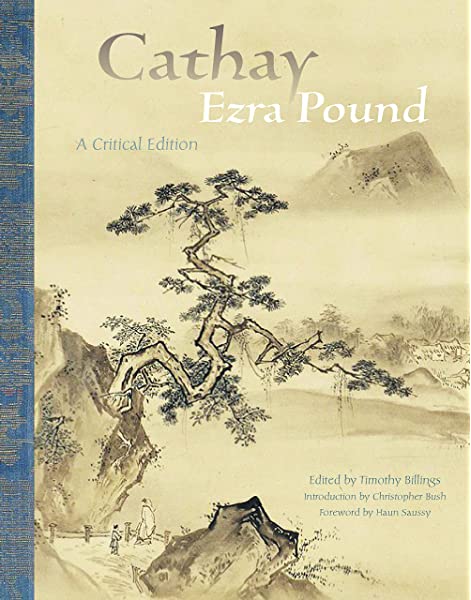与英镑纠缠不休
“国泰:埃兹拉·庞德的批评版”,蒂莫西·比林斯编辑。福特汉姆大学出版社,2019年。精装,364页,35美元。
“疯人院:埃兹拉·庞德的诗歌、政治和疯狂”,丹尼尔·斯威夫特著。法拉·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2017年出版,精装,320页,27美元。
我们要拿埃兹拉·庞德怎么办?一个答案是“取消”他,把他的雕像扔进河里,让水把它冲走。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称他的政治和个性令人反感是轻描淡写的。但这也太简单了。庞德的指纹随处可见:最著名的是在“荒原”上,但在叶芝、弗罗斯特、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和H.D.D.的职业生涯中也有。(希尔达·杜利特尔);关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出版;关于意象主义、狂想主义和一个世纪前出现在诗歌中的“新诗”。他无疑是二十世纪文学的关键人物之一。
如果我们必须和庞德生活在一起,那么必要的问题是如何:仅仅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参与者,还是作为文学的作者仍然值得一读?最近的两部非常不同的作品提供了自己接近他的方式。丹尼尔·斯威夫特(Daniel Swift)的《臭虫:埃兹拉·庞德的诗歌、政治和疯狂》(2017)引导着一批颇受欢迎的读者,尽管他们很有见识,但庞德在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被制度化了十年;而蒂莫西·比林斯(Timothy Billings)的《华夏:批评版》(2019年)则提供了一本经过仔细研究的文本指南,介绍了庞德1915年从中国诗歌中突破翻译(或称“翻译”)的写作。
“华夏诗集”的前言、引言和编辑介绍:批评版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诗歌本身当作庞德的作品来读,而应该“作为一系列汇编、注解和创造性重写的纽带”,与原著作者和调解庞德与他们相遇的许多人物进行“文本合作”。这种方法更狭隘的(也是公认的)目标是绕过关于庞德作为译者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的长期争论,而把重点放在他的文本翻译过程上-这一切都是最好的。但人们不禁注意到另一种效果:将诗歌与诗人分开,解散庞德的作者身份,以免除文字的责任。
比林斯进行了细致、详细和传统的文本研究:抄写、注释、校对。归根结底,这些努力掩盖了庞德独特的作者角色可能仅仅是文本传播中的一个偶然联系的概念。
斯威夫特在书中称,国泰“发明了现代主义诗歌”。就像所有关于现代主义起源的说法一样,这是对文学神话的夸大。但它的意义是值得的:在他们那个时代,这24个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古英语“海员”)翻译过来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晦涩难懂的古董作品。他们是活生生的诗歌--一种新的东西。当然,翻译在这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动词:庞德根本不懂多少中文。取而代之的是,他从美国艺术历史学家欧内斯特·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曾经跟随两名日本学者Umewaka Minoru和Mori Knan学习的笔记本中进行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批评家和学者一直在争论庞德的翻译方法、他的错误和他的发明,而没有仔细或系统地参考庞德工作的文件-尽管这些文件可以在耶鲁大学的特别收藏中找到。比林斯转录并组装了这些“婴儿床”,作为这本“华夏集”的后备材料,这本书是这本书的主要部分。版面确实呈现了一个多作者的快照:首先是汉字本身;下面是罗马字的音译;然后是字面定义的逐字注解;提供了整行意义的“释义”;最后是庞德发表的翻译。对于每首诗,这五层逐行重复,强调了比林斯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发现:庞德的翻译实践源于一种名为kundoku的传统日语阅读习惯,即注解阅读。欧内斯特·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的老师们采用了一个分三步走的过程:一次朗读一行;简明地解析每个字符,包括多种含义;为这行字创建一个通俗易懂的释义或翻译。结果,在笔记本中,注释和释义往往在设计上不一致。正如庞德翻译的那样,他在光泽方面犯了错误-导致了洞察力和错误的时刻。
比林斯称庞德的工作方法为“卡莱克”,即“一种词汇意义的转移,如此‘字面’地将它的异国性统一地强加于新的文本上”(The Calque),或“如此‘字面’地转移词汇意义,从而将其异国性统一地强加给新的文本。”在一个较小诗人的手中,这很容易就像庞德拒绝和咨询的十九世纪末华丽的习语翻译一样灾难性。盖伊·达文波特(Guy Davenport)在批评里士满·拉蒂莫尔(Richmond Lattimore)1967年翻译的荷马作品“另一个奥德赛”(Another Odysey)时指出,“翻译涉及两种语言;翻译者经常有可能创造出介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第三种语言,这是一种由原文建议的、不被原文转译成的语言所承认的危险的不存在的语言。”这就是庞德的镇定技巧--它突显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十心桥旁诗”的第三行,用费诺洛萨的笔调写道:“清晨成为切开/撕裂的肠花”(Fenollosa的光泽是这样写的:“清晨成为切开/撕裂的肠花。”套用一下,就是“早上开的花美得让人受不了。”这两句话都无法避免地引出庞德富于想象力的、独一无二的、但又高人一等的话:“早晨,这些花是用来切开心脏的。”
英语世界可能再也见不到像他这样的编辑了。他用拉丁文雕刻“向塞克斯图斯·普洛蒂乌斯致敬”的方法,用拉丁文翻译的荷马作品或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的书信中的各种诗章,或艾略特蜿蜒的“他用不同的声音做警察”中的“荒原”,推动了他在这里的过程。如果国泰真的发明了现代主义,那是通过磨练庞德的编辑能力。“国泰”的文本历史可能是复杂的,涉及多个声音的整理,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也是庞德独特而反复无常的天才的作品。
比林斯的英镑消失在文本历史中。斯威夫特根本就没有去过那里:在虫屋里,这位年迈的、制度化的诗人对那些来圣伊丽莎白拜访他的人来说是一个谜。与他的同代人(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新兴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休·塞德尔(Hugh Seidel))以及他的医生们的接触,指导着斯威夫特对庞德在那里十年的描述-以及其他从美国和意大利政治的新法西斯主义边缘漂移到舞台上的更短暂的人物。所有人都在庞德身上找到了他们想要(或许也需要)找到的东西:反抗诗意传统的典范、敌手、导师、也在与疯狂作斗争的老诗人、名人病人、经济和政治理论家,他的作品根除了高利贷者(犹太人、资本家、军国主义者、混血儿和更多的犹太人)的全球阴谋。就它提供的文学史上某个时刻的叙事快照而言,这是有价值的:庞德在20世纪50年代与其说是一个祖先,不如说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物体,比如奥兹曼迪亚斯的基座重现生机,或者《人猿星球》中被摧毁的自由女神。
但斯威夫特将他的研究描述为他自己试图与庞德一起访问-也是我们的。“圣伊丽莎白的庞德是二十世纪的核心之谜,”他写道,“庞德的矛盾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确定因素。“。但在260页之后,斯威夫特无法得出任何答案。庞德是自相矛盾的。他(和他的诗歌)可能不能被信任,但也不能被忽视。这本书的最后一幅画是庞德,1959年自由,等待BBC纪录片的导演告诉他该做什么:一个必须由其他人创造其意义的人物。庞德永远只是我们对他的评价。
这是所有世界中最糟糕的:一种无意中赦免庞德罪过的方式,同时却认为诗歌充其量只是次要于他传记中的空容器。斯威夫特犯了与庞德的许多客人相同的错误:他拜访了庞德,并希望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在新批评将作者和语境从考虑中剔除近一个世纪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将诗歌从属于心理、政治和人格。这不是斯威夫特的错;这既是许多文学批评的条件,也是我们当代将诗歌视为纯粹的“自我表达”的条件,一种在你所有的“个性”中“被倾听”的方式。
但如果我们完全诚实,斯威夫特将这首诗的重要性降至最低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庞德的大部分作品--包括几乎所有的诗章--根本不值得阅读,也不值得投入时间和学术资源。关于庞德政治的争论似乎常常是回避他的文学价值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他很重要,但他真的很棒吗?
所以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庞德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中心人物,如果没有他,长盛不衰的作品就不会有今天的样子。直到35岁左右,他一直是一位才华横溢、富有创新精神的诗人。但是,他将自己的声誉押在上面的“诗章”是失败的。现代主义学者劳伦斯·雷尼(Lawrence Rainey)称它们为“C
J·L·沃尔的诗歌和散文曾出现在“第一事物”、“现代”、“弧形数码”、“凯尼恩评论在线”和“美国”等杂志上。在推特上,他是@JL_WALL。
大学布克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使之成为可能的。本文中表达的任何观点、发现、结论或建议不一定代表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观点、发现、结论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