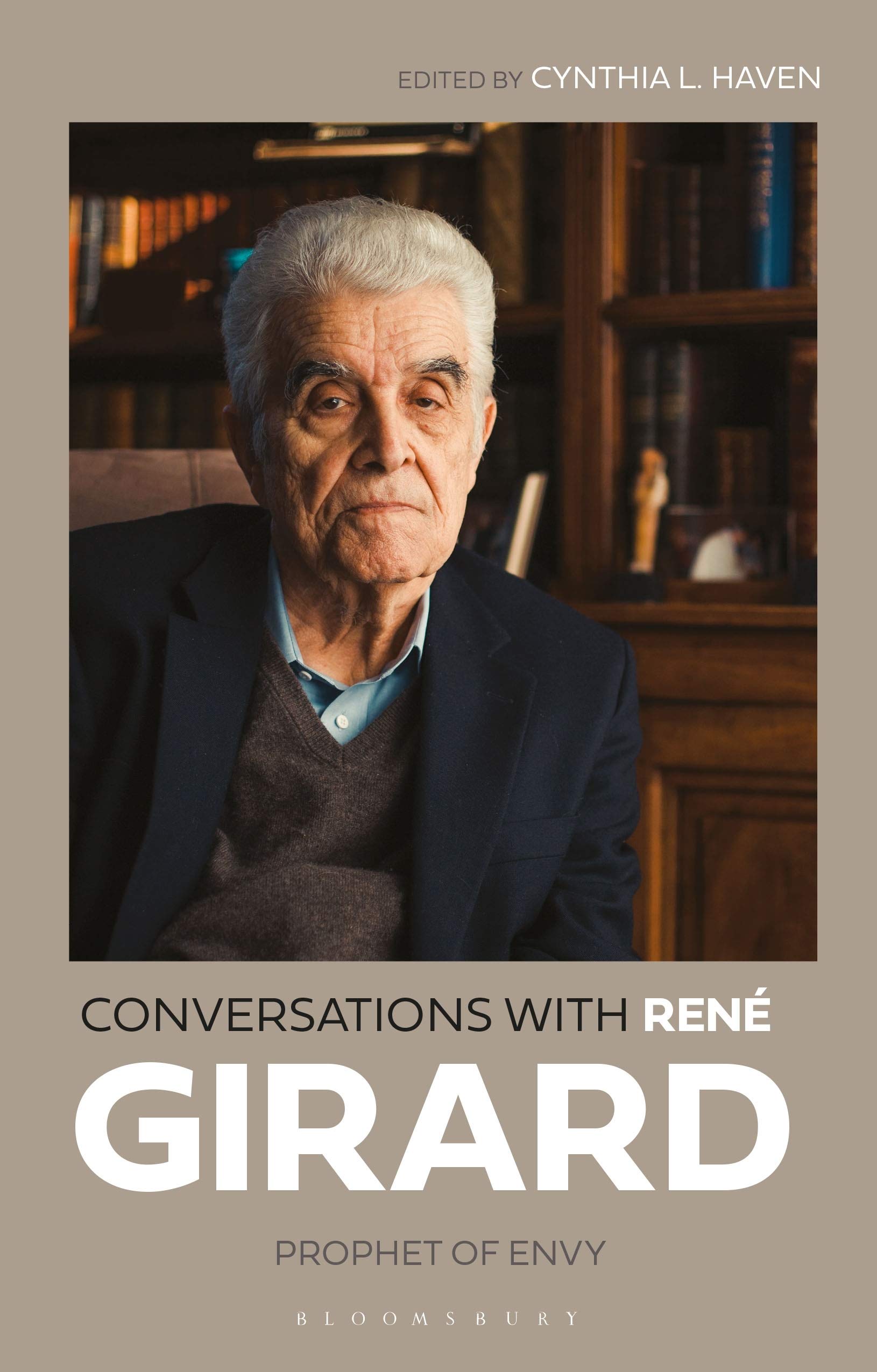刺猬的最后:勒内·吉拉德(RenéGirard)
1953年,以赛亚·伯林发表了他的长文“刺猬和狐狸”,概述了他现在著名的牛津剑桥变种:世界上有两种人。他取自帕洛斯的古代抒情诗人阿基洛库斯的一段模棱两可的片断:“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指出托尔斯泰的宏伟历史观和认为这种观点站不住脚的艺术气质之间的紧张关系,柏林的这篇文章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尽管与其说是因为它对俄罗斯文学的论证,不如说是因为它认为有两个对立的人物统治着思想世界:刺猬,他们按照某种包罗万象的体系来看待世界,认为所有的事实都符合宏伟的模式;狐狸,那些以知识分子或气质为理由拒绝“大理论”的多元主义者或特殊主义者。
柏林的类型学非常直截了当:也许比科学类型学更严肃的游戏,它只有在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发挥奇妙的作用。与法裔美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勒内·吉拉德(RenéGirard)合作,它效果很好。正如罗伯托·卡拉索(Roberto Calasso)所暗示的那样,吉拉德几乎是柏拉图式的刺猬理想:他属于19世纪和20世纪思想家的世系,他们巨大的人工野心现在被学院里的许多人视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几乎是不礼貌的。像他这样全面的智力项目今天给人的印象是天真的,甚至是压抑的,受到最令人厌恶的启蒙运动怀旧情绪的鼓舞。当然,提供这种判断的学者通常是那些自己的工作寄生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等大综合理论家的人。
与这些较年长的思想家一样,尽管吉拉德在重要方面与他们截然不同,但他不倾向于单纯的分类学工作,如结构主义分类或语言“主题”和“人物”的识别,而更感兴趣的是询问有关起源的大问题-宗教、语言、文化、暴力、人类精神生活的起源。尽管如今在人文科学学者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解释野心,但在当代科学家中却出人意料地普遍,他们对自己解决最感兴趣的重大问题的能力的焦虑要少得多-有人可能会说,焦虑不足。因此,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继续为我们这些不久前礼貌地离开这一领域的人写关于人性和文化的重大问题的惊人的不连贯的畅销书。无论这是因为我们人文科学中的我们不再发现这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在智力上站得住脚,还是(不那么恭维地)我们受到了那些使此类项目无法实施的制度和资金框架的制约,没有弗洛伊德、尼采或马克斯的一代可能有一天会成为我们会后悔的事情。(当然,除非我们现在满足于让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为我们所有人扛起旗帜。)。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吉拉德。在看似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形式--神话、仪式、禁令--背后,他著名地看到了一种惊人的统一,一套有限的模式,他假设其中一种模式是由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产生的:普遍模仿和集体暴力。吉拉德的人类概念是模仿人:人类是模仿者。被剥夺了统治大多数有意识生命的僵硬的本能脚本,人类反而是模仿机器,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模仿形式来居住在他们的文化和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可遗传的遗产,尽管不是以双螺旋形式进行的;不像蚂蚁丘,那些名副其实的昆虫杰作,人类的虚构并不是从某些染色体文字中衍生出来的。这种关于人类模仿的见解并不新鲜,从亚里士多德到加布里埃尔·塔德,都有类似的观点。但许多人认为,在吉拉德的工作之前,这一洞察力的最严重影响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
虽然在2005年11月,哲学家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带着令人屏息的法令欢迎他加入法兰西学院的所谓“神仙”行列,但“我是新人类科学的化身!”(Je vous Nomme désormais le nouveau Darwin des Science humaines!,Je vous Norme désormais le nouveau Darwin des Science humaines!)。[“我在此称你为人文科学的新达尔文!”],吉拉德在主流社会科学中留下的遗产相对较少。和弗洛伊德一样,他最终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当吉拉德是一名拥有现代史博士学位的初级学者时,他被要求向本科生教授法国文学,原因无非是他自己是法国人-有点像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因为出生证而被要求教授《论语》。吉拉德不得不站起来,想出一些话来,他很快就做了。
他的首部文学理论著作“M。
吉拉德的一篇著名论文与社会理论中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他认为人类冲突是我们无法应对差异的结果。吉拉德的论点是,相反的情况往往是正确的-产生冲突的不是差异,而是相同。这一事实通常只能在敌对者(他们之间看到各种激进的差异)的范围之外才能被感知到,这一事实意义不大;“差异”的意识形态不仅是理解冲突的一种手段,有时也是支撑冲突的主要神话之一。正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对殖民者最具挑衅性的往往不是被殖民者的差异,而是他们对平等的假定,他们对他者的拒绝。
当然,没有什么比认为自己与我们的对手没有什么区别更令人羞辱的了。但即使是恐怖主义,也不仅仅是基于感知到的差异,而是基于致命的对抗性对称。在本书收录的一次采访中,吉拉德反问道,9/11的袭击者是不是“本身就有一点美国血统”。毫无疑问,这些相似之处可能被夸大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而且是正确的--可能揭示的东西。毕竟,托马斯·杰斐逊所宣称的“自由之树必须不时用爱国者的鲜血来刷新”,与阿亚图拉·霍梅尼所断言的“只有不断地用烈士的鲜血哺育,伊斯兰之树才能生长”并无太大不同。
类似的挑衅行为在整个港湾的藏品中随处可见。在这些页面中发现的吉拉德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思想家,在一个政治身份变得如此同质化的时代,他的意识形态承诺很容易混淆,尤其是在他们退回到轻而易举的对立中。吉拉德是一位天主教徒,他批评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不足,赞扬理查德·道金斯,认为尼采对宗教的理解比19世纪神学中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深刻;他是一位理论家,有时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替罪羊,但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对他来说,经济不公正迫在眉睫,马克思主义者卢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对他的工作大加赞扬;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赞扬福柯对现代性的分析,同时也赞扬亚当。诸若此类。尽管他追求抽象,但吉拉德通常并不是这部片场的粉丝。
在整个系列中,吉拉德展示了令人钦佩的自嘲能力,对自己弱点的深刻洞察。他认为在他所描述的争斗之上或之外没有任何立场,甚至承认他自己喜欢模仿、好争辩的天性,有自己的替罪羊。他还表现出顽皮的幽默感。在他与法国编剧兼导演米歇尔·特雷格(Michel Tréguer)精彩的争吵中,吉拉德问道,特雷格为法国乡土主义辩护是否需要穿上传统的普罗旺萨尔服装,演奏木笛。这里展示的吉拉德是一位思想家,他可以批评自己的工作,可以发现过度强调和遗漏,一个似乎永远对挑战和变化持开放态度的人。在阅读他的专著时,人们可能会想象,吉拉德总是有一个故事要讲,并坚持下去,但显然不是这样。
在1978年出现在“变音”杂志上的一次引人入胜的采访中,吉拉德承认他的观点“与时代的普遍情绪格格不入”。自那以后,尽管所谓的“大历史”和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等哲学家提出的宏伟体系卷土重来,但这种情绪大体保持不变。但是,海文的书对于我们这些普遍主义理论容易引发蜂巢爆发的人来说,是一种受欢迎的补药。正如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曾经在谈到精神分析时所说的那样:“就像所有的本质主义理论一样,”它“把可能只是一个不错的公司的东西变成了狂热的崇拜”。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吉拉德最重要的智力项目,毫无疑问,他往往是真正的优秀公司,正如这本藏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