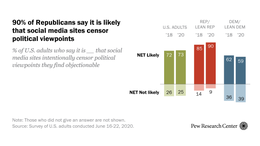中国的恐吓运动是针对美国公民塞缪尔·朱(Samuel Chu)的
塞缪尔·朱(Samuel Chu)习惯了他的手机在半夜变得无赖,嗡嗡作响,要求他注意。他是香港民主的倡导者,但他住在洛杉矶。时差意味着,当新闻传回中国时,他通常都睡得很熟。因此,当他的手机几周前开始响起时,他大多试图忽略它,但事实证明,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朱发出逮捕令的“突发新闻”。朱是美国公民。但他的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Hong Kong Democratic Council)在华盛顿倡导香港抗议者。朱的逮捕令是根据香港新的安全法发出的,这项法律适用于外国公民,即使他们在外国领土上。
我和朱谈到了登上中国的黑名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的活动家教育是如何让他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的。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的对话经过了编辑和浓缩。
玛丽·哈里斯:那晚你是怎么知道逮捕令的?
朱塞缪尔:当我终于不厌其烦地拿起我的手机时,我意识到有突发新闻。只是一条不同的突发新闻,因为出现在突发新闻上的是我的名字。直到几分钟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好的。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事实上,在国家安全法通过后,我与某人交谈,他们开玩笑说,塞缪尔,这部法律是他们为你写的。
他们读到其中一些条款几乎是针对像我这样的人和组织。“在法律上,逮捕令对我没有任何帮助。”事实上,老实说,我甚至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签发逮捕令。我是说,他们会发短信给我吗?他们会给我发电子邮件吗?他们又不是真的能在美国领土上签发逮捕令。
这一定让你觉得有点疯狂,不过,你会想,这是不是真的发生了?这不是真的吗?
我认为这是策略的一部分。这里的现实情况是,这不仅仅是一份传统的、常规的逮捕令。它应该牵连到所有人和任何跟我有联系的人。这是一系列你不一定能看到的更大的连锁反应。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与美国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只是在美国这里的普通美国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或与我一起工作的人。即使它们与香港没有任何联系,但它们现在与我相关的事实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它们会被审查吗?他们会被列入黑名单吗?
89年5月,当第一次百万香港人游行发生时,我就在那里。
我11岁的时候,那些照片和记忆对我来说是灼热的,就像作为一个香港人意味着什么一样。
香港人聚集在街上,表示对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支持。在北京的人群被军队强行驱散后,你父亲帮助中国活动人士经由香港逃往西方。
这是一次走私行动,估计帮助500名持不同政见者逃离广场或该国其他地区。他们将他们偷渡到香港,并将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地方,然后通过谈判将他们安全地送往西方国家。
这听起来不像是安全的工作。你知道你的家人在做什么吗?你知道这样做的风险吗?
是的,百分之百。实际上,我父亲过去常常在周末带我去安全屋,所以我实际上有机会和许多从中国偷渡到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呆在一起。我还记得周末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踢足球,当他们等待证件和旅行证件时,我看着和听着我父亲试图安抚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对我发出逮捕令并不让我感到震惊。我意识到了巨大的风险和每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代价,包括我的家人,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的父亲。而这一直是持续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父亲在89年就在那里。去年,我参加了对我父亲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审判。去年我在法庭上,这一次在香港,他们以基本上组织抗议的罪名对我父亲和其他八人进行了审判。所以我认为有一种非常根本的意识,这对一个家庭和我们认识的人个人造成了巨大的后果,而且它可能不仅会危及生命-你可能会冒着坐牢的风险-而且这会影响到我们联系到的每个人。
去年,我采访了一位曾在香港担任教授的女性,她写了一篇文章,她基本上是说:香港抗议者会输,但他们无论如何都应该继续抗议,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但我们好像到了这堵墙。就像上个月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样,人们的政治言论受到限制似乎是如此极端。你认为未来几周、几个月、几年香港的抗议活动会是什么样子?
我对香港人怀有极大的尊重和信心,因为我认为你们已经看到,即使从2014年到去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香港人的抵抗。如果你认为这次镇压会以某种方式限制抵抗的声音和表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已经看到人们想方设法表达不满的巨大创造力和韧性。人们四处走动,举着白纸表示抵抗,因为他们不能再展示任何口号、标志或图案。我毫不怀疑,过去一年表现出的弹性将会继续下去。北京的中国政府必须明白的一件事是,这不像他们曾经做过的任何其他镇压行动。你不能把在香港世世代代自由生活和呼吸的750万人重新放回一个受控制的铁幕式的环境中。这就像在你打开电视并把他们放在电视前面之后,告诉你的孩子,电视不存在。
你们成立香港民主委员会还不到一年。你在社会正义运动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成立这个倡导组织对您来说很重要?
我的职业生涯是建立在你如何从草根抗议转向真正的永久政治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上的。从本质上说,你是如何为目前没有权力的人建立权力的?
你在那里的工作主要是游说华盛顿,对吗?确保香港的这些抗议者在国会有发言权。
一点儿没错。我们需要在华盛顿有一个永久性的存在,这样才能真正转化出香港抗议活动正在产生的巨大善意、灵感和可信度。既要翻译它,又要重新架构它,这样它才能真正直接影响美国的政策。这就是缺失的部分。如此多的人关心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并热爱香港。但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只是不像我那样了解和理解美国政治。因此,我认为那里有义务为香港的这场运动创造美国的声音,事实证明,这对通过实际的立法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拍照、抗议和集会。
令我震惊的是,你们在特朗普总统任期中途创建了这个组织,因为那是我们与中国关系大规模重置的中期。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谈谈在这个时刻做你的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比如你与谁合作,你信任谁?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是为数不多的坚定而强烈的无党派和两党合作的政治工作者之一。香港一直是两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设法保持了压倒性的两党支持。最近,鉴於不断升级的迫害,我们一直致力为香港人争取移民和难民保障。我们现在可以在国会提出两党合作的移民和难民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一个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在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看到获得支持的情况下,移民仍然是最后一件事。
是不是有点像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想,我想你一定会在政府用恐惧和民族主义的语言谈论中国的时候苦苦挣扎。你一定很难接受这一点。
对我来说,这并不新鲜。问题和事业总是被政客和政党拉拢和利用,作为他们激励基础的方式。我不是纯粹主义者,也不是空想家。我相信人们总是出于错误的原因做正确的事情。我不需要他们出于正确的理由去做这件事。
使用下面的播放器收听整集,或者订阅苹果播客、阴天播客、Spotify、Stitcher或任何你可以获得播客的地方的下一集内容。
像您这样的读者使我们的工作成为可能。帮助我们继续提供您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报道、评论和批评。
加入Slate Plus。
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