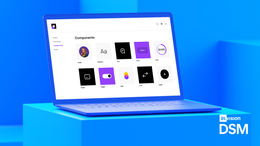系统和约束
这次采访是关于艾丽西亚·华雷罗思想的一篇文章的补充,那篇文章也发表在“大桥”上。
Alicia Juarrero是华盛顿特区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Vector Analytica,Inc.的创始人和总裁。她的著作包括“行动中的动力:作为复杂系统的意向行为”(1999)和即将出版的“复杂性与约束:上下文如何改变一切”(The Complex and Constraint:How Context Changes Everything);她的许多论文可以在她的网站www.aliciajuarrero.org上找到。华雷罗曾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社区学院教授哲学,并曾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和英国达勒姆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她在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的迈阿密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最近,Juarrero采访了Mercatus中心的访问研究员Martin Gurri。为了清楚起见,这份他们的谈话记录经过了轻微的编辑。
Martin GURRI:在你们的术语中,制度可以被描述为奇怪的吸引者,它们将系统行为约束到特定的结果。如果我们以现代政府为例,你会说这些制度约束是内在的稳定还是不稳定?是什么决定了系统内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
Alicia JUARRERO:像机构这样的复杂系统是层级纠缠的网络-跨越空间和时间尺度的纠缠。网络嵌套在网络中,而网络又嵌套在更广泛的网络中。我认为重要的是使用术语系统来表示整体:既有个体的,也有较小的参与者,以及更大、更持久的动态(吸引子),这些参与者都被卷入其中。
我认为一个较大机构内的系统稳定性,更多的是两者之间的连贯性或适合性的问题。符合适合性的意义,而不是旧时达尔文对最快或最高效等的解释。你永远不会想要一个完全符合的、连贯的、因此是稳定的系统(这就是停滞和死亡)。但是,一个系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并因此持久,需要一定的(未指明的!)。与其说是稳定,不如说是韧性。我确实认为,世界发现自己处于历史的某个时刻,由于同时出现的各种原因,两者之间的契合度非常紧张。
GURRI: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案例(我已经详细说明过了),我们从20世纪继承下来的机构已经陷入了终极危机的状态:它们正处于你们所说的相变的阵痛中。坚持以现代政府为例,你会在一个系统中寻找哪些要素来决定转型的结果?阶段后的变化结果(在我们的例子中,是转型中的政府)可以以任何方式预测吗?
JUARRERO:我们不能提前知道它是否是末日,因为我们不能详细地预测复杂的系统,除非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即使到了那时,也只能在它们处于稳定状态的时候。你无法预测,因为它们是非线性的,对初始条件和一般情况等很敏感。--艾丽西亚·胡雷罗(Alicia Juarrero)
一旦复杂系统达到不稳定的临界值,就可能有三种选择:适应、进化或解体。永远不能保证整体不会崩溃,如果我们不能适应和发展以实现新的一致性或契合性,它就会崩溃。我认为适应是在给定的可能性空间内的修改。您可以扩展自适应能力,也可以在该自适应空间内移动到更稳定的位置。
因此,如果我们调整能力,使其能够处理当前较高的扰动幅度和频率,我们就已经适应了。例如,建议像石油储备这样的国家储备卫生应急设备就是扩大适应能力的一个例子。正在进行的流行病学监测(如斯德哥尔摩范例提出的监测)将是另一个。
另一方面,我设想进化是对整个可能性空间的全面重新配置,这样它就会变得具有全新的参与者(角色)和模式。一些人争辩说,按照这个标准,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不是美国革命。实际上,这样的重新配置更容易发现。脊椎动物的进化、语言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就是四个例子。
全新的技术有能力影响这种全面的相变。但一组新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关闭也是如此。不过,解决这一问题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特别是在社会制度方面。
GURRI:一旦相变开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或至少影响相变的结果?有没有办法从内部重塑或改革现代政府这样的制度?在这一努力中,一个威权政府(例如,中国的政府)是否会比一个更喧闹、更混乱的民主国家更具优势呢?
JUARRERO:相变的方向和速度取决于当前环境是否会出现并放大任何新的涨落,从而成为相变本身的形核。我们对如何检测和管理这种波动的时机知之甚少。
我认为威权政府可以打压,从而强制实施维持现状的约束-但我不知道有任何情况下,新的一致性从自上而下的策略演变而来,更不用说强硬的策略了。我怀疑,与允许更早发生变化相比,压制时间过长会导致更剧烈的相变。我会把我的长期赌注押在印度,而不是中国-当然,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美国的变革能力。
但是进化的剧变并不美观,也不令人愉快。唉,创造性的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摧毁了很多。我们可以寻找一些方法,让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人变得更容易,而不是试图阻止过渡。
古瑞:您说过,奇点是触发相变的独特事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将事件识别为奇点?从这个角度看,大流行危机在您看来是什么样子?马丁·古里(Martin Gurri)。
JUARRERO:在我看来,奇点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触发相变。。。但只有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在其他情况下,同样的事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忘记了时间约束--时间--在复杂系统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只能催化而不能指挥阶段变化,所以在变化的时间窗口中识别并采取行动-如果不加以利用可能会关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还没有得到太多的探索。
我确实认为一种可能有用的管理技术是确定我们希望看到变化发生的方向的小型实验,并通过提供资源使它们蓬勃发展来放大这些实验。美国的联邦组织有效地将这种可能性制度化。做同样事情的另一种方式是放松阻碍新思想放大的管理约束。同样,自下而上的波动比自上而下的波动更有可能成功。但过于严格的自上而下的约束将阻止来自地方层面的创新冒泡。
当一个复杂的系统失去补偿时,发生的剧烈波动和振荡--发生的频率更高,幅度比系统的特征更大--往往先于相变。支配整个系统的约束条件的完全瓦解(比如摧毁恐龙的流星撞击,或许还促成了寒武纪的爆发,或者罗马的陷落)也可能导致相变。但复杂的系统通常会优雅地退化-它们会经历一段失代偿期;它们是功能失调的,但还不是没有功能-在完全崩溃之前。
要判断这场大流行是否构成将导致相变的奇点,需要比任何人都拥有的更宽广的视角。
GURRI:你描述了一种在局部和系统之间的舞蹈。一件地方性的事件有时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世界各地都能听到枪声”。你能从明尼阿波利斯一名警察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后的抗议活动的角度对此发表评论吗?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我们能确定影响是永久性的,而不是一时的产物?
朱瑞罗:康德把那支舞描述得比我好得多。他说,树是由树叶产生的,然后又产生树叶-各个部分相互作用,产生一个新的整体,然后循环回来产生这些部分。他说,这种部分到整体和整体到部分的影响“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因果关系。”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太理解部分和整体之间的递归因果关系-当然不是在人类组织中。
再说一次,时间是在这些动态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限制因素,也是我们在人类组织中不太理解的一个限制因素。我们在某些动力学方面是这样做的:想象一个孩子的秋千。重要的不是孩子踢得多用力才能把秋千踢得更高,而是孩子踢的时候。因此,上下文依赖对于一个事件是否能够产生全球影响至关重要。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事件发生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在大流行导致的数周封锁之后;与特朗普(而不是奥巴马)在白宫;在每个人都有带摄像头的手机的时候。但复杂系统的相变只能在回顾中才能理解;它们不能像几个世纪后精确的第二次日食那样详细地预测。我们美国人喜欢“这次不同”的想法,但我们只有回首往事才能说出这一点。
JUARRERO:我的论文是关于“道德行为的解释和辩护”。解释行为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一些事情。在眨眼的情况下,解释是直接的机械原因:吹到我眼睛里的灰尘导致我眨眼。另一方面,对眨眼的解释并不直接屈服于这种原因--解释更像是“我的眨眼意图导致了我这样做”。。。.“。同样的,“我举起手臂”和“我的手臂抬起”也是一样。后者可以用痉挛抽搐、插入电极等来解释。另一方面,“我举起手臂”则暗含有意之意。
那么意图是如何导致行为的呢?这就是我自论文发表以来一直感兴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