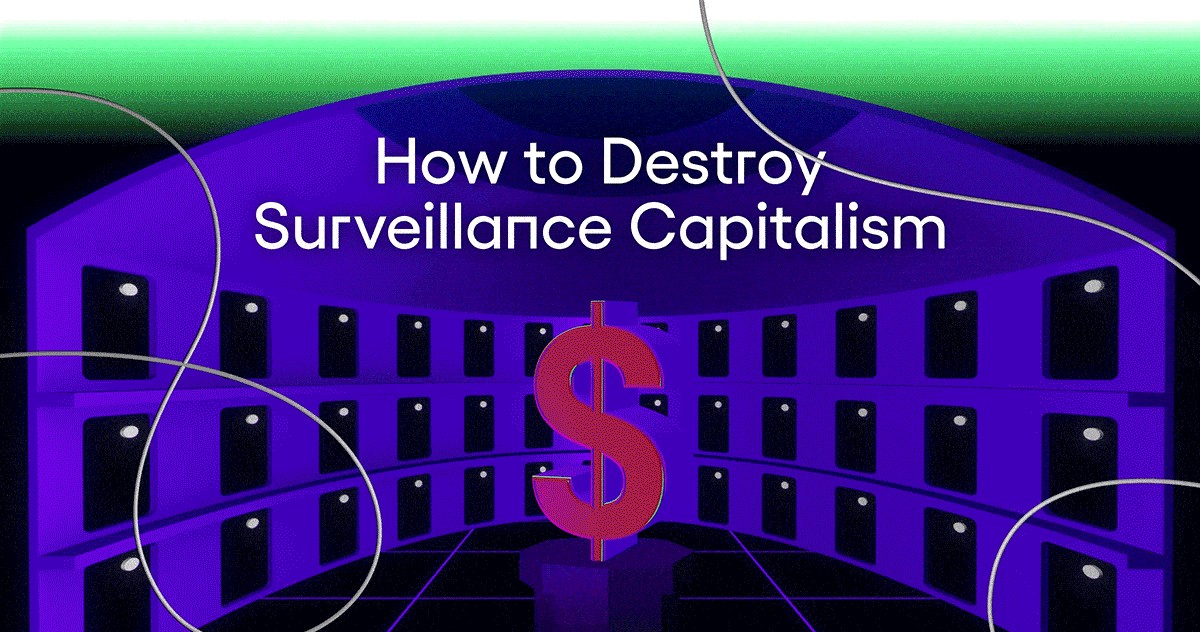“如何摧毁监视资本主义”,这是一本书长的对S·祖博夫(S.Zuboff)的反驳
编者按:监督资本主义无处不在。但这并不是某些错误的转弯或流氓滥用公司权力的结果-这是系统按预期运行的结果。这是科里·多克托罗的新书的主题,我们很高兴能在OneZero上完整出版这本书。这就是摧毁监视资本主义的方法。
关于平坦地球人在21世纪的重生,最令人惊讶的是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是如此普遍。你可以理解,几个世纪前,那些从未获得足够高的观测点来观察地球曲率的人,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常识,即看似平坦的地球确实是平坦的。
但是今天,当小学照例从气球上悬挂GoPro相机,并将它们升空到足以拍摄地球曲线的高度时-更不用说从飞机窗户看到弯曲的地球的平凡景象了-需要做出英勇的努力才能维持世界是平的这一信念。
白人民族主义和优生学也是如此:在这个时代,你可以通过擦拭脸颊并将其与适量的钱一起邮寄给基因测序公司,成为计算基因组学的数据点,在这个时代,“种族科学”从未像现在这样容易反驳。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既有现成事实又有否认事实的黄金时代。在边缘徘徊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可怕想法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主流。
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想法流行起来时,只有两件事可以解释它的优势:要么是表达这个想法的人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方面变得更好了,要么是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这个主张变得更难否认。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让人们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我们可以让一群Greta Thunberg在讲台上发表雄辩的、充满激情的论点,赢得我们的心,或者我们可以等待洪水、火灾、烈日和流行病为我们辩护。在实践中,我们可能不得不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越是沸腾、燃烧、溺水和消瘦,世界上的格里塔·通伯格(Greta Thunbergs)就越容易说服我们。
反对接种疫苗、否认气候、地球平坦和优生学等令人讨厌的阴谋的荒谬信念的论据并没有比一代人之前更好。事实上,它们更糟糕,因为它们被推销给至少对反驳事实有背景意识的人。
自从第一批疫苗问世以来,反VAX就一直存在,但早期的反VAX人士向那些甚至连微生物学最基本的概念都不太了解的人推销,而且,这些人还没有亲眼目睹小儿麻痹症、天花和麻疹等大规模杀伤性疾病的灭绝。今天的反恶作剧者并不比他们的前辈更有说服力,他们的工作也要艰难得多。
那么,这些牵强的阴谋论者是否真的能基于优越的论据而成功呢?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机器学习和商业监视可以把即使是最笨手笨脚的阴谋论者也变成一个狡猾的人,他们可以扭曲你的看法,通过找到脆弱的人,然后用人工智能精致的论点向他们推销,绕过他们的理性能力,把普通人变成扁平的地球人、反流氓,甚至纳粹,从而赢得你的信仰。当兰德公司指责Facebook是“激进主义”,当Facebook在传播冠状病毒错误信息方面的角色被归咎于其算法时,隐含的信息是,机器学习和监控正在导致我们对什么是真实的共识发生变化。
毕竟,在一个像Pizzagate和它的继任者QAnon这样杂乱无章的阴谋论拥有广泛追随者的世界里,肯定有什么事情在酝酿之中。
但如果有另一种解释呢?如果是物质环境,而不是争论,对这些阴谋推销员产生了影响呢?如果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真实阴谋的创伤-富人、他们的游说者和立法者之间的阴谋,掩盖不方便的事实和不法行为的证据(这些阴谋通常被称为“腐败”)-使人们容易受到阴谋论的影响,那该怎么办?
如果是创伤而不是传染-物质条件和意识形态-造成了今天的不同,并在容易观察到的事实面前促成了令人厌恶的错误信息的上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计算机网络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仍然在做着繁重的工作,定位弱势群体,引导他们通过一系列越来越极端的想法和社区。
对阴谋的信仰是一场熊熊大火,已经对我们的星球和物种造成了真正的破坏和真正的危险,从拒绝接种疫苗引发的流行病,到种族主义阴谋引发的种族灭绝,再到否认引发的气候不作为导致的地球崩溃,不一而足。我们的世界着火了,所以我们必须扑灭大火--找出如何帮助人们通过他们被迷惑的阴谋来看到世界的真相。
但是灭火是被动的。我们需要防火设备。我们需要打击使人们容易受到阴谋蔓延的创伤的物质条件。在这一点上,科技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解决这个问题的提案不在少数。从欧盟的恐怖主义内容监管规定,要求平台监管并删除“极端主义”内容,到美国提议迫使科技公司监视用户,并要求他们为用户的不良言论承担责任,有很大的能量迫使科技公司解决他们制造的问题。
然而,这场辩论中遗漏了一个关键的部分。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假设科技公司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对互联网的主导地位是一个永恒的事实。用一个更加分散、多元化的互联网取代大型科技公司的提议无处可寻。更糟糕的是:今天摆在桌面上的“解决方案”需要大型科技公司保持规模,因为只有非常大的公司才能负担得起这些法律要求的系统的实施。
如果我们要走出困境,弄清楚我们希望我们的技术是什么样子是至关重要的。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正在试图弄清楚,我们是想修复主导我们互联网的大型科技公司,还是想通过摆脱大型科技公司的束缚来修复互联网本身。我们不能两者兼得,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我希望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驯服大型科技公司是修复互联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此,我们需要数字权利激进主义。
数字权利激进主义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今年就满30岁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成立于1985年。在这场运动的大部分历史中,针对它的最突出的批评是它无关紧要:真正的激进主义原因是现实世界的原因(想想2010年芬兰宣布宽带是一项人权时的怀疑主义),而现实世界的激进主义是鞋皮激进主义(想想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对“点击主义”的蔑视)。但随着科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无关紧要的指责首先让位于缺乏诚意的指责(“你只关心科技是因为你在为科技公司赚钱”),让位于疏忽的指控(“为什么你没有预见到科技可能是一股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但数字权利激进主义一如既往:在一个科技正在无情地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里,为人类着想。
这一批评的最新版本以“监督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商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她2019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长书“监督资本主义的时代:新权力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The Age of SurveMonitoring Capitism: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中创造的一个术语。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是科技行业独一无二的产物,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滥用的商业行为,它“由意想不到的、往往难以辨认的提取、商品化和控制机制构成,这些机制有效地将人们从自己的行为中流放出来,同时产生了新的行为预测和修改市场。”监督资本主义挑战民主规范,在关键方面与市场资本主义长达数百年的演变背道而驰。它是一种新的致命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一种“流氓资本主义”,我们对其独特能力和危险的缺乏理解代表了一种关乎生存和整个物种的威胁。她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威胁着我们的物种,她说科技给我们的物种和文明带来了独特的挑战,这是对的,但她关于科技的不同之处以及为什么它威胁我们的物种的说法是真的错了。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她的错误诊断将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最终让大技术公司变得更强而不是更弱的道路。我们需要拿下大型科技公司,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正确识别问题开始。
数字权利运动的早期批评者--或许最好的代表是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等活动组织,以及其他专注于维护和加强数字领域基本人权的组织--谴责那些践行“技术例外论”的活动人士。在世纪之交,严肃的人们嘲笑任何声称科技政策在“现实世界”很重要的说法。声称科技规则对言论、结社、隐私、搜查和扣押以及基本权利和股票有影响的说法被认为是荒谬的,这将公告牌系统上争论《星际迷航》的悲伤书呆子的担忧提升到了自由骑士、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或华沙犹太人区起义的斗争之上。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科技在日常生活中作用的扩大,对“科技例外主义”的指控只会变得更加尖锐:现在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网络生活已经被少数巨头垄断,数字自由的捍卫者被指责为大型科技公司提供了水,为其自私自利的疏忽(或者更糟糕的是,邪恶的阴谋)提供了掩护。
在我看来,数字权利运动一直停滞不前,而世界其他地区却在移动。从最早的时候起,这场运动的关注点就是用户和工具工,他们提供了实现自己基本权利所需的代码。数字维权人士只关心公司,因为公司是为了维护用户的权利而采取行动(或者,同样经常的是,当公司如此愚蠢地采取行动,威胁要出台新的规则,这也会让优秀的演员更难帮助用户)。
“监视资本主义”的批评再次以新的视角重塑了数字权利运动:不是作为高估其闪亮玩具的重要性的危言耸听者,也不是作为大型科技公司的闪光点,而是作为平静的甲板椅重整者,他们长期的行动主义是一种负担,因为这让他们在继续打上个世纪的科技战时,无法感知新的威胁。
你可能听说过“如果你不为产品买单,你就是产品”。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是正确的,如果不完整的话。但绝对正确的是,广告驱动的大技术公司的客户是广告商,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卖的是说服你购买东西的能力。大科技的产品是说服力。这些服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地图、消息等-是说服的传递系统。
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恐惧始于这样一种(正确的)假设,即大技术公司关于自己所说的一切可能都是谎言。但监视资本主义的批评对大技术公司在其销售手册中的说法是一个例外-在向潜在广告商推销其产品的功效时,在线和广告技术研讨会上对其进行了令人窒息的炒作:它假设,大技术公司在向轻信的客户销售有影响力的产品时,就像他们声称的那样善于影响我们。这是一个错误,因为销售资料并不是衡量产品功效的可靠指标。
监视资本主义假设,因为广告商购买了大量大技术公司正在销售的东西,所以大技术公司肯定在销售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是,大型科技公司的巨大销售额很可能是流行的错觉或更有害的东西造成的:对我们通信和商业的垄断控制。
被监视会改变你的行为,而不是变得更好。它给我们的社会进步带来了风险。祖博夫的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精美的解释。但祖博夫也声称,监控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当我们的个人数据与机器学习混合在一起时,它创造了一个毁灭性的说服系统,以至于我们在它面前无能为力。也就是说,Facebook使用一种算法来分析它非自愿地从你的日常生活中提取的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来定制你的订阅源,让你可以购买东西。这是20世纪50年代一本漫画书中的一条精神控制射线,由疯狂的科学家挥舞着,他们的超级计算机保证了他们永久和全面地统治世界。
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不应该担心精神控制射线,而是为什么你应该担心监视和大技术,我们必须从我们所说的“说服”开始。
谷歌、Facebook和其他监控资本家向他们的客户(广告商)承诺,如果他们使用机器学习工具,这些工具针对无法想象的大量非自愿获取的个人信息进行培训,他们将能够发现绕过公众的理性能力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的方法,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购买、投票和其他期望的结果。
支配的影响远远超过操纵的影响,应该是我们分析和寻求任何补救措施的核心。
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取而代之的是,监视资本主义向其客户提供的预测要平淡无奇得多。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监控资本家并没有想方设法绕过我们的理性能力,而是大多做以下三件事中的一件或几件:
如果你在卖尿布,如果你把它们推销给产房里的人,你会有更好的运气。并不是每个进入或离开产科病房的人都刚刚生过孩子,也不是每个刚生过孩子的人都在市场上买尿布。但是,在尿布市场上有孩子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相关性,而住在产科病房与生孩子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产房周围的尿布广告(甚至还有婴儿产品的代言人,他们拿着装满免费赠品的篮子出没在产房)。
监视资本主义正在分割数十亿倍。尿布销售商可以远远超越产科病房里的人(尽管他们也可以通过基于位置的移动广告等方式做到这一点)。他们可以根据你是否正在阅读关于育儿、尿布或许多其他主题的文章来瞄准你,而数据挖掘可以提出一些不明显的关键字来做广告。他们可以根据你最近读过的文章来锁定你。他们可以根据你最近购买的东西来锁定你。他们可以根据你是否收到关于这些话题的电子邮件或私人消息,或者即使你大声谈论这些话题(尽管Facebook等公司令人信服地声称这还没有发生)来锁定你。
它不会剥夺你的自由意志。它骗不了你。
想想监督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政治中运作的。监视资本主义公司向政治操纵者出售定位可能接受他们推销的人的权力。竞选金融业腐败的候选人寻找与债务作斗争的人;竞选仇外心理的候选人寻找种族主义者。政治人员总是针对他们传达的信息,无论他们的意图是光荣的还是不光彩的:工会组织者在工厂门口设置摊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在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会议上分发传单。
但这是一种不精确的做法,因此是浪费的。工会组织者不知道在走出工厂大门的路上应该接近哪个工人,可能会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一个秘密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成员身上;白人至上主义者不知道伯彻夫妇中有哪些人如此妄想,以至于他们只能参加一个会议,而哪些人可能会被说服穿越全国,携带提基火炬穿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街道。
因为目标可以提高政治宣传的收益,它可以加快政治动荡的步伐,因为它可以让每个私下希望推翻独裁者-或者只是一个11届在任政客-的人都能以非常低的成本找到其他所有有同样想法的人。这对最近的政治运动的快速结晶至关重要,包括“黑人生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以及在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游行的极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等不那么有味道的参与者。
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政治组织与影响力运动区分开来;找到暗地里同意你的人并不等同于说服人们同意你的观点。非二元或不一致的性别认同等现象的兴起,往往被反动派描述为在线洗脑运动的结果,这些运动让易受影响的人相信,他们一直在偷偷地做同性恋。
但那些站出来的人的个人描述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那些长期对自己的性别隐藏秘密的人,被其他站出来的人所鼓励,那些知道自己不同,但缺乏讨论这种不同的词汇的人,从这些低成本的找人和了解自己想法的方式中学到了正确的词。
谎言和欺诈是有害的,监视资本主义通过目标来加强它们。如果你想出售欺诈性发薪日贷款或次级抵押贷款,监督资本主义可以帮助你找到既绝望又不老练的人,从而接受你的推销。这解释了许多现象的兴起,比如多层次营销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关于潜在收入和销售技巧有效性的欺骗性声明是针对绝望的人的,方法是针对搜索查询进行广告,例如,搜索查询表明有人在与不明智的贷款作斗争。
监视资本主义还通过使定位其他同样被欺骗的人变得容易,从而助长了欺诈,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错误信念的人的社区。想想那些受到多层次营销诈骗的受害者的论坛,他们聚集在一起交换关于如何改善他们在兜售产品时的运气的提示。
有时,网络欺骗涉及用不正确的信念取代某人的正确信念,就像反疫苗运动中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一开始相信疫苗,但却被看似可信的证据说服的人,这些证据导致他们错误地相信疫苗是有害的。
但是,当欺诈不一定要取代真正的信仰时,欺诈成功的情况要普遍得多。当我女儿在托儿所染上头虱时,一位托儿所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可以用橄榄油治疗她的头发和头皮,这样就可以把虱子除掉。我对头虱一无所知,我以为托儿所的工作人员知道,所以我试了试(它不管用,也不管用)。当你根本不知道更好的东西时,当这些信念是由一个似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人传达的时候,很容易导致错误的信念。
这是有害的,也是困难的--这也是互联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