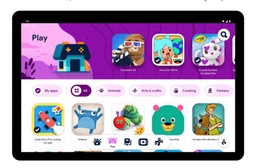医生为什么讨厌他们的电脑(2018年)
2015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其他十几名外科医生一起,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座办公楼里开始了16个小时的强制性计算机培训。我们坐在三排,每个人都停在一台台式电脑后面。再过一个月,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依赖于对EPIC的掌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医疗软件系统。从我们的自制软件升级将花费我们工作的医院系统Partners Healthcare,令人震惊的16亿美元,但它的目的是让我们在技术上保持最新。
在过去的十年里,超过90%的美国医院已经实现了计算机化,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将他们的健康信息存储在EPIC系统中。分布在新英格兰12家医院和数百家诊所的Partner Healthcare的7万名员工将不得不采用新软件。我和其他18000名医生、护士、药剂师、实验室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一起参与了实施的第一波浪潮。
我估计,参加培训课程的外科医生年龄从30岁到70岁不等-大约60%是男性,100%的人对不得不去那里而不是去看病人感到恼火。我们的教练看起来比我们任何人都年轻,可能刚从大学毕业几年,留着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早期的波浪式发型,蓝色纽扣衬衫,斜纹棉布裤子。凝视着外面闷闷不乐的观众,他似乎并不慌张。在接下来的几个课程中,我了解到每个教练都有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敌对的乌合之众。一个是鼓励的、父母的,另一个是沉默寡言的、效率很高的。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采取了驾驶教育的方式:你不想在这里;我也不想在这里;让我们尽力而为吧。
我在最初的练习中做得很好,比如查找病人的名字和紧急联系人。然而,当涉及到查看测试结果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我的屏幕左侧有一个由13个选项卡组成的列,上面挤满了几乎相同的术语:“图表审查”、“结果审查”、“审查流程图”。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学习如何输入信息,每个选项卡显示的字段都有自己的工具和细微差别。
但我并不担心。我一生都在吸收计算机技术的变化,我知道如果我推动学习曲线,我最终会做一些相当酷的事情。1978年,当我还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八年级学生时,我用邮购套件建造了自己的4KB计算机,学会了编程,很快就在我们的黑白电视机上玩起了街机游戏Pong。第二年,我买了一台Apple II电脑,最终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交电脑打印作文的孩子(此后不久,我也是第一个要求延期的孩子,“因为电脑吃掉了我的作业”)。当我的史诗训练开始时,我希望我的耐心也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多年来,我的医院已经将许多记录和流程计算机化,但新系统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平台,几乎可以做卫生专业人员需要的一切-记录和交流我们的医疗观察,向患者的药房发送处方,订购测试和扫描,查看结果,安排手术,发送保险账单。有了史诗,纸质的化验单、生命体征图表和医院病房记录就会消失。我们会更环保、更快、更好。
但三年后,我开始感觉到,一个承诺增加我对工作的掌握的系统,反而增加了我对工作的掌握。我不是唯一一个。201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医疗软件的品牌是什么,医生与患者面对面的每一个小时都要花大约两个小时做计算机工作。在检查室里,医生们花了患者一半的时间面对屏幕做电子任务。而这些任务在几个小时后就开始溢出。威斯康星大学发现,其家庭医生的平均工作日增长到了11个半小时。其结果是临床医生中职业倦怠的流行水平。40%的人抑郁症筛查呈阳性,7%的人报告有自杀想法-几乎是普通工作人口的两倍。
有些事出了很大的问题。医生是社会上最热衷于技术的人之一;计算机化简化了许多行业的任务。然而,不知何故,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点,医疗界的人积极地、发自内心地、滔滔不绝地憎恨他们的计算机。
2015年5月30日,第一阶段Go-Live开始。我的医院和诊所在两周内减少了入院和预约时间,而工作人员则在使用新系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的部门将分配给预约和程序的时间增加了一倍,以适应我们的学习曲线。我发现,这才是升级花费16亿美元的真正原因。软件成本不到一亿美元。大部分费用来自患者收入的损失,以及实施阶段所需的所有技术支持人员和其他人员。
在最初的五周里,IT人员记录了2.7万张服务台罚单-每两个用户就有三张。大多数是基本的如何操作问题;少数涉及重大技术故障。印刷问题比比皆是。许多患者的药物和说明没有准确地从我们的旧系统转移过来。我的医院不得不雇佣数百名兼职住院医生和药剂师,在技术人员努力解决数据传输问题的同时,对每位患者的药单进行复核。
然而,许多最愤怒的抱怨都源于Epic高级副总裁苏米特·拉纳(Sumit Rana)所说的“附属机构的复仇”。在构建一个给定的功能时-比如,脑部MRI的订单-设计选择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技术上的:行政人员和医生对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有不同的看法。医生们习惯了拥有所有的投票权。但埃皮克已经安排了会议,试图裁决这些分歧。现在工作人员有了发言权(有时医生甚至没有出现),他们添加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让他们的工作更容易,但其他工作更耗时。医生们经常跳过的问题现在让他们停了下来,并发出了“需要现场”的警报。现在,一个简单的请求可能包括填写一张详细的表格,占用了与患者相处的宝贵时间。
拉娜说,这些成长的烦恼是可以预见的。Epic族总是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优化”--根据用户的反馈重新配置各种功能。“第一周,”他告诉我,“人们会说,‘我怎么才能挺过去呢?’一年后,他们会说,‘我希望你能做这做那。’“。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六个月后,我对新软件已经相当熟练了。每次预约,我都会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虽然是敞开的,但在我身边。“我能帮上什么忙吗?”我会问一个病人。我的笔记本电脑可以用来查看信息和偶尔点击笔记;咨询完后,我完成了我的办公室报告。有些东西比我们的旧系统慢,有些东西改善了。从我的电脑上,我现在可以远程检查我的病人从医院手术中恢复的生命体征。只需点击两下,我就可以像许多人现在所做的那样,从使用Etic的外部机构查找患者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我的临床常规没有太大变化。
然而,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大部分的临床时间都是在手术室里度过的。我想知道我那些更忙碌于办公室的同事们过得怎么样。我找到了苏珊·萨杜吉(Susan Sadoughi),一位内科医生朋友对我说,她是他的团队中最忙、最有效率的医生之一。萨多吉是一名50岁的初级保健医生,来自伊朗,已经在我们医院工作了24年。她嫁给了一位退休的波士顿警长,育有三个孩子。在她的工作和家庭日程表中抽出时间与我交谈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找到的唯一窗口是在清晨,当时我们在她通勤的路上通了电话。
萨多吉告诉我,她每小时有四个病人时段。如果她去看新病人,或者每年做一次体检,她会用两个老虎机。早些时候,她就认识到技术可以为简化医疗做出贡献。她加入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我们过去依赖的家庭构建的电子医疗记录系统的更新,帮助根据她的初级保健同行的需求进行定制。当她听到新制度的消息时,她很乐观。再也不会了。她觉得这让她和她的病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以前,萨杜吉几乎从不需要把任务带回家完成。现在,她经常在孩子们上床后花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在电脑上。
她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每个患者都有一份关于他或她的积极医疗问题的“问题清单”,例如难以控制的糖尿病、痴呆症的早期迹象、慢性心脏瓣膜问题。这份清单旨在让临床医生一目了然地告诉他们在看病人时必须考虑什么。萨多吉过去经常仔细更新名单-删除不再相关的问题,添加有关那些相关问题的细节。但现在,整个组织的每个人都可以修改这份名单,她说,“它已经变得完全没有用了。”三个人会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列出相同的诊断。否则骨科医生会列出相同的基因
“他们很长,他们有缺陷,他们是多余的,”她说。“现在我来看一位病人,调出问题清单,没有任何意义。我必须通读他们过去的笔记,特别是当我在做紧急护理时,“她通常是第一次和别人见面。而且,有时拼凑病人病史的重要信息实际上比她翻阅一叠纸质病历要难得多。医生的手写笔记简明扼要。然而,对于计算机,快捷方式是粘贴整个信息块-比方说整个两页的成像报告-而不是选择相关的细节。下一位医生必须翻几页才能找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将这个数字乘以每天约20名患者,你就会看到萨多吉的问题。
这款软件“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难以理解的怪物,”她提高了声音说。甚至在她看到病人之前,她的时间就已经很紧了。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步,复杂性都在增加。
“订购乳房X光检查过去只需点击一下,”她说。“现在我要额外点击三次才能输入诊断结果。当我做巴氏涂片时,我有11次点击。是“哦,是谁干的?”为什么不默认地认为是我干的呢?“。她现在几乎要喊了。“我是下订单的人。如果病人今天在办公室,为什么要问我几号?你觉得这真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太不可思议了!“。“附属品的复仇”,我想。
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出这样的例子。她说:“大多数时候,到一天结束时,我只做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的笔记。”其余的是几个小时后送来的。花额外的时间并没有激怒她。这件事毫无意义,这就是原因所在。
在工作场所使用电脑的困难并不是医学界独有的。马特·斯宾塞(Matt Spencer)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他研究的是科学家,而不是文明。在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群研究流体力学的研究人员共处18个月后,他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脆性和官僚主义”的论文,对人类与软件关系的痛苦演变进行了一系列观察。
几年前,一名研究生编写了一个名为“流动性”的程序,该程序允许研究小组运行小规模流体动力学的计算机模拟-特别是与为核反应堆安全运输放射性材料的挑战有关的模拟。这个程序优雅而强大,其他研究人员很快就把它应用到了广泛的其他问题上。他们定期为其添加新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程序以多种计算机语言扩展到100多万行代码。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会产生无法预见的缺陷。随着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代码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出现故障或崩溃。
IBM软件工程师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Frederick Brooks)在1975年的经典著作“神话中的人月”(The Mythical Man-Month)中称这种最终状态为焦油坑。他说,从一个很酷的程序(比如说,由几个书呆子为他们的几个书呆子朋友开发的)到一个更大的、不那么酷的程序产品(向更多的人提供相同的功能,使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和不同的能力水平),到一个更大的、非常不酷的程序系统(针对更多的人,在许多种类的工作中有许多不同的需求),这是可以预见的。
斯宾塞描绘了伴随这一进程的人类反应。人们最初欣喜若狂地接受新程序和新功能,然后开始依赖它们,然后发现自己受制于一个控制自己生活的系统。在这一点上,他们要么投降,要么反叛。伦敦的科学家们造反了。斯宾塞写道:“一周后,他们得到的结果不再是可重现的,他们对此感到厌倦。”他们坚持要求该小组花一年时间从头开始重写代码。然而,在重写之后,官僚主义的枷锁依然存在。
随着一个节目适应和服务更多的人和更多的功能,自然需要更严格的监管。软件系统控制着我们作为群体进行交互的方式,这使得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总会有一些人想要维护这个系统,有些人想要挑战这个系统的边界。保守派和自由主义者应运而生。
科学家们现在谈论的是“旧流动性”,即合作者较少的较小程序,让科学家可以自由开发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以及“新流动性”,它拥有更多的用户,因此更受规则的约束。变革需要委员会、谈判、不令人满意的分歧解决方案。许多科学家以医生的方式向斯宾塞抱怨--他们在软件的要求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浪费了实际研究的时间。“我只想做科学!”一位科学家哀叹道。
然而,没有人能指出更好的方法。斯宾塞写道:“虽然受访者会让我知道他们的抵触情绪,但他们中没有人甚至声称流动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运行得更好。”新的流动性具有任何小型个性化系统都无法提供的功能,也是科学家无法替代的。
柏油坑困住了我们中的许多人:临床医生、科学家、警察、销售人员-我们所有人都弓着腰盯着屏幕,花更多的时间处理我们工作方式上的限制,而不是简单地做这些事情。我们唯一的选择似乎是要么适应这个现实,要么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来。
许多人已经被压垮了。伯克利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职业倦怠现象。她很早就被与病人一起工作的苛刻性质所吸引,专注于医疗保健。她将倦怠定义为三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的组合:情绪疲惫、去人格化(对他人持愤世嫉俗的、工具性的态度)和个人无效感。相反,一种深深投入到工作中的感觉,来自一种精力、个人参与感和效能感。她和她的同事们开发了一项名为马斯拉赫工作倦怠清单(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的22个问题的调查,近40年来,该调查一直被用来跟踪从监狱看守到教师的各种职业的工人的幸福感。
近年来,很明显,医生的倦怠率非常高。2014年,54%的医生报告至少有三种倦怠症状中的一种,而2011年这一比例为46%。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意他们的工作安排“为我的个人/家庭生活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而在其他员工中,这一比例几乎为三分之二。女医生的职业倦怠程度更高(同时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也较低)。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一项分析发现,倦怠增加了医生转而从事兼职工作的可能性。它把医生逼出了行医的境地。
职业倦怠似乎因专业而异。神经外科等外科专业在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评分特别差,但仍低于平均职业倦怠水平。另一方面,急诊医生的工作-生活平衡好于平均水平,但职业倦怠得分最高。当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一个团队发现,职业倦怠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是一个人花在处理计算机文档上的时间有多长时,这种不一致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外科医生一天中花在电脑前的时间相对较少。急诊医生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花掉的。随着数字化的普及,护士和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也感受到了被屏幕束缚的类似影响。
萨多吉告诉了我她自己的挣扎--包括每天与她的史诗“篮子”战斗,她说,篮子已经堵塞到了功能障碍的地步。有来自患者的消息、包含实验室和放射学结果的消息、来自同事的消息、来自管理员的消息、关于未回复先前消息的自动消息。“所有来自专家小组的信件,我都看不懂百分之九十。所以我看了一眼病人的名字,如果是我担心的人,我会读到的。“她说。其余的她删除了,未读。“如果这只是一次例行的内分泌科医生随访,我希望上帝,如果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注意,他们会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简而言之,她希望他们能尝试通过另一个收件箱联系到她。
随着我观察到更多的同事,我开始看到软件改变了人们合作方式的阴险方式。他们变得更加脱节;不太可能看到和帮助对方,而且通常也不能这样做。杰西卡·雅各布斯(Jessica Jacobs)是我执业期间的一名长期办公室助理--45岁左右,敬业,有着吸烟者沙哑的嗓音-她说,每一个新的软件系统都减少了她的角色,把更多的责任转移到了医生身上。在此之前,她在门诊前整理患者记录,起草给患者的信,准备常规处方-所有这些任务都减轻了医生的负担。这一切再也不可能了。医生们不得不自己做这一切。她称这是“一种‘待在你的车道上’的事情。”她甚至不能帮助医生导航和简化他们的计算机系统:办公室助理有不同的屏幕,没有经过培训或授权使用医生拥有的屏幕。
“你不能从这个系统学到更多,”她说。“你不能再做更多了。你不能承担额外的责任。“。即使是小事也常常不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例如,她最近注意到,系统中有一个错误的推荐医生的邮寄地址。但是,她告诉我,“我所能做的就是去服务台找13次。”
雅各布斯对这种变化模式感到悲哀,有时甚至感到痛苦:“这让人丧失了权力。这是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