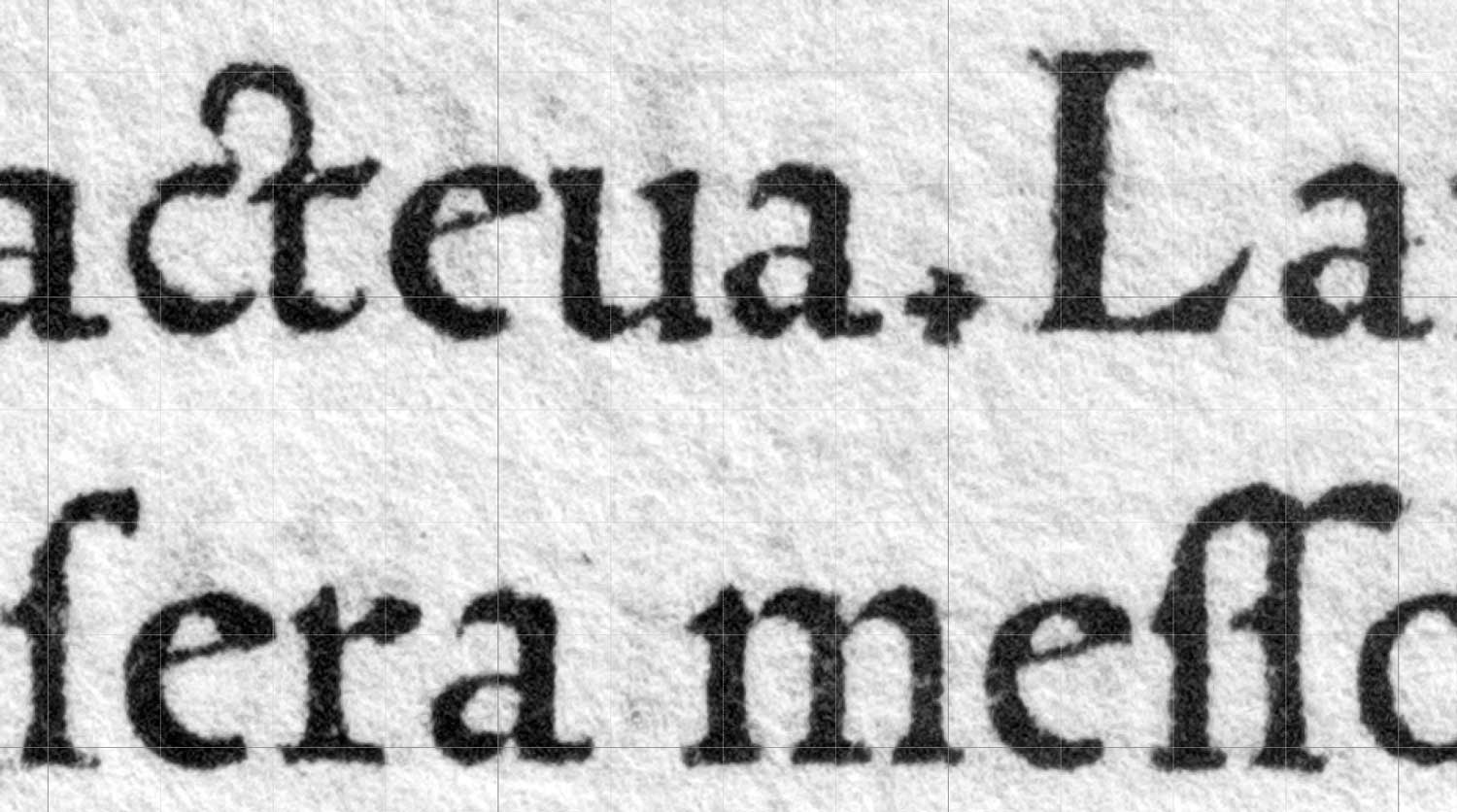第一批罗马字体(2016)
文艺复兴影响了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变化,但也许它最持久的遗产之一是它留给我们的字母。但他们的遗产远远超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古代。在古罗马,共和国首都和帝国首都之间有乡村首都、方形首都(罗马帝国首都用毛笔书写)、单行字和半单行字,此外还有日常使用的更快书写的草书。从这些非社会性和半社会性的形式演变出一种在法国实践的新的正式书法,这种书法在中世纪和欧洲迅速传播开来。
这种加洛林文字在8世纪和9世纪蓬勃发展。然而,从11世纪初到大约1225年,卡罗琳小字(伴随着一种单字大字)演变成了一种更加棱角分明、横向压缩的文字。不仅字体受到这种压缩的影响,字母间距也受到影响,以至于字母开始接吻、咬合和融合。到了12世纪,这种哥特式文字,有许多国家和地方的变体,在整个欧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采用。然而,到了14世纪,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像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和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等人文主义者,倡导一种新的半哥特式文字,此后演变为人文主义书本。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哥特式字体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是卓越的正规书法。然而,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北部纹理(或纹理)的极端角度和压缩受到了抵制。南欧变体,或Southern Textualis,以圆形蝴蝶结和更宽的字体为特征。
人文主义,一种诞生于佛罗伦萨的文化和智力运动,在古代看到了一种远远优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伯克哈特将早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描述为“他们自己的时代和受人尊敬的古代之间的调解人”。(Burckhardt,第135页)。他们的极大热情是为了恢复古典文明,这体现在它的文学上。因此,他们在地球上搜寻手稿,认真地抄写、翻译和抄写。看到他们的许多受人尊敬的古典作家都是用与哥特式截然不同的文字书写的,他们错误地将中世纪的卡罗琳小号作品归因于古代,因此有了“Littera Antica”一词,即古董字母。当两名尘土飞扬、疲惫不堪的德国神职人员抵达罗马东部萨宾山安静隐居的苏比亚科修道院时,人文主义剧本已经完全演变,已经成为古典文学手稿书籍的自然选择。
Sweynheym&Amp;Pannartz Proto Romans印刷在14世纪50年代中期从美因茨传播到斯特拉斯堡、班伯格、埃尔特维尔和科隆。但是,尽管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印刷术要突破阿尔卑斯山还需要十年的时间。不是在欧洲最国际化的城市威尼斯,甚至也不是在罗马,而是在苏比亚科的本笃会修道院Sancta Scholastica修道院的安静避难所,那里位于罗马喧嚣以东约70公里处。一个世纪前的1364年,教皇乌尔班五世对其“不可救药的僧侣”感到失望,命令巴塞洛缪院长解雇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德国,这随后吸引了更多的德国移民,包括两名级别较低的神职人员康拉德·斯威恩海姆(Konrad Sweynheym)和阿诺德·潘纳茨(Arnold Pannartz)。事实上,这两位牧师印刷工很可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他们被这么多的同胞包围着。在苏比亚科修道院,在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僧侣的数量超过了外国人。在1360年至1515年间被点名记录的大约280名僧侣中,不到三分之一(83名)来自意大利;110名来自德国,19名来自法国;其他僧侣来自遥远的波希米亚、波兰、普鲁士、匈牙利、西班牙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其他地方。斯威海姆可能和彼得·舍弗尔一起受雇于美因茨,而帕纳茨来自科隆(不是布拉格1号)。
到1464年,或最晚1465年,斯威海姆和帕纳茨已经抵达苏比亚科。也许他们是由胡安·托奎马达2(1388-1468年)邀请的,他是自1455年以来苏比亚科修道院、圣朔拉斯蒂卡和萨克罗·斯佩科修道院的住持。他们可能只带了最少的随身物品,包括他们的类型,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排字材料。他们就不必拖着媒体翻越阿尔卑斯山,因为这是一座在他们到达后很容易就能在苏比亚科僧侣和其他陪同他们从德国出发的人的帮助下建造起来的东西。他们首先印刷了300册罗马语法学家杰罗姆(Jerome)的四世纪导师埃利乌斯·多纳特斯(Aelius Donatus)的拉丁文语法,不幸的是,没有一本幸存下来。他们的下一版,不迟于9月14日发行
此外,在第一次尝试中,大小写字母之间缺乏统一,这是意料之中的。例如,大写字母中的应力或轴有时几乎是垂直的,而在小写字母中则是倾斜的。衬线治疗相当随意。正如莫里森指出的那样,[莫里森,图书馆,第21页]这种类型包括几种d,l和m-对书法变体的让步。
总体而言,字体的对比度很小。苏比亚科罗马文字的小写和当代人文主义文字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许多小写字母被切割的范围有多窄。这一特点,加上紧凑的间距,形成了一种相对较暗的颜色。
由Sweynheym和Pannartz印刷的大量书籍前往罗马,有60册,几乎是他们最后的Subiaco印记de Civitate dei印刷量的四分之一,运往罗马(Füssel,第60页),尽管正如埃德温·霍尔所说,这些书籍可能是分配给僧侣作为他们帮助运行印刷机的报酬。他们的书没有当地市场,这可能促使他们在1467年搬到罗马。
有些奇怪的是,本笃会的僧侣们没有继续他们自己的新闻出版。在Sweynheym和Pannartz离开去罗马四年后,圣斯科拉斯蒂卡上方的修道院Sacra Speco的僧侣本尼迪克图斯·德·巴伐利亚(Benedikt Zwink)写信给奥地利哥特威格本笃会修道院住持劳伦蒂乌斯,提出印刷一本摘要,但没有证据表明苏比亚科在原型打印者离开后产生了一个标题。
他说:“我们有所有的印刷设备,也有懂得使用的人。如果我们能成为这个宗教联盟(扩大的会众)的一部分,所有的书籍,无论需要多少,都可以印刷并分发给所有的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反过来也会加入会众,使用现场可用的设备,并在可以指导这种技术的五个弟兄的帮助下进行…“。
这封信还建议他们可以印刷200份。甚至连斯威海姆和帕纳尔茨版的“de Civitate dei”中的一页也附在信中,作为他们将使用的字体的例子。Subiaco Roman字体再也没有被Sweynheym和Pannartz使用,这表明Subiaco僧侣是他们的字体和排字设备的继承人。
Lotte Hellinga挖苦地总结说,“其他的工作,比如给花园除草,肯定占用了太多的时间。”然而,很明显,僧侣们密切参与了苏比亚科出版社,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空谷仓和一个葡萄酒压榨机”。
罗马人当教皇和反教皇在跨越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分裂期间在阿维尼翁和罗马之间进行神权拔河时,罗马被忽视,年久失修,公民四散。当分裂最终在康斯坦斯委员会解决时,新当选的教皇马丁五世开始恢复罗马。他鼓励移民,作为回应,有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在这座城市定居。在德国社区的中心矗立着他们的教堂,圣玛丽亚·戴尔·阿尼玛(St.Maria Dell‘Anima)。斯威海姆和帕纳茨无疑会感到宾至如归,因为他们的印刷厂靠近坎波德·菲奥里(Campo de‘Fiori),距离Anima只有几分钟的步行路程。他们用新成立的罗马印刷厂制作了一种新的罗马字体。
这第二个罗马人在许多方面不同。使用衬线的方法要一致得多。一些大写字母更宽:最明显的是E、F和K。在小写字母中,大多数字母都更宽,包括e,它采用笔尖或延伸的横杠。此外,碗是圆的-这些成分使Sweynheym和Pannartz的第二个罗马颜色更浅。
尽管斯威海姆和潘纳茨因将排版书籍和罗马字体引入意大利而闻名,但他们似乎并不是最有商业头脑的人。到1472年,他们濒临破产,他们的编辑乔瓦尼·安德里亚·布西(Giovanni Andrea Bussi)向教皇请愿,要求救济。请愿书按时间顺序列出了它们的版本和各自的印数(总计令人印象深刻的12,475卷),包括它们的Subiaco印记。
斯威海姆和帕纳茨的请愿书印在尼古拉斯·德·莱拉(Nicolaus De Lyra)的“Postilla Super totam Bibliam”第五卷的序言中,这是一个听起来相当绝望的恳求:
“我们是德国人中第一个把印刷艺术带到罗马的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费用。我们与别人拒绝面对的困难作斗争,结果我们的钱花光了,我们的房子里满是卖不出去的东西,却没有生活资料。我们力不从心地恳求您的帮助,作为回报,我们很乐意给您尽可能多的我们的手工艺品。“。
“您忠实的请愿人,美因茨和科隆教区的神职人员,马西莫家族的图书印刷工康拉德·斯威海姆和阿诺德·潘纳茨,恳请教皇陛下允许他们在两座大教堂…中拥有两座圣殿。”
人们一度认为他们的请愿书被置若罔闻,但Schlecht在一卷1471年8月至1472年8月提交给教皇十六世的杂项请愿书中发现的一份文件显示,他们的请愿书确实得到了积极响应,这无疑是由于他们的编辑乔瓦尼·安德里亚·布西(Giovanni Andrea Bussi)的影响,后者最近被任命为最近重新建立的梵蒂冈图书馆的首席图书馆员。如果说有哪本书是斯威海姆和帕纳尔茨陷入绝境的罪魁祸首,那么它就是尼古拉斯·德·莱拉(Nicolaus De Lyra)的“波斯蒂利亚”(Postilla),这是一本5卷本的对开本作品,共1832页,是15世纪最大的作品之一(霍尔,埃德温出版社,第7页和第15页)。
相反,被托克马达邀请到罗马的乌尔里希·韩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但是,为什么乌尔里希·韩在斯威海姆和帕纳茨失败的地方能够蓬勃发展呢?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的答案在于他们的书,在于他们选择印刷的内容。斯威海姆和帕纳茨几乎只生产古典作家的作品;他们从来没有用哥特式字体印刷过;事实上,他们似乎没有一种哥特式字体。尽管有富有而有影响力的马西莫家族的好感,也有教皇的恩惠,但他们的印刷量和图书销量都比乌尔里希·韩少得多。即使在他们1472年的请愿书之后,当Sweynheym和Pannartz可能会想到,也许他们选择印刷的书目是他们财务困境的来源;而且被堆积如山的未售出库存所包围,他们也没有考虑印刷不同的体裁和作家。
新任命的红衣主教Torquemada,谁可能已经邀请Sweynheym和Pannartz到Subiaco,没有为印刷他的冥想寻求他们的服务,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1467年12月31日)。托克马达的书中有33幅木刻插图,斯威海姆和帕纳茨除了1470年用木刻首字母做了一个简短的实验外,从来没有用过这些版画;显然,这些木刻都是印刷的,没有正文,而是单独的手工盖章。T.F.Dibdin挖苦地暗示,Sweynheym和Pannartz已经“发誓不再装饰”。(“书目十日谈”,1817年)也许这并不是一个牵强的概念。因为事实上,他们的出版计划-几乎完全是以罗马为背景的经典作品-即使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也可能表明了他们的原则性审美或顽固性。他们的编辑布西的另一句话也许说明了他们排版能力的局限性,当时他在奥卢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夜曲(Noctes Atticae)(1469年)第一版的序言中说,印刷商无法印刷边缘评论。(埃德温·霍尔,第62页)
为什么乌尔里希·韩能够在斯威海姆和帕纳茨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虽然斯威海姆和帕纳茨享受着马西莫兄弟的富丽堂皇的住所,并与布西有重要的联系,但他们继续出版难以售出的版本,乌尔里希·韩不仅得到了托克马达红衣主教的好感,而且还与查德拉合作。查德拉自己虽然不是印刷商,但显然了解图书市场。在1471年之前,韩主要印刷古典文本(西塞罗、利维、朱维纳尔、普鲁塔克等),但他的合作伙伴查德拉建议他出版的不是经典,而是关于教会法的书籍(毕竟那是罗马!)。除了教会法方面的书籍,这种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还出版了13世纪主教和教会主义者纪尧姆·杜兰(他的叔叔,而不是那个不太出名的侄子的同名侄子)撰写的礼仪论文《宗教仪式的原理》(Rationalale Divinorum Offerorum)等书籍。在1470年之前,我们只看到两个宗教标题,而经典中只有八个;到1473年,只有一个经典,维吉尔的歌剧,和七个宗教标题(包括教会法)。同年,斯威海姆和帕纳茨出版社出版了四版经典著作,没有一本宗教著作发行。然而,尽管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他似乎和许多15世纪的印刷商一样,从未远离破产的境地。1476年,韩无力支付40金币的欠租,他提供了一本书代替付款,但他的房东阿尼玛兄弟会(Brotherhood Of The Anima)只以3金币的价格出售了这本书。(马斯,第125页)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支付差额的,但他确实一直印刷到大约1480年,总共出版了大约100个版本。由于印刷数百本书所需的巨额资本投资,一个失误就可能导致灾难。最成功的印刷商是最灵活的,也是那些最善于解读市场的人。我们不应该把私人出版社运动中的浪漫主义与那些离破产只有一本书的印刷公司混为一谈。乔治·劳尔在罗马,在他的编辑庞波尼乌斯·莱图斯的坚持下,成功地将他的注意力从古典版本转移到教皇法庭的法律文本和小册子上。顺便说一句,1479年,劳尔正在与斯威海姆和帕纳茨的第二个罗马类型合作。亚当·罗特(Adam Rot)从1471年开始在罗马印刷,他能够垄断罗马导游的市场,包括他的米拉比利亚·罗梅(Mirabilia Romae)版本,这是一本迎合这座城市数十万游客和朝圣者的“美妙罗马”(Mirabilia Romae)。
在他们请愿后的短短14个月内,斯威海姆和帕纳茨的合作关系就结束了。另一部经典著作“他们的自然历史”出版于1473年5月,是他们合作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帕纳尔茨继续独自在马西莫兄弟皮埃特罗和弗朗西斯科的宫殿里的同一个车间里印刷,直到1476年。他死于1478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斯威海姆致力于制作铜版地图,包括托勒密的宇宙地图,但在完成它们之前就去世了(约1477年)。这本书是由另一位德国印刷商Arnoldus Buckinck于1478年10月10日完成的(ISTC:ip01083000),一对开本充满了木刻和27幅华丽的铜刻地图。序言是写给第六章四世的,就是五年多前向斯威海姆和潘纳茨授予福利的教皇。
许多新兴印刷品的历史表明,罗马字体一经引入,很快就变得无处不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罗马是意大利的发展,但它在意大利的使用,至少在15世纪,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广泛。一百三十八种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印刷机似乎没有使用任何罗马字体。(赫希,第115页)9%的欧洲印章是古典文本;意大利这一数字上升到略高于30%,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都是用罗马字体设定的,那么近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印章是用罗马字体设定的-仍然远远超过用哥特式字体印刷的书籍。在德语国家,各种形式的黑信或哥特式字体在文艺复兴之后继续占据主导地位。
罗马字体的早期历史被类似半哥特式和半罗马式的术语搞混了。丹尼尔·厄普代克(Daniel Updike)使用“纯罗马人”或“过渡罗马人”来区分罗马人,例如,达斯皮拉兄弟和苏比亚科式的斯威海姆(Sweynheym)和帕纳茨(Pannartz)。乔治·艾布拉姆斯(George Abrams)将苏比亚科风格描述为“从哥特式到罗马式的过渡”。然而,斯坦利·莫里森(Stanley Morison)认为这样的术语是错误的。Sweynheym和Pannartz没有试图创造一种混合了哥特式和人文主义风格的字体。他们的类型是以人文手稿为基础的,这些手稿确实显示了一些哥特式的元素-不是因为这样的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半人文主义的,而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哥特式手稿演变而来的。但是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