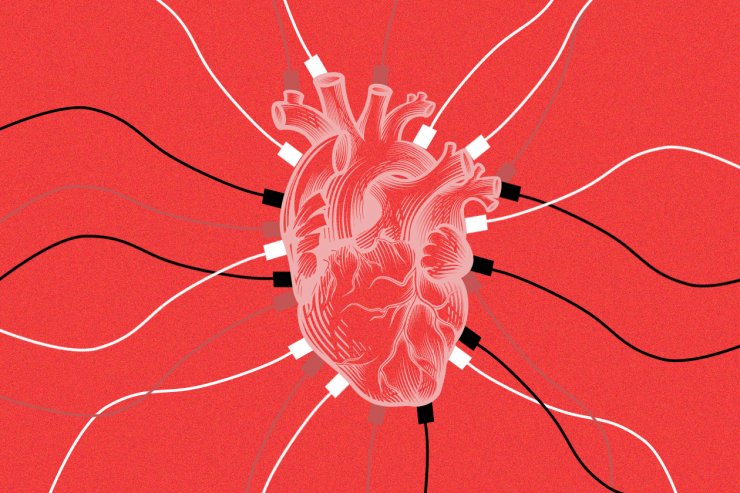什么时候死了?(2019年)
在我的一生中,我认为生与死之间的界限是无可辩驳的。在我在多伦多地区担任护理人员的十年里,我认为身体很简单:氧气流入肺部,被吸收到血液中,被泵到打破它的细胞周围,以及从肠道吸收的葡萄糖,向下产生为生命提供动力所需的微小能量。我想,死亡也很简单:没有产生新能量的那一刻,电池耗尽的那一刻,以及灯熄灭的那一刻。我已经宣布了数十人死亡。例如,在特别可怕的情况下,当某人是房屋火灾或钝器头部创伤的受害者时,我甚至不需要检查脉搏。苍白的皮肤,空洞的眼睛,以及身体对重力的默许都说明了一切。
但当我在2012年开始读医学院时,我的思维受到了挑战。在医院里,人们似乎死亡,嗯,比他们在战场上的死亡要慢。通常没有车祸、子弹或大动脉撕裂可以作为他们死亡的原因。死亡不再是突如其来的。取而代之的是,我照顾濒临死亡的人-这一过程可能需要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当我作为一名医科大四学生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时,这条线变得更加难以聚焦。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小男孩,他在紧急手术后住进了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他病得很厉害,靠生命维持系统维持生命。一天晚上,他的瞳孔停止了对光线的反应。我记得主治医生--我的老板--透露说那个男孩可能脑死亡了。“我们早上会做正式测试,”他告诉我。“可能”和“死亡”通常不会并驾齐驱;作为医生,我们想要确定-如果可以,我们希望有时间做出反应。但是,一旦大脑这个词在可能和死亡之间被粉碎,确定死亡时间只会变得更加复杂。
有时,宣布某人脑死亡需要几天时间,而器官捐赠过程则需要几天时间。如果有人在接受生命支持,在这段时间里,血液将继续在体内循环,能量将继续产生。那么,那个男孩是什么时候死的呢?当我们细细观察他那两个睁得大大的、黑得像黑夜的瞳孔时,他当场就死了吗?是不是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我们正式宣布死亡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之后的两天,一名外科医生挖出他的心脏,并迅速将它送给了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后来成为了移植幸存者?
那个男孩的案子让我震惊。看着这么年轻的人死去是一回事,但让他们的死亡问题挥之不去又是另一回事。这是第一次,我的病人是活着还是死了,这个清晰的黑白问题变成了一个灰色的模糊大问题,似乎由哲学家而不是医生更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突然间,我觉得死亡很复杂。直到今天,谁来决定生命何时结束的问题仍然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一种药物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一些人来说,活着和死亡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难以确定。机械呼吸机可以让空气无限期地进出肺部,透析机可以代替肾脏过滤血液中的废物,药物可以模仿大脑产生的荷尔蒙和化学物质,心脏的巡航控制功能-称为自动性-意味着只要获得适当的氧气供应,心脏就可以在体外跳动几个小时。
不过,医生并不是在黑暗中飞行。由于之前缺乏书面文件,专家们在严谨的科学指导下,在加拿大制定了确定死亡人数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南写于2006年,概述了如何宣布神经性死亡。他们是严格的,在器官捐赠的情况下,要求两名医生核实大脑不可逆转的死亡。任何可能影响评估的药物都必须从患者体内清除,如果有任何疑问,就会进行神经成像研究,通常是用对比染料或放射性颗粒进行研究,以证明血液没有流向大脑。
人们倾向于认为死亡分为两类:肉体死亡发生在心脏已经停止并且不能重新启动的时候,神经死亡发生在大脑已经不可逆转地停止功能的时候。也被称为脑死亡,神经性死亡代表着意识和脑干功能(包括呼吸能力)的不可逆转的丧失。后者的挑战是,有时一个人在神经性死亡后仍然可以看起来活着。偶尔,当家属不同意脑死亡的诊断时,他们可以在法庭上反驳这一声明。
最近,加拿大法院审理了两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接近2017年底,多伦多地区有两个家庭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提交申请,分别挑战宣布脑死亡的布兰普顿市(Brampton Civic)和亨伯河(Humber River)医院医生。两个家庭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获得了法院禁令,迫使医院维持他们所爱的人的生命维持。当时,塔基沙·麦基蒂(Taquisha McKitty)是一名27岁的基督教女性,在服药过量后被宣布脑死亡,然后一直接受生命维持,直到2018年12月,也就是医生最初宣布她死亡整整15个月后,她的心脏衰竭。沙洛姆·瓦努努乌(Shalom Ouanounou)是一名东正教犹太男子,25岁时患有严重哮喘,他一直在接受生命维持,直到2018年3月,也就是医生宣布他死亡六个月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在这两起案件中,这些家庭都辩称,根据他们对宗教的解释来定义死亡是他们的权利。在每种宗教的情况下,根据各自的家庭,最后一条线只以心跳停止为标志。
几个世纪以来,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不和谐一直困扰着许多医学院的讲座,在我看来,它似乎永远都会如此。有时,这种不和谐会把我们带到更富有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地方;有时,并非如此。对我来说,许多反对医学上对死亡的定义的人--即脑死亡--相信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某个地方,他们所爱的人的人格还在那里。
为了试图理解他们对生死的看法,我联系了惠利房地产诉讼公司(Whaley Estate Litigation)的律师马克·汉德尔曼(Mark Handelman),他代表瓦努努乌的家人。汉德尔曼拥有生物伦理学的健康科学硕士学位,他并没有试图改变我对死亡的看法。取而代之的是,他把我带入了信奉东正教的瓦努诺家族的头脑中。他告诉我,一种方法要求,要宣布死亡,心脏功能必须停止,包括心脏。汉德尔曼说:“一些正统的犹太人认为,因为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有无限的价值,心脏功能肯定会不可逆转地停止。”另一种方法似乎只与呼吸有关,将死亡定义为呼吸停止。这可能会令人困惑:一种解释认为脑死亡是最终死亡,另一种解释则不是。汉德尔曼强调,他的工作不是决定哪个定义(如果有的话)是正确的,而是捍卫个人的宗教自由权利。“我不想靠自己维持生命,”他说。“但我仍然捍卫(瓦努努乌)自己对此进行解释的权利,他的解释不是基于医疗利益,而是基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
如果宗教定义获得支持,或者成为法律,家庭可能会要求对身体进行通风、喂养和无限期维护-顺便说一句,这种做法可能会花费省级政府数百万美元,并进一步挤压人满为患的人群。
安大略省的准司法同意和能力委员会()已经听取了几个家庭希望脑死亡的亲人继续接受生命维持的案例。许多医生认为,使用科技让某人无限期地在场是跨越了道德界限-亵渎了人体-同时也有可能让那些依赖它们的人无法获得珍贵而昂贵的床位。很难不把这看作是一场战斗。而且,作为一个发誓要为我的病人而战的人,要弄清楚我站在哪一边就更难了。我是否准备好说,没有任何犯错的余地,被宣布脑死亡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是否存在灰色地带,或者神经性死亡真的是非黑即白?
我,当麦基蒂和瓦努诺都还戴着呼吸机的时候,我给安德鲁·贝克打了电话。贝克是一名医生,是加拿大脑死亡指南的作者之一。他简直就是重症监护领域的传奇人物,当他在电话的另一端讲话时,我就知道,如果可怕的消息正向你袭来,你会想听到他的声音。贝克以温和而自信的方式承认了死亡困境的复杂性,但对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值得辩论的,他坚定不移。“只有一人死亡,”他说。“脑干死亡和意识(能力)不可逆转的丧失。”
心脏与死亡的关系很复杂。正如贝克所说:“如果你的心脏停止跳动,你可能不会死。它可以自动复苏。“。换句话说,停止跳动的心脏可以自行重新开始跳动--尽管这并不是很常见,而且必须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几分钟内发生。更有可能的是,有人会介入,重新启动你的心脏,恢复你大脑的血液流动。
我们现在有了可以帮助重新启动静止心脏的药物,在商场、机场、曲棍球场,甚至是人们的家中都可以找到启动心脏的除颤器。生存
但是,当缺乏流向大脑的血液时,最常见的原因是脑部肿胀或出血,这会使颅骨的压力高于心脏产生的血压。所以心脏可能是健康的和跳动的,但是病人可能还在断头台下面。
现代医学现在几乎可以暂时有效地替代人体的每一个器官。甚至心脏也可以由心肺搭桥机和机械心脏泵来支撑。那么,鉴于这些进步,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必须划清界限,”贝克说。“白血球可以在体外存活数百年。我们可以把你的细胞植入细胞,它会制造蛋白质。我可以把你的肾移植到别人身上,你的肾就活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还活着?“。
他认为,这条线在于意识--这条线与整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一致。他补充说,科技意味着我们必须坚定地定义死亡。他说,这意味着,当神经性死亡被证明发生时,人格就结束了。
A自1976年以来一直住在渥太华。她是两位医学家的女儿,是一名社会研究人员。我想和她谈谈,因为她的父亲,当时是拉瓦尔大学(Laval University)的退休医学教授,在2016年摔倒,后来在渥太华的一所大学陷入昏迷。她告诉我,医生建议停止生命支持。她的父亲没有被宣布脑死亡,但伊斯特布尔说,渥太华的医生告诉她的家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她补充说,他们要求她指定她的父亲为“不要复苏”的患者,并且不要升级治疗。但是与一个妹妹和一个兄弟分享委托书的伊斯特布尔拒绝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官僚拉锯战,导致她的家人和医疗队分道扬镳。
埃斯特布尔很快澄清说,随后的争议与她父亲的死亡无关。“他的死没有争议,”她尖锐地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他的一生饱受争议。”埃斯特布尔告诉我,她的父亲清楚地表示,即使他的生活质量很差,他也想活下去。然而,医院对这一决定提出了质疑,并将这家人带到了法庭。当安大略省的家庭和医生意见不一时,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动议,有时会调解患者、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之间的分歧。委员会可以任命一名代表代表患者做出决定,裁决赞成或反对手术、治疗或撤销维持生命的治疗。
伊斯特布尔说,这段经历让她和她的七个兄弟姐妹感到受到欺凌。他说:“我们不断被鼓励改变主意。这一过程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接近持续骚扰的过程,“伊斯特布尔说。她说,她和家人承受的压力仍然让她“目瞪口呆”。“这是卡夫卡式的。太离奇了。每个凡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愚蠢,我们的父亲也在这条路上。但让他自己走吧,“她说。
作为医学研究人员的孩子,伊斯特布尔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立即浏览了文献,以了解她父亲的病情。他们利用医院的资源来确保他的意愿得到尊重;咨询了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伦理学家和医院牧师,希望找到解决方案。但医院还是求助于。埃斯特布尔的家人聘请了一名律师,并最终在法庭上赢得了这场官司。她说,她的父亲在那年晚些时候去世之前恢复了意识,并与家人进行了交谈。当联系到渥太华医院时,渥太华医院告诉海象,它支持委员会的工作,“虽然我们无法对委员会的决定发表评论,但他们的工作允许通过一个明确、开放、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来分析病例。”
虽然埃斯特布尔的父亲从未被宣布脑死亡,但这起案件鲜明地说明了医生在试图为病人辩护时可能给一个家庭带来的痛苦。它还表明,在生命末期的讨论-通常是很糟糕的-可以瓦解医生被教导要培养的治疗关系。
埃斯特布尔对她的家庭经历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思考。“国家什么时候可以夺走一条生命?”她问道,并不完全是修辞。听了这番话,我不禁怀疑,是不是家人就是这样看待我的医生角色的--我是一个国家演员,幻想着在这里还是那里夺走一条生命?
过去与病人家属的谈话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感到内疚,想知道我是否也让家人感到受到了欺凌。我问伊斯特布尔,她认为在法庭就脑死亡进行辩论时,大脑死亡的身体由机器通风的情况下应该做些什么。“为什么不让他们自生自灭呢?这些家庭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痛苦。“。我是不是因为好奇而变得冷漠--这不就是问题的关键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痛苦和悲痛地继续前进吗?在接受死亡的过程中,家庭可以通过失去和痛苦来工作,并过渡到新的常态。作为医生,我的角色不是如此清晰地传达死亡的悲痛,然后才能在适当的时候接受吗?
从来没有,我既完全相信医学对脑死亡的定义的准确性,又对如果一个家庭对这个定义提出质疑时我应该怎么做的可怕冲突。
我回想起两年前的12月,当时我坐在布兰普顿的一个法庭上,对Taqisha McKitty一案的结案陈词做笔记。医生们坐在房间的左边,麦基蒂的家人坐在右边。一台投影仪在法庭墙上播放了麦基蒂的视频。我记得她的手指抽搐,每个人都点头:医生很可能看到了与大脑无关的脊髓反射的证据;这家人很可能将这种运动视为生命的迹象,希望的迹象。在那一刻,我很清楚,法庭不是进行这场辩论的地方。
尽管如此,法庭似乎是唯一可以澄清的地方。尽管麦基蒂最终被安葬,但她的案件仍在安大略省上诉法院继续审理。无论结果如何,败诉的一方都有可能申请许可,前往最高法院进行最终裁决。
需要明确的是,这场关于生死界限的辩论必须尽快解决。除了医生、护士和家庭感受到的痛苦之外,还有真正的资源问题。布兰普顿市政医院拒绝评论麦基蒂在纽约16个月的影响,所以我提出了信息自由的请求。结果发现,在她宣布死亡后的11个月里,24张床位有23天是满的,177天是“接近满的”。患者通常在急诊室等待超过6个小时,有时是几天,才有床位可供他们使用。救护车不得不将43名需要床位的患者转移到其他医院,还有4次手术因为没有床位而被取消。
我成为一名医生是因为我珍视生命。但我选择了在死亡不可避免的领域工作。医学界最尊崇的一句话是“第一,无伤大雅”。在下一次我与家人谈论他们即将死去的亲人之前,我会重复这句咒语,希望我对生活的热情能激发我对死亡终极的解释。
我们以加拿大的声音和专业知识为特色,报道具有全球影响的故事和事件,从大麻的主流到加拿大对新冠肺炎的回应,从大麻的主流到加拿大拉瓦林事件的余波,我们坚信这一报道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我们请求像您这样的读者支持“海象”,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引领加拿大的对话。捐款20美元或以上将获得慈善税收收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