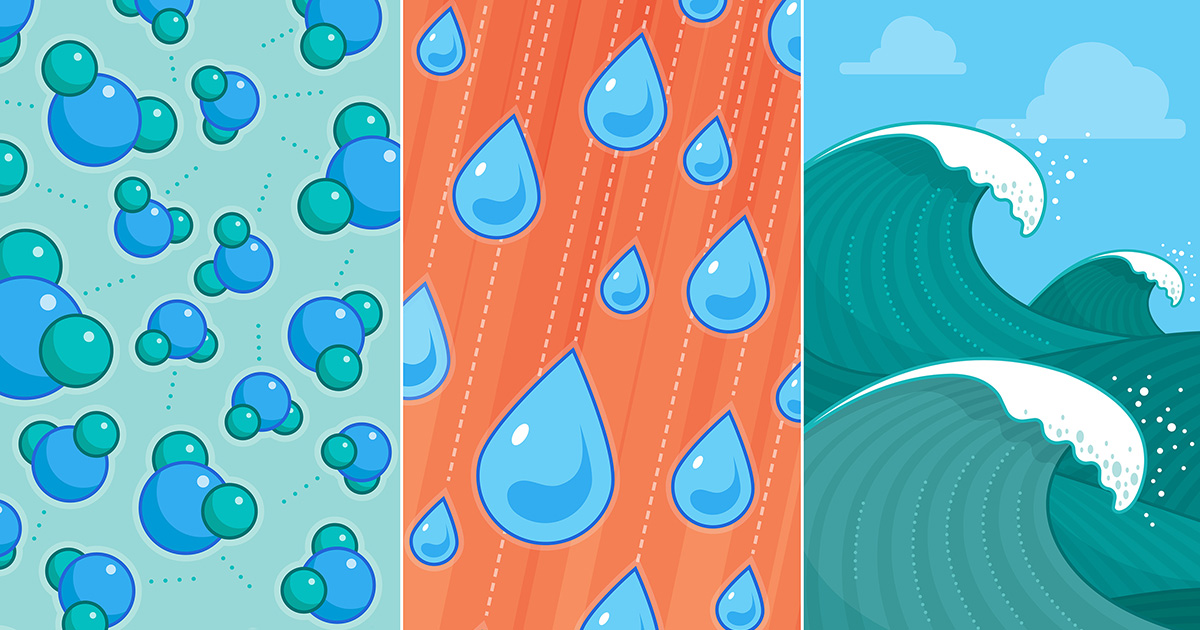数学上的“Hocus-Pocus”拯救了粒子物理
在20世纪40年代,开拓性的物理学家偶然发现了下一层现实。粒子出来了,田野进来了--广阔的、起伏的实体,像海洋一样填满了空间。一个场中的一个波纹是电子,另一个波纹是光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可以解释所有的电磁事件。
只有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用希望和祈祷粘在一起的。只有使用一种被称为“重整化”的技术,包括小心地隐藏无限数量,研究人员才能避开虚假的预测。这一过程奏效了,但即使是那些开发这一理论的人也怀疑,这可能是建立在一个痛苦的数学技巧之上的纸牌屋。
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后来写道:“这就是我所说的愚蠢的过程。”“不得不诉诸这样的骗局,使我们无法证明量子电动力学理论在数学上是自洽的。”
几十年后,一个看似互不相关的物理学分支证明了这一点。研究磁化的研究人员发现,重整化根本不是关于无穷大的。取而代之的是,它讲述了宇宙分裂成独立大小的王国,这一观点指导着当今物理学的许多角落。
剑桥大学的理论家大卫·唐写道,重整化“可以说是过去50年来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一项进步。”
从某些方面来看,场论是所有科学中最成功的理论。量子电动力学(QED)理论构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它做出了与实验结果相匹配的理论预测,精确度为十亿分之一。
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一理论的未来远非板上钉钉。近似场的复杂行为往往会给出无意义的、无限的答案,这让一些理论家认为场论可能是死胡同。
费曼和其他人寻求了全新的视角-甚至可能是将粒子带回中心舞台的视角-但却带着一种破解回来了。他们发现,如果用令人费解的重整化过程修补,QED的方程可以做出可观的预测。
这个练习大概是这样进行的。当QED计算得出一个无穷大的和时,缩短它。将想变成无穷大的部分填入一个系数--一个固定的数字--放在和的前面。用实验室的有限测量值代替这个系数。最后,让新驯服的金额回到无穷大。
对一些人来说,这份处方感觉就像是一场骗局。“这是不明智的数学,”开创性的量子理论家保罗·狄拉克写道。
问题的核心-以及最终解决问题的种子-可以从物理学家如何处理电子电荷中看出。
在上面的方案中,电荷来自系数-在数学洗牌过程中吞噬无穷大的值。对于对重整化的物理意义感到困惑的理论家来说,QED暗示电子有两种电荷:一种是理论电荷,它是无限的;另一种是测量的电荷,它不是。也许电子的核心带着无限的电荷。但在实践中,量子场效应(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虚拟的正粒子云)掩盖了电子,所以实验者只测量了适度的净电荷。
1954年,两位物理学家Murray Gell-Mann和Francis Low充实了这一观点。他们用一个随距离变化的“有效”电荷将两个电子电荷连接起来。你离得越近(你越是穿透电子的正极斗篷),你看到的电荷就越多。
他们的工作首次将重整化与尺度概念联系起来。它暗示量子物理学家对错误的问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连接微小和巨大上,而不是担心无限。
南丹麦大学的物理学家阿斯特丽德·艾希霍恩(Astrid Eichhorn)说,重整化是“数学版的显微镜”,他利用重整化寻找量子引力理论。“相反,你可以从微观系统开始,然后缩小。它是显微镜和望远镜的结合体。“。
第二条线索出现在凝聚态物质的世界里,物理学家们对粗略的磁铁模型是如何设法确定某些转变的精细细节感到困惑。伊辛模型只由一个原子箭头网格组成,每个箭头只能向上或向下移动,但它却以难以置信的完美预测了现实生活中磁铁的行为。
在低温下,大多数原子排列,使材料磁化。在高温下,它们无序生长,晶格退磁。但在一个关键的过渡点,各种大小排列的原子岛共存。至关重要的是,在伊辛模型中,在不同材料的真实磁铁中,甚至在一些不相关的系统中,比如水和水蒸气变得难以区分的高压转变中,某些量围绕这个“临界点”变化的方式似乎是相同的。这种被理论家称为普遍性的现象的发现,就像发现大象和白鹭以完全相同的最快速度移动一样离奇。
物理学家通常不会同时处理不同大小的物体。但临界点周围的普遍行为迫使他们一次计算所有的长度尺度。
1966年,凝聚态研究人员利奥·卡达诺夫(Leo Kadanoff)想出了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开发了一种“积木旋转”技术,打破了伊辛网格过于复杂而无法迎头对付的局面,分成每边只有几个箭头的适度积木。他计算了一组箭头的平均方向,并用该值替换了整个块。重复这一过程,他平滑了晶格的精细细节,缩小以摸索系统的整体行为。
最后,曾是盖尔曼大学研究生的肯·威尔逊(Ken Wilson)将盖尔曼和洛的观点与卡达诺夫的观点统一起来。威尔逊在粒子物理和凝聚态两个领域都有研究。他在1971年首次描述了他的“重整化小组”,证明QED痛苦的计算是合理的,并为攀登宇宙系统的规模提供了一个阶梯。这项工作为威尔逊赢得了诺贝尔奖,并永远改变了物理学。
牛津大学的凝聚态理论家保罗·芬德利(Paul Fendley)说,将威尔逊的重整化群概念化的最好方法是将微观与宏观联系起来的“理论理论”。
考虑一下磁栅格。在微观层面上,很容易写出连接两个相邻箭头的方程式。但是把这个简单的公式外推到数万亿个粒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你想的尺度不对。
Wilson的重整化群描述了从积木理论到结构理论的转变。你可以从小棋子理论开始,比如说台球中的原子。转动威尔逊的数学曲柄,你会得到一个描述这些棋子群的相关理论-也许是台球分子。当您不断转动时,您会缩小到越来越大的分组-台球分子簇、台球扇区,等等。最终,您将能够计算出一些有趣的东西,例如整个台球的路径。
这就是重整化群的魔力所在:它有助于识别哪些大图像量是有用的,哪些错综复杂的微观细节可以忽略。冲浪者关心的是浪高,而不是水分子的碰撞。类似地,在亚原子物理学中,重整化告诉物理学家,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处理相对简单的质子,而不是它内部的夸克纠缠。
威尔逊的重整化组还提出,费曼和他的同代人的困境来自于试图从无限近距离理解电子。英国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物理哲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说,“我们不认为(理论)会在任意小的(距离)尺度上都有效。”物理学家现在明白,当你的理论有一个内置的最小网格大小时,数学上缩短总和并将无穷大打乱,是进行计算的正确方式。“我们不指望(理论)在任意小的(距离)尺度上都是有效的,”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是英国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物理哲学家。弗雷泽说,“截止日期正在吸收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无知”,“在较低的水平上”。
换句话说,QED和标准模型根本不能说出零纳米外电子的裸电荷是多少。它们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有效”理论。它们在定义明确的距离范围内工作得最好。找出粒子变得更舒适时到底会发生什么是高能物理的一个主要目标。
今天,费曼的“愚蠢的过程”在物理学中已经变得和微积分一样无处不在,它的机制揭示了该学科一些最伟大的成功和当前挑战的原因。在重整化过程中,复杂的亚微米马鹿往往会消失。它们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不会影响大局。“简单是一种美德,”芬德利说。“这里面有一个神。”
这一数学事实捕捉到了自然界将自己归类为本质上独立的世界的倾向。当工程师设计摩天大楼时,他们忽略了钢铁中的单个分子。化学家分析分子键,但幸好对夸克和胶子一无所知。通过重整化小组量化的按长度分离现象,使得科学家们可以在几个世纪内从大到小逐渐移动,而不是一次破解所有的尺度。
然而,与此同时,重整化对微观细节的敌意与现代物理学家的努力背道而驰,他们渴望看到下一个领域的迹象。鳞片的分离表明,它们需要深入挖掘,以克服大自然对我们这样好奇的巨人隐瞒其细微之处的喜好。
“重整化有助于我们简化问题,”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理论物理学家内森·塞伯格(Nathan Seiberg)说。但是“它也隐藏了近距离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两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