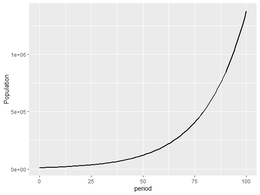经济学人世界中的人类学家
在本期ASOMC中,我想向最近不幸去世的人类学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胎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美丽而勇敢的嗓音致敬。大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激励着我,并在去年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们共有的一件事是,在一个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世界里,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难度很大,所以这是我想简单谈一谈的一个话题。
大卫是一位撰写关于经济的人类学家,这是我对他的研究产生共鸣的第一个原因。人们有时认为我出身于经济学背景--因为我写的是金融和金钱--但实际上我拥有人类学学位,而人类学是一门经常与经济学产生对立关系的学科。
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存在这种对立,但这是我对它的描述。
人类学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一个人--至少在第一种情况下--不能离开一个群体而存在。换言之,人类学假设人类网络总是先于其个体成员,而关怀和繁衍先于任何形式的个人英雄行为。如果让人类婴儿自己照顾自己,他们活不了多久,即使他们奇迹般地在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他们也不会说语言,这将使未来所有的社交、关系和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参见野性儿童)。
当孩子们长大成人并获得自信时,他们确实会意识到自己的边际差异,并可能会接受成为独立的“个体”的想法,但在人类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永远不会是一个主要的取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可以自己走到地平线上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没有与乐队、氏族或部落的密切联系,就没有独立的“自我”存在于荒野中。
因此,人类学家最先意识到,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广泛使用的“个人”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不如说是在特定群体内部、特定条件下、特定时间和地点出现的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更具体地说,这是一个在庞大的民族国家体系中蓬勃发展的概念,这些体系消除了亲密亲属的需要。
在大型民族国家里,你确实可以离开原籍地,在其他陌生人中作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走来走去,同时所有人都在一个共同的元规则体系下被团结在一起(法律体系、货币体系以及抽象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旗帜,给这些陌生人带来一些松散的连接感)。在许多人类学家中出现的异端思想是,也许现代个体是国家的产物。这也是现代人类学与左倾无政府主义有联系的原因:人类学家是最先意识到资本主义是由国家催化的,而不是存在于与国家对立中的人之一。
这种取向使许多人类学家与许多标准经济学家对立(我之所以说“标准”,是因为来自不同分支的不同经济学家之间显然存在多样性和细微差别)。标准经济学是在现代国家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国家的人口上。因此,当人类学家沉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氏族社会时,他们震惊地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而经济学家们则如此沉浸在现代国家中,以至于这些国家融入了背景之中,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几乎看不见。
而且,一旦你忘记了国家,你就会简单地看到它存在的社会后果。你会看到陌生人,彼此分离,四处漂浮,交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开始想象世界是一个自治的、自由流动的个体。你甚至可能开始松散地认为,个人优先于人的网络。这是因为-在一个州的背景下-他们有时会这样做:来自全国各地的不稳定的工人与一群从分散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的经理们建立了联系,这些经理都在共同的国家基础设施下运营,瞧,一家公司就存在了。
经济学教科书通常从供给和需求曲线开始,代表成年成年人进入市场相互签约所依据的条件。这个模型背后的这种心态经常被隐含地扩展,并被用来描述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源于个人的理性效用计算,这就是它变得循环的地方。
忽视国家对市场的支撑的倾向意味着,经济学学科长期以来一直隐含着一种信念,即群体只是“个人的集合”,似乎在经济学的集体思维背后,有一种愿景,即如果社会不再适合他们,人们可以选择离开并离开社会。
在许多人类学家和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缺陷,有点像你的学科基础代码的最深层有一个虫子。这种对“自我”独自漂浮在市场中的想象,使这门学科能够创造出“自我利益”(自我关注自己)和“利他主义”(自我关注他人)等人类行为的漫画,而对于许多早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自我利益和群体利益是彼此的一部分,就像鸡和鸡蛋一样。现代资本主义仪式,比如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举行的小组讨论,对冲基金经理们在会上讨论追求自身利益是否会通过慈善实现利他主义,对于任何基本理解生存不是个人吞噬的人来说,这都是荒谬的。
那么,在最糟糕的时候,主流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那就是把一个特定于历史的经济体系--以资本主义货币兑换为基础,由大规模国家释放--笼统地贴上“经济学”的标签,然后将其普及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其投射到根本不存在的情况。(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一位音乐教授声称古典音乐是唯一的音乐形式,然后继续使用西方古典音乐符号和音阶来转录印度拉格音乐)。
这种殖民倾向产生了诸如货币起源易货贸易理论等极具吸引力的理论,在易货贸易理论中,后货币时代的心态被投射到前货币世界,然后被用来争论为什么货币必须起源。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可以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但大卫在他的书“债务:最初的5000年”(Debt:The First 5000年)中拆解了这种知识上的可憎之处。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易货贸易理论到现在已经受到了100多年的攻击-但他的书要比这广泛得多。它是人类学冲向经济学的大门,揭示了隐藏在所谓的科学原则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判断(如“债务必须偿还”)背后的政治动态。
大卫是一位人类学风格的大师,这种风格让你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选择的范围比你想象的要广泛得多。虽然保守的经济部门试图将伴随资本主义货币兑换的心态自然化,但经济人类学充其量就像是我们集体潜意识中的叛逆者,保持着对其他存在方式的了解(其中许多方式仍然存在于我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的阴影下,并寄生在我们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的阴影下)。
我们发现自己被困在这些系统中,它们构成了不断的矛盾。例如,我与…的想法有着长期而艰难的关系。Well…。将我在另类货币方面的工作货币化,要求人们将数字银行存款转移到我身上,以换取我对另类经济系统的想法。在我与大卫的第一次相遇中,我感觉到了同样的挣扎。他和我一样,相信团结网络,而不是在那里测量他的时间,并给它一个货币价格。一些知名作家拒绝出现在活动中,除非他们得到五位数的报酬,而大卫会出现在由热情的活动家举办的最卑微的活动中,根本没有钱。
他经常性格内向,但致力于帮助他人,这意味着他经常面临被热心的信徒耗尽精力的风险。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2年伦敦的无政府主义书展上,他就是在那里演讲的。他之后在走廊休息时,我试图走近他--我想试着用他讲话的一些要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疲惫地看着我,我都退后了。
我第一次真正与他交谈是在几年后的一次晚宴上,当时他与债务活动家共进晚餐。他告诉我,试图帮助所有需要支持的团体是多么困难,但他仍然坚持下去。这就是大卫对我来说是人类学英雄的原因,因为他明确地政治化了,并实践了他的人类学知识。他敏锐地意识到,被殖民主义推倒的社会在分配劳动力和能源方面往往有着完全不同的习俗,并精通这些习俗的模棱两可(比如我将在下一个DFMM视频中讨论的“空壳钱”-见下文)。尽管如此,他相信我们有能力重塑这些知识,以挑战我们周围令人压抑的金融结构。
最重要的是,我记得他对被视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感到非常不舒服。去年,我和他的学生、朋友胡里奥·利纳雷斯(Julio Linares)一起排队等候。我们试图进入一个人满为患的活动,在那里每个人都认识他的脸,在那里他会被当作贵宾对待。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走进去,但拒绝插队。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们一直没进去。我们坐在会场外,开始讨论建立一个名为“幽灵”的集体--秘密政治经济联盟(Secret Political Economy Consortium)。
在封锁期间,我们试播了幽灵电视台的第一集试播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编辑视频。那是关于基本收入的,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大卫说话。
大卫就像一副古怪的扑克牌。他的政治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就像德克萨斯Hold-em游戏中翻出来的牌一样-但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幸运,因为我有几次机会看到他向我展示了一两张个人卡片,古怪、滑稽和温暖。我和其他许多人都会深深地怀念这一点。
不过,我希望我与大卫的对话能够打个比方地继续下去,继续将货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政治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即将出版的“现代货币前沿快讯”中,我将以新冠肺炎为背景,探讨“空壳货币”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长期以来是人类学家最喜欢的地方)复兴的话题。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故事是在8月21日,当时“卫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空壳资金的回归:巴新在Covid';经济遭受打击后复兴旧方式”的报道。要了解我对这个故事的深入了解,以及我对它的典型表现方式的解构,请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