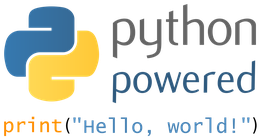约翰·克里斯谈创意、巨蟒和洋蓟
我和约翰·克里斯一起急速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时他威胁要过来打我的耳朵。两年前,我曾问过他的声明,即他对英格兰不再抱有幻想,将至少暂时搬到加勒比海的尼维斯岛。与他成长的“更平静、更有礼貌”的国家相比,当代英国有很多令人讨厌的地方。但他当时说,他“特别不满”的是英国媒体的状况,以及Leveson 2的沉没。Leveson 2是政府调查的一部分,这项调查源于2011年的“世界新闻报”电话窃听丑闻,可能会导致英格兰咄咄逼人的小报文化进行改革,而这种文化一直是许多名人和皇室成员的祸根。
在我们采访几个小时后,克里斯在推特上抱怨说,“一些美国记者一直在向我施压,要求我发表我没有发表的声明。”他特别提到了我的假设,即他自我流放的原因之一是对英国退欧的愚蠢言论。他再次将我的错误信息归咎于下流的英国小报。(事实上,我从他接受BBC采访时得到了英国退欧的印象,他在采访中说,“这个国家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英国退欧的辩论标准。”)。他的570万追随者不会对他的愤怒感到惊讶;去年秋天年满80岁的克里斯在Twitter上抨击政治正确性、“沃克斯人”(Wokes)、否认气候变化的人、特朗普政府、BBC的“小官僚”,以及他认为的各种愚蠢和无稽之谈。
当然,愚蠢和胡言乱语是Monty Python的主要目标,Monty Python是Cleese在1969年与Eric Idle、Terry Gilliam、Terry Jones、Michael Palin和Graham Chapman共同组建的无政府主义喜剧团体。“Monty Python的目标,”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2004年在“纽约客”(The New York Ker)上写道,“不仅是为了让观众发笑,同样重要的是,用极端的偏见撕裂了电视这一媒介。”它的处女作系列“巨蟒的飞行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 Circus)就像一只巨人赤脚踏上了克利斯现在推崇的有礼貌的英国文化。但Cleese的职业生涯远远超出了Monty Python,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滑稽情景喜剧“Fawlty Towers”和他因“一条叫旺达的鱼”而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剧本。他还写了几本书,包括他早年的一本畅销回忆录《所以,无论如何…》,还有一本名为《创意》的新手册,号称是《短小而开朗的指南》。
当Cleese出现在我们的Zoom房间时,他告诉我:“我希望13岁的孩子能在一小时内读完它。”他是在伦敦说这番话的,当时他在约克拍完一部电影,路过伦敦。(“我们处于泡沫之中,或者他们怎么称呼它。”)。大流行期间,他在贝莱尔的一家酒店里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制作音乐剧“旺达”和改编自舞台剧“巨蟒的布赖恩的一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接下来,他和妻子去了马斯蒂克,之后--谁知道呢?“我们真的很幸运还活着,真的,”他坐在一张喷鼻斑马的照片前说。在我们谈到他最近接二连三的政治冲突之前,我们的谈话(经过编辑和浓缩)就开始了,主题是他的新书。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创造力指南是一种矛盾修饰法。你相信它是可以学习的吗?
你可以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你可能会变得更有创造力。一位心理学教授曾对我说:“如果你悲伤,你就会有悲伤的想法。如果你生气了,你就会有愤怒的想法。“。所以,要想有创造力,你必须有创造性的想法。你需要有创造性的心情。你是如何产生创造性情绪的?嗯,根据定义,创造性的情绪是一种嬉戏的情绪。为什么孩子们可以玩得这么自然呢?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照看商店。孩子们不用担心谁在做饭。因此,如果你想像成年人一样玩耍,你必须创造一个空间,在那里你可以摆脱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责任。
你写了很多关于盖伊·克莱斯顿的书,“兔子的大脑,乌龟的头脑”。你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这是我拼图的一大部分,因为他指出了这两种思维方式。有一种快速、默认的方式,还有一种速度较慢、深思熟虑的方式。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认为智力总是与敏捷有关,这是错误的。大错特错了。问题越像数学问题,你知道所有的因素,你得到测量值,这对兔子的大脑来说就是理想的东西。它变得越不确定,越与感觉和人有关,你就越需要缓慢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观点,即潜意识非常强大,但是很难控制。有点像女人。你不能对它指手画脚。你必须哄骗它,对它友好些。如果你追求它,它似乎会变得更远。
你写道,“我们‘乌龟头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一种不确定和温和的困惑中进行的。”你是怎么进入这种心态的?
你不能用棍子打它。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想出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似乎确实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平均水平。查普曼和我每周可以做15到20分钟的好材料,这比“巨蟒”一集所需的时间稍多一点,其他人都在贡献。如果有一天它没有到来,你只要坚持下去就行了。当你在吃饭的时候,食物正从叉子上朝你端来,你不能说,“嗯,这是好事,而从嘴里空着走到盘子里就是坏事了。”这都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如果你开始自责,那也没用。
看起来你从你钦佩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创造力的东西,比如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
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每个人都认为是天才的人是彼得·库克。他是一位出色的小品作家和表演者,也是一位门徒--你怎么称呼一个独白的人?一夫一妻制!我过去常常拿到我亲爱的旧黑胶唱片,放他的一张小品--就像那个试图教乌鸦在水下飞行的人--我会试着凭记忆把它写出来。然后我会再听一遍这张唱片,直到最后,大约在第六稿的时候,几乎就是我一直在听的剧本。我学的是技术,而不是创造力。在过去,他们常常让艺术家们临摹大师的作品。
正确的。你给出的建议之一就是向你钦佩的人“借用”。
是!。不过,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会说你是“受影响的”。你知道,“我深受迈克尔·舒尔曼作品的影响。”当然,如果你只是以现在的形式偷东西,而你没有对它做任何事情,那么这就是偷窃。你什么都学不到。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从别人那里借用一种风格并使用它,那么它就会成为你的风格,因为你正在这样做。我认为莎士比亚一生中从未想过一个情节。他只是抄袭了别人的故事。他似乎从未因此失去过任何分数。
在“所以,不管怎样…”中,你谈到了那些让你倾向于创造的东西。你写道,“所以,创造性地,我得到了双重的祝福:不断的搬迁和父母的不和谐。”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成长的地方只有一种版本的真理,只有一种做事的方式,那么你可能会认为那是唯一的版本。如果你从小就经常旅行或听到父母之间的争吵,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你可以把这两种方式进行比较,然后说,“我更喜欢上一个城镇。”比较经验,即使是和你的父母,也会让你考虑其他的可能性。然而,对于在爱荷华州长大的人来说,没有太多其他的展示,所以他们不太擅长想象其他场景。
是的,有可能。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他们没有地图。反正他们也看不懂。
没关系。我有一个去柬埔寨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我只是在检查板球。抱歉的。我们要和澳大利亚队打一场大赛。
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你在孤独中所做的创造力,但你最出名的事情是合作完成的。你如何比较这两种类型的创造力?
你说得很对。团队合作的整个过程很吸引人,当然这也是你想要多样化的地方,因为观点越不同,团队就越有创造力。如果你把许多中年白人男性放在一起,他们最后会说这是一次多么令人满意的经历,他们真的很想再来一次。当然,他们已经想出了他妈的所有东西。但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那么危险的是你会得到与创意无关的争论。因此,你希望有一个人负责,他会封闭那些试图主宰的人,并鼓励那些不能那么容易推动自己前进的害羞的人。
我们很早就发现,如果有四个人在那里,你不可能真正写出任何东西,因为四个人中的一个不会喜欢刚刚提出的建议。我和格雷厄姆共事过。迈克和特里有时一起写作。埃里克总是独自工作。特里·乔里安也不是真的写信。我们告诉他我们想让他怎么做才能从现在的情况发展到现在的情况,然后他就会消失,我们会看到他在节目当天下午制作的精彩的动画片。
几年前,我采访了埃里克·伊德尔(Eric Idle),他告诉我,当他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成为朋友时,他认为他们在各自的群体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被称为“自由漂浮的激进分子”。这让我想问你是哪个披头士。
我相当同情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因为我认为约翰·列侬(John Lennon)有点过分崇拜,有些人更愿意拿麦卡特尼出气,他似乎是这个团体中非常好的一员。在委员会审议阶段,我发现埃里克是最容易共事的。他可以放手。而我发现琼斯很难做到,因为他对每件事都坚信不移,而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让他改弦易辙。查普曼反正也没在听。乔里安不在那里。迈克尔只是简单地同意每个人的观点,因为他讨厌冲突。
你写过你是如何与一月份去世的特里·琼斯正面交锋的。这是更有成效,还是对创作过程不利?
它的危害更大。特里更有可能想出奇怪的、更大的想法,比如士兵们跑向德国人,大声喊出这个致命的笑话。你还记得吗?或者是愚蠢的步行部,或者是餐厅里的超大胖子克洛索特先生。但他对一切都很关心,而且他总是确信自己是对的。即使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他辩论,总体感觉是我的想法更好,第二天他会说,“昨晚我在思考,我真的感觉到了-”然后我们又会回到同样的辩论中。他真正出色的地方是导演。他在“布赖恩的一生”中做得非常出色,他在“圣杯”中执导的东西是最好的。乔里安很擅长拍照,但琼斯更擅长拍摄喜剧。
你最重要的合作关系可能是与格雷厄姆·查普曼(Graham Chapman)的合作关系,这始于剑桥大学。你写道,“格雷厄姆和我一样,对我们在学校以宗教的名义被灌输的废话怀恨在心。”
我们过去常常写很多有圣经背景的小品。人们进来看到圣经就会说,“哦,你一直在写小品!”
人们说我们是反专制的。我想事实是我们是反坏当局的。我是说,你必须要有权威。你不能就这样放弃红绿灯。
你还说过你更有逻辑性,格雷厄姆会加上精神错乱。你如何平衡这两件事呢?
当我们想不出要写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拿一本同义词词典,我会把单词读出来。他会说“黄瓜”“”黄瓜?嗯。没有。“。“好吧。一落千丈。“。这真的发生了。他说:“我喜欢直落。”我说,“我也是。这是个有趣的词。”胡说八道…。砰的一声!“那么什么会暴跌呢?”他说:“如果一只羊想要飞,它就会直线下降。”然后我们有了素描。
至于你什么时候会出轨,答案是当有人说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突然你意识到有一个5秒前还没有的喜剧想法,它几乎和性高潮一样好。格雷厄姆的男朋友大卫·夏洛克(David Sherlock)会在楼下,我们会在楼上,突然他会听到巨大的噪音-尖叫和脚步声-就在那一刻,我们都看到了很大的喜剧可能性。
你和格雷厄姆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动力,但也有它的挑战,对吗?
到了第二季,他已经开始认真喝酒了。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以前我和他合住一套公寓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直到他喝醉了,然后他会变得非常咄咄逼人。他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他记不住自己说的话了。我们不得不放弃他和我写的一个小品,因为他确实不能在观众面前说出他的话。
你现在已经失去了两条蟒蛇。我能问一下成为这个现在减少了两个人的著名团体的一员是什么感觉吗?
我不认为失去朋友的现象,特别是在Python环境中,因为我一直是迈克尔·佩林的天然朋友,而且他和我无论如何都会成为朋友的。但我认为我永远不会成为琼斯或乔里安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太不同了。我发现埃里克很容易交谈,因为与大多数英国人不同的是,他接受过一些治疗。查普曼因为他是同性恋,过了一段时间离开伦敦,和一群年轻人一起住在肯特郡,而我过去一年只见到他一两次。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我记得我看了看,发现这里有一块红色的斑点。[用手势指着他的脖子。]。他解释说是他扁桃体上的辐射。我们都很惊讶,因为一旦他戒酒了,他就成了我们中最健康的人,你可以从他在“布赖恩的一生”中的裸照中看到。他看起来非常乐观,事后我无法断定他是勇敢的,还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乐观是真诚的。迈克尔和我去了他快要死的医院,彼得·库克也下来了,我们也在他去世时在场。
我读到过,所有的蟒蛇对改编的作品都有否决权,比如“Spamalot”。你正在创作的“布赖恩的一生”这部剧的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有些人曾与我们接洽,想把“布赖恩的一生”改编成舞台剧,我说,“好吧,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每个人都说,“是啊,有何不可?”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迈克尔和埃里克对此都没有丝毫兴趣。所以突然我发现自己在房间里说,“你是说我是唯一想做这件事的人吗?”他们说,“是的。”我想,那太棒了,因为我可以去做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我一直觉得(舞台改编)不应该是音乐剧。虽然“布赖恩的生活”很有趣,但它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如果我们有任何欢快的歌曲,它就会失去这个目的。我也不认为怀念的歌会奏效。
是的,你看,但每个人都在期待这一点。我是个非常反常的人,我只是想,也许不是!我在想彼拉多的妻子-不,我不能。[板球眼球得分。]。哦,操,我们丢了两个。这不是好消息。
我想问你关于今年夏天关于“Fawlty Towers”节目“德国人”的争议,其中有一幕是Gowen少校用“N”这个词来描述西印度群岛板球队。英国广播公司(BBC)旗下的英国广播公司(UKTV)最初将其停播,你称其为“懦弱和懦弱”。现在又回到了免责声明中。你对事情的结果满意吗?
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屈服。令我苦恼的是,那些应该经营电视公司的人不明白,你可以用两种方式取笑一个团体或他们的想法:一个是直接攻击这个团体,另一个是把这个团体的话塞进一个明显是白痴或离谱得可笑的人的嘴里。这就是少校的问题所在。实际上,他来自另一个世纪。所以,当他以一种非常合理和非常绅士的方式解释这些辱骂的种族诽谤词语的含义时,我们是在取笑这些词语,因为它们是从一个你不能认真对待的人的嘴里说出来的。这就像你和阿奇·邦克遇到的问题一样,当他说这些荒谬的右翼言论时,一些人坐在爱荷华州-哦,对不起!-坐在美国的某个地方,那里正在说这些事情。这是你控制不了的。
我自己的感觉是,一切与P.C.有关的事情都是对喜剧的误解。喜剧不是关于完美的人。它是关于人类的弱点和弱点。
我明白你所说的上下文。你看到一些观众不想在他们的电视上听到N字的理由了吗?
几年前,一位学者用了“niggardly”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好而且很正常的英语单词,经常使用,特别是在一百年前,人们认为它与N-单词有关。在某个时候,你会说“不”。我知道我不应该说“有色人种”,但我认为我可以说“有色人种”而不能说“有色人种”是荒谬的。我是说,为什么?嗯,因为人们会心烦意乱。好的,嗯,当有人说A字的时候,我碰巧会心烦意乱。[暂停。]。朝鲜蓟!。请不要在我面前提到这种特别的蔬菜。
但显然有某些类型的喜剧已经过时了。在“所以,无论如何…”中,你有一张你在百老汇拍摄的“剑桥马戏团”(Cambridge Circus)中的小品,名为“中国歌曲”(Chinese Song),你把它描述为“现在不可饶恕的种族主义,但在1963年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在63年,如果你说“操”就会引起骚乱。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有点武断。重要的是我们努力善待他人,这是所有宗教的基础。如果我们试着表现得友善,我们就不必担心特定的词,因为词的意义--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是从上下文中获得的。如果我叫你“笨蛋”,你就会知道那是深情的。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有些人会说,“你不能说‘混蛋’这个词。”我犯了一个错误,把某人描述成“快乐的”,结果被告知,“哦,不,那意味着胖。”没人告诉我它的意思是胖。而且,如果很多21岁的人认为“快乐”的意思是“胖”,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每个人都要说,“你说得对。”在过去的800年里,我们一直在错误地使用它。“。
这周我看了“德国人”的一集,听到N这个词如此随意地四处游荡,我感到很不舒服。它让我有五分钟没有参与这个故事。
我认为,恕我直言,这与美国的种族历史有关。我们在英国没有奴隶制,除非我们是罗马人的奴隶,然后是诺曼人的奴隶。我学法律的时候,有三个关键日子。我认为在1700年的一个法律案件中,奴隶制在英国是错误的。然后是奴隶贸易,我很自豪地说威廉·威尔伯福斯和贵格会做了很大的努力来阻止这一点。然后是关于在加勒比海地区实际使用奴隶的最后一件事,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停止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