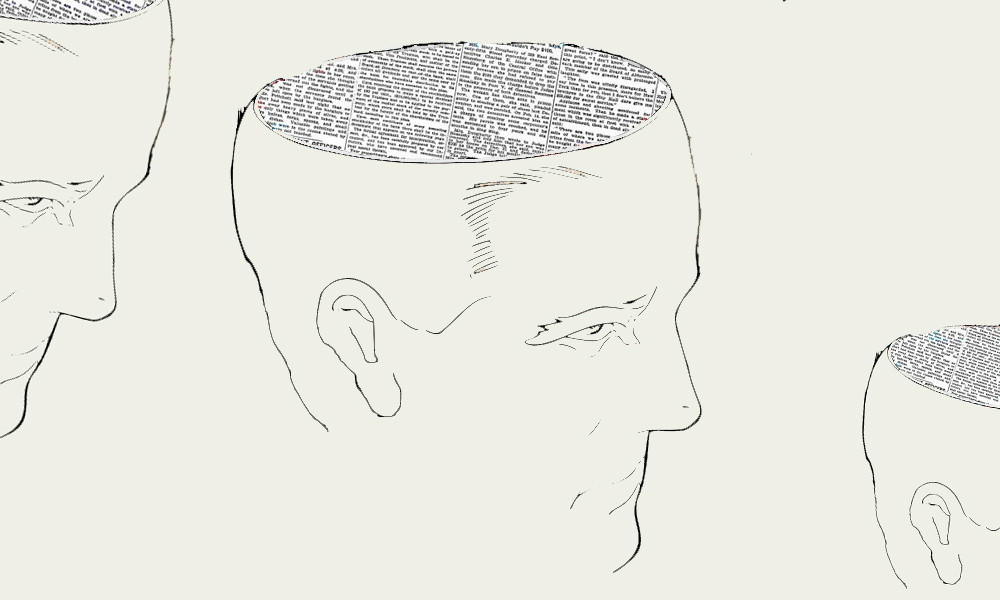什么是思想之声?
直接从大脑阅读语言思想使我们更接近于回答一个古老的问题-并为更多的问题打开了大门。
当我们不说话而思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中包含了文字的声音呢?它们仅仅是我们对公开语言的记忆所产生的错觉吗?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指向一个谜团,一个与我们努力识别不可能的语言相关的谜团-也就是无法在人脑中扎根的语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个谜团同样相关,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处理语言和大脑关系的方法。它需要从识别(通过神经成像技术)神经元在哪里放电,转变为在我们从事语言任务时识别哪些神经元在放电。
想一想这个简单的问题:语言是由什么组成的?当然,语言是由单词和组合规则组成的,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它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中:大脑外部和大脑内部。当它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外时,它由压缩和稀薄的空气分子(即声音)的机械声波组成;当它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内时,它由作为神经元通信通道的电波组成。Waves: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都是语言的物理构成的具体材料。
声波和大脑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联系。声音允许一个大脑的内容,如文字所表达的那样,进入另一个大脑。(当然,两个大脑还有其他方式来交换语言信息-例如,通过眼睛,通过手语,或者通过触觉系统,如盲文或Tadoma方法。)。声音通过我们的耳朵进入我们,穿过鼓膜和耳蜗中的科尔蒂器官,鼓膜是我们身体中最小的三块骨头,被称为听骨,耳蜗是一个蜗牛形状的器官,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复杂的系统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将声信号的机械振动转换成电脉冲,将复杂的声波分解成表征它们的基本频率。然后,不同的频率被映射到初级听觉皮层的专用槽上,在这一点上,声波被电波取代。
至少自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电生理学家埃德加·阿德里安勋爵的开创性工作以来,我们已经知道,任何物理信号在到达大脑时都不会完全丢失。我们最近的发现令人惊讶:显然,电波在大脑的非声学区域保持了相应声波的形状,比如在负责语言产生的大脑的布罗卡区(Broca‘s Area)。
这些发现对大脑中声波和电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几乎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与语言相关的神经心理过程的一个方面:即声音发射解码。然而,我们知道,语言也可以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存在,当我们阅读时(就像我们此时此刻最有可能经历的那样),或者当我们在思考时使用语言-用专业术语说,当我们从事内隐活动时。
这个简单的事实立即引发了下面的关键问题:当我们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的情况下产生语言表达时,我们大脑中的电波会发生什么?
2014年,我和同事们出发寻找答案。我们将表征布罗卡区活动的电波的形状与声波的形状进行了比较-不仅是当说话者听到声音时,也是当他们在绝对无声的情况下阅读语言表达时;也就是说,当输入完全不是声学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分析内心语言在神经心理学中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我们从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戈茨基(Lev Vygosky)对心理发展的推测到基于神经成像的分析等各种来源都知道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用来探索这一现象的技术是不同寻常的和有启发性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至少可以说是意想不到的。
在我们的实验中,数据是通过所谓的清醒手术来收集的。这项技术提供了刺激和分析患者的电生理皮层活动的可能性,这些患者在部分头盖骨被移除后被唤醒。由于明显的心理、技术和伦理原因,这种技术的侵入性、涉及的器官的脆弱性以及患者在极其微妙的情绪状态下的合作使得这项研究非常困难。
例如,切除大脑皮层以切除肿瘤的外科医生不能事先知道(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切除脑组织是否会中断神经元网络,从而损害或破坏由该网络支持或传达的认知、运动或感知能力。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手术带来的潜在损害,一旦患者被麻醉,部分头盖骨被移除以进入手术部位,外科医生就会唤醒患者(短暂的过渡期,大约10到20分钟),并要求他或她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这些任务应该需要他们利用暴露的皮质。
当他们进行手术时,外科医生通过小电极刺激病人的大脑皮层(这不会引起疼痛,因为大脑中没有疼痛感受器)。如果大脑皮层某一部分的电刺激干扰了特定任务的执行,外科医生就知道切断这一部分皮质可能会对患者造成永久性损害,并可以评估是否有其他可用的手术部位。因此,患者从这些练习中获得了无价的优势,这是通过任何其他技术几乎不可能获得的。同时,这项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研究大脑功能,并获得极其重要的数据。
首先,外科医生可以确定与特定任务相关的神经元网络的关键节点在任何给定患者中的位置,这中和了与神经成像技术相关的主要问题之一:受试者在大脑中确切执行特定功能的位置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此外,外科医生可以逐步精确地记录神经元的电活动,低至单个神经元的水平-尽管目前的技术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这项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用于局灶性病变以外的病理-例如,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病例。在这种情况下,外科医生还可以植入临时电极,一旦颅盖关闭,在日常环境中提供长时间的连续信息,以及不限于手术室范围的信息。这种测量方法使我们在理解大脑中发生的神经生理过程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它提供了比神经成像技术所能提供的更精确和更明确的空间分辨率水平,并提供了间接其他测量手段所不能提供的电活动的具体测量。
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的实验。16名患者被要求大声朗读语言表达:要么是孤立的单词,要么是完整的句子。然后,我们将声波的形状与布罗卡区的电波形状进行了比较,并观察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并不出人意料)。
第二步很关键:我们让病人再读一遍语言表达,这一次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只是在脑海中阅读。通过类比,我们比较了布洛卡区的声波和电波的形状。我应该指出,一个信号确实进入了大脑,但它不是声音信号;相反,它是由电磁波携带的光信号-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我们用来表示单词(即书写)的字母所传达的信号:绝对不是声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当默读语言表达时,记录在大脑非声学区域的电波的形状与如果这些词实际上被说出时会产生的空气机械声波的结构相同。因此,语言存在的两个波系是紧密相关的--事实上,这两个波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这两个波系相互重叠,独立于声音的存在。当一个人需要与其他人交流时,声学信息并不是后来植入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代码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在声音产生之前是代码的一部分。它还排除了在阅读或用文字思考时利用声音表征的感觉只是一种建立在对公开演讲的记忆基础上的虚幻人工制品。
这两个独立的波系是语言的物理构成,它们彼此严格相关-即使在非声学领域,无论语言结构实际上是说出来的还是留在个人脑海中的-这一发现表明,声音在语言处理中发挥的作用比之前认为的要核心得多,这一发现表明,声音在语言处理中发挥的作用比之前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即使在非声学领域,语言结构也是如此。这就好像这种意想不到的关联为我们提供了一块丢失的“罗塞塔石头”,其中两个已知的代码-声波和由声音产生的电波-可以被利用来破译第三个代码: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产生的电子代码,这反过来有望导致发现人类语言的“指纹”。
这一发现提出的问题包括:从未听过出生声音的人在语言网络(包括布罗卡区)中详细描述了哪种电活动?我们能不能利用大脑皮层信息获取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思维,尽管是通过人工设备,但他们的发音装置本身已经受损,我们能再次听到他们说话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做梦或处于最低意识状态的病人所使用的语言吗?我们能不能把严重的口吃看作是不同网络中不同声音表征之间不协调的一种形式,并希望对其进行干预和治疗?这些发现会导致不道德地使用设备从不想交流的人那里摘录语言思想吗?
人类的大部分交流是通过波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可能不是偶然的事实;毕竟,波构成了最纯粹的交流系统,因为它们在不改变两个实体的结构或组成的情况下将信息从一个实体传输到另一个实体。它们穿过我们,让我们完好无损,但它们允许我们解释它们瞬间振动所承载的信息,前提是我们有解码的钥匙。“信息”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词根形式(Shape),这绝非偶然:通知就是共享一个形状。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他的“哲学调查”中问道:“人们不应该说一种听得见的语言,但却应该在想象中对自己进行内心对话,这是不是可以想象的?”这项实验的结果出人意料地以新的视角复活了这个预言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们完全提出了新的问题。
安德里亚·莫罗(Andrea Moro)是意大利帕维亚大学高级研究学院(IUSS)的普通语言学教授。他是几本书的作者,包括“巴别塔的边界”、“动词简史”和“不可能的语言”,本文就是从这些书改编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