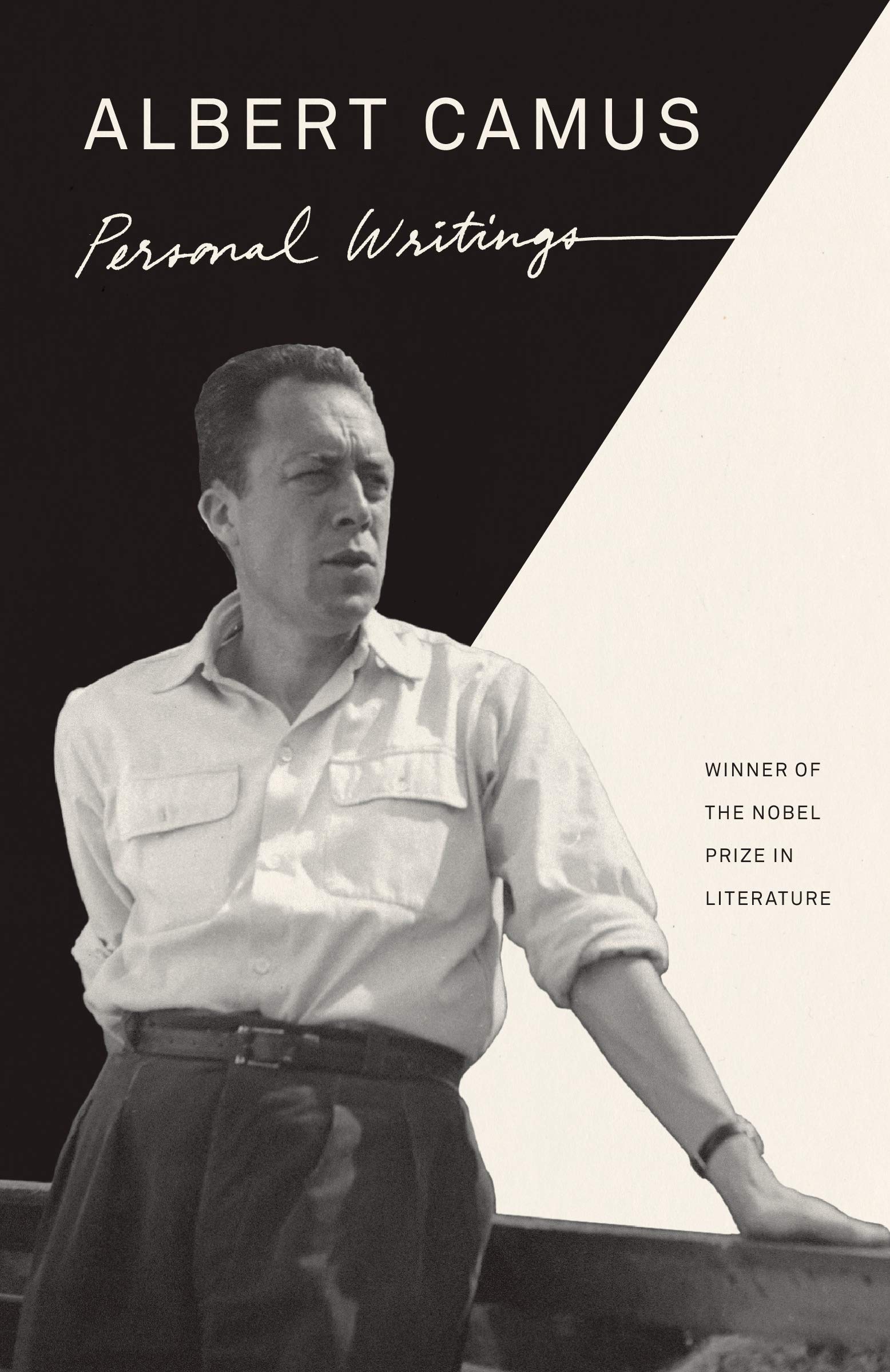对加缪来说,这永远是私人恩怨
“在隆冬时节,我终于知道,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无敌的夏天。”
如果你已经听过这句话,请停止我。你可以在贺卡和T恤上,在电子邮件的底部和海报的顶部,在钥匙链和咖啡杯上-包括坐在我笔记本电脑旁边的那个有缺口和划痕的杯子上找到它。这是一个人送的礼物,如果他更了解我,他就不会把它给我了。这是一句台词,至少当从上下文中剥离出来时,它适合咖啡杯,与其说是鼓舞人心,不如说是平淡无奇。
这句话取自“回到提帕萨”(Return To Tipasa),这是个人作品中倒数第二部作品,是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最新重新打包和再版的散文集(由艾伦·康罗伊·肯尼迪(Ellen Conroy Kennedy)和贾斯汀·奥布莱恩(Justin O‘Brien)巧妙翻译)。对于那些每天都在寻找一本语录的人来说,要事先得到警告。这位法属阿尔及利亚作家没有创作灵感。
或者,至少不是咖啡杯上的那种灵感。这本散文集提醒我们,加缪提供了一种更困难的灵感-那种不会让我们感到轻松,但让我们感到不安的那种;不会美化生活,但睁开眼睛看它的那种。正如他所写的,“我想把我的清醒保持到最后,带着我所有的嫉妒和恐惧凝视着我的死亡”-这句话,当一切都说完和做完的时候,已经说过和做过了。
不用费心在谷歌上搜索一个点缀着这个誓言的咖啡杯了。我试过了,但一无所获。
爱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在她犀利而富有同情心的序言中指出,对于那些只知道加缪是“陌生人”作者的读者来说,“这些早期散文和故事的浓郁情感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然而,我承认,即使对于一个了解加缪这一面的人来说,当我重读这些片段时,我又一次对它们的酒神般的强烈程度感到惊讶。
今天的抒情诗尤其令人振奋,即使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也会在举行狂欢之前三思而后行。对于加缪来说,抒情的情感深深植根于他的祖国阿尔及利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中。他们是从他在阿尔及尔一个贫困社区度过的童年时代流淌出来的。在那里,他由一位目不识丁、专横的祖母和一位聋哑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住在一座下垂的两层建筑里,楼梯间蟑螂出没,通往楼梯平台上的一个普通厕所。
厕所在他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1994年出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了保留去商店后收到的零钱,加缪青春期的另一个自我告诉他的祖母,零钱掉进了厕所里。她一言不发,卷起袖子,走到洞里去挖。在那一刻,加缪写道,“他明白了,不是贪婪导致他的祖母在粪便中摸索,而是迫切的需要让两个法郎在这个家里变得相当可观。”
然而,就像西西弗斯和他的巨石一样,加缪声称他贫穷的童年是他自己的。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错误的一面和正确的一面”(1937年)的序言中,加缪回忆说,他的家人“几乎什么都没有,几乎什么都不羡慕”。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贫穷让我无法想象天下和历史上一切都很好。”然而,与此同时,“太阳告诉我,历史并不是一切。”他坚称,贫穷并不是不幸。相反,它是“光芒四射”。
早期的散文洋溢着灿烂的光芒,有时是如此浮夸,以至于很难让你的头保持在层层叠叠的文字之上。在早些时候访问蒂帕萨(Tipasa)时,加缪似乎相当热衷于-被众神填满-因为他是异教徒。提帕萨是一座俯瞰地中海的罗马瓦砾堆,阳光普照。他宣称,这个地方居住着神灵,他们“在阳光下说话,在苦艾酒树叶的香味中说话,在银色的大海盔甲中说话,在原始的蓝天中说话,在鲜花覆盖的废墟中说话,在石堆中发出巨大的光泡。”他宣称,就是在这里,“我睁开双眼,敞开心扉,看到这片炎热的天空令人难以忍受的壮丽。要成为现在的自己,重新发现自己最深层的尺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是的,想到这位穿着风衣、抽着高露丝的标志性黑白形象是这些话的作者,真令人惊讶。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他写下这些话(或者,就这一点来说,他曾经穿过风衣)之前,加缪和两个朋友在罗马废墟中漫步时念出了这些话。然而,这种抒情性确实在他的小说朴素的散文中迸发出来,比如当默尔索发现自己与《陌生人》(The Stranger)中的“阿拉伯人”独自站在阳光明媚的海滩上(1942年),或者当里厄和塔鲁在瘟疫(1947)中进行夜间游泳时。
这些散文的抒情性-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20多岁的年轻人,试图成为一名作家,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他已经成为名人,发现写作是一种可怕的负担-反映了加缪与西西弗斯的另一个共同点。就像那个古老的胡迪尼一样,他怀着热爱太阳的激情憎恨哈迪斯,加缪同样怀着同样的激情憎恨意识形态和抽象,将他牢牢地绑在他将永远知道的唯一生活和唯一的世界上。他在“阿尔及尔的夏天”(Summer In Algiers)一书中写道:“没有超人的幸福,也没有超越日积月累的永恒。”他总结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石头、肉、星星,以及那些手能触摸到的真理。”
加缪的童年是光明灿烂的,但也沉浸在沉默之中。住在阿尔及尔公寓的是他的叔叔艾蒂安(Etienne),他说话困难,主要通过手势和面部表情进行交流。他的母亲凯瑟琳·海莱娜·加缪(Née Sintès饰)在得知丈夫加缪的父亲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阵亡的消息后,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而正是他的母亲占据了笼罩着加缪早年生活的寂静的震中。
在他最早的散文之一“在是与否之间”中,他写道,他的母亲白天打扫别人的房子,晚上在自己家里想着什么都不做。他解释说,她什么都不想,因为公寓里“什么都有”:她的两个孩子,她的许多任务,她的几件家具,她丈夫的一件纪念品(从他头骨上取下的贝壳碎片)。她的生活充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一幅不可磨灭的肖像画中,加缪写道,小时候,他会盯着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会“蜷缩在椅子上,凝视着她的面前,在地板上头晕目眩地寻找裂缝。夜色越浓,她的沉默就显得无可救药地凄凉。“。看着她,男孩先是被这种“动物的沉默”吓坏了,然后感受到一种他认为一定是爱的感觉,“因为毕竟她是他的母亲。”
这种母性的沉默,很快就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成为他作品的中心。加缪一生都在努力,他在“错误的一面和正确的一面”的序言中写道,“为了重新发现与沉默相匹配的正义或爱。”凯瑟琳·加缪对她儿子的爱,就像科迪莉亚对她父亲的爱一样,是最伟大的爱。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加缪并没有完全接受他母亲在场的根本陌生感。他在给第一个人的笔记中写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想要的是永远不会拥有--也就是说,让他的母亲“阅读与他的生活和存在有关的一切东西。”[…]。他的爱,他唯一的爱,将永远无言以对。“。
无敌的夏天暗示着坚不可摧的希望。但个人著作提醒我们,正如加缪没有做灵感一样,他也没有做希望。希望是给像厄皮米修斯这样的傻瓜的,他无视哥哥普罗米修斯的警告,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在这么大的范围内
这就解释了加缪自相矛盾的说法,即虽然没有理由抱有希望,但这从来不是绝望的理由。当我们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危机时,看一眼这本书中最短的散文“杏树”可能会有所帮助。在1939年法国对德国宣战后不久,加缪写下了这几页,他告诉读者,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相反,我们必须简单地团结起来,采取行动:
作为人类,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能够平息自由灵魂无限痛苦的为数不多的原则。我们必须修复被撕裂的东西,在一个如此明显不公正的世界里,让正义再次成为可能,让被本世纪苦难毒害的人民再次获得幸福的意义。[…]。这是一项超人的任务。但超人是指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仅此而已。
这句话有点长,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咖啡杯上看到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