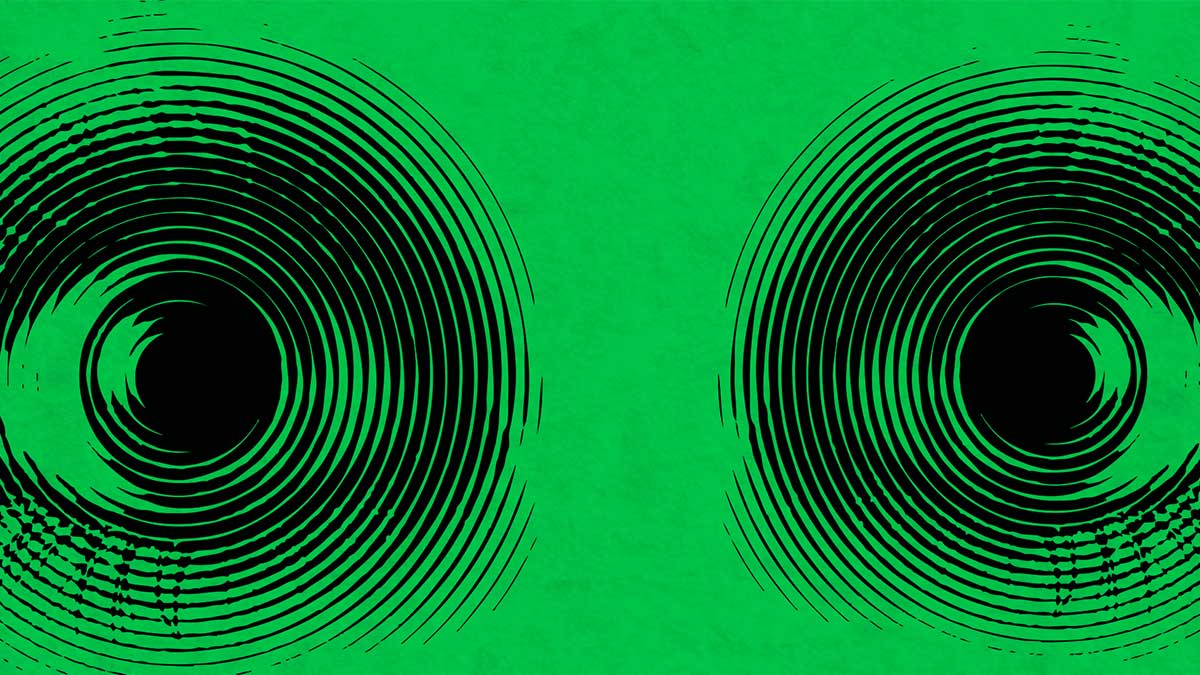不管你喜不喜欢,“聪明的药物”就要来到办公室了
在过去的五年里,你一直在管理同一个团队,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你最成功的员工在工作中使用了增强认知的药物。
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未经授权使用处方药,如ADHD药物Adderall和Ritalin,以及发作性睡病药物Modafinil,现在美国大学生中很常见。他们使用这些药物不是为了逃避工作和逃避责任,而是为了能够工作得更多、更好。
高达20%的常春藤盟校大学生已经尝试过“聪明的药物”,所以我们可以期待这些药丸在组织中的显著地位(如果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毕竟,在学生毕业的那一刻,表演的压力不太可能消失。工作要求很高的高级员工可能会发现,这些药物甚至比一个19岁的大学生更有用。事实上,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2012年的一份报告强调,这些“增强功能”,以及其他用于自我增强的技术,可能会对商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除了坊间证据之外,我们对这些药物在专业环境中的使用知之甚少。英国“金融时报”声称,它们“在城市律师、银行家和其他渴望获得相对于同事的竞争优势的专业人士中变得流行起来”。早在2008年,治疗发作性睡病的药物莫达非尼就被TechCrunch贴上了“企业家的首选药物”的标签。同年,“自然”(Nature)杂志询问其主要读者是否使用增强认知的药物;在1400名受访者中,五分之一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与此同时,管理界保持着令人震惊的沉默。但高管们迟早要面对这些药物的问题。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药物是如何起作用的(或不起作用),并问自己一些关于服用它们意味着什么的严肃问题。
首先,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聪明的药物确实有效。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和牛津大学(Oxford)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莫达非尼对那些没有睡眠剥夺的人有显著的认知益处。药物治疗提高了他们的计划和决策能力,对学习和创造力有积极作用。另一项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表明,莫达非尼有助于睡眠不足的外科医生更好地制定计划,重新定向他们的注意力,并在做出决定时不那么冲动。
不难想象,这些好处会受到一些组织的欢迎。美国军方已经开始试验莫达非尼,包括印度空军飞行员的受控使用。
我们知道这些药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在医学上是安全的。根据哈佛-牛津研究的合著者安娜-凯瑟琳·布雷姆(Anna-Katharine Brem)的说法,莫达非尼在受控环境中使用时“几乎没有副作用”。在这项研究发表后,媒体报道开始将莫达非尼称为世界上第一种安全的智能药物。
而且这些药物并不是很难买到,这取决于你所在的地方。莫达非尼在全球的年份额为7亿美元,估计标签外使用量很高。虽然这些药物可以在互联网上购买,但它们的法律地位因国家而异。例如,在英国,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拥有和使用莫达非尼是合法的,但在美国是不合法的。
ADHD药物销售增长迅速,2015年的年收入约为129亿美元。这些药物可以由有处方的人合法获得,其中也包括那些故意伪造症状以获得所需药物的人。(根据2010年发表的一项实验,医生很难区分那些假装症状的人和真正有症状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医生认为你期望的生产力水平或你对一个大项目的压力足以开出药物,那么假装可能就没有必要。
由于这些药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安全、有效和容易获得的,它们对工人和组织都构成了几个道德挑战。
使用这些药物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吗?我们是否应该将聪明的药物比作兴奋剂-换句话说,就是作弊?
是的,根据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一项新政策,该政策称,“未经授权使用处方药来提高学习成绩”应被视为作弊。“。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法学教授尼塔·法拉哈尼(Nita Farahany)表示,不是这样的。她称这项政策“考虑不周”,认为“禁止智能药物使学生没有能力为自己做出受过教育的选择。”
对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来说,“兴奋剂的问题是,它能让你比没有兴奋剂的情况下更加努力地训练。”他争辩说,我们不能因为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过药物,就轻易地称某人为骗子。他解释说,这相当于一个学生从老师那里偷了一张试卷,然后不再回家,根本不学习,而是去图书馆,加倍努力学习。
另一个道德担忧是,这些药物-特别是常春藤盟校学生或任何已经处于特权地位的人使用时-可能会拉大优势者和劣势者之间的差距。但另一些人则反驳了这一论点,称这些药物可以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缩小差距。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迈克尔·安德森博士解释说,他以ADHD(他称之为“捏造”的诊断)为借口,给真正需要的孩子开阿得拉--来自贫困家庭、学习成绩不佳的孩子。
哲学教授尼科尔·文森特认为,不管怎样,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些类型的兴奋剂,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不断扩大的神经学竞赛中。但这一定是一件坏事吗?不,法拉哈尼说,他认为认知功能的改善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种社会公益。她认为,更好的大脑功能将带来社会效益,“比如经济收益,甚至减少危险的错误。”
是否应该鼓励在工作中使用这些药物?作为一家医院的经理,如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药物能改善他或她的工作,你会希望你的外科医生受到这些药物的影响吗?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果能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你会更愿意让飞行员服用药物吗?
公司已经对员工的生活方式了如指掌。在可穿戴技术和健康筛查的帮助下,公司现在可以分析身体活动-例如锻炼、睡眠、营养等-与工作表现之间的关系。有了健康员工表现更好的理由,一些公司通过对拒绝表现的员工实施制裁,强制要求他们进行锻炼。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数据,在提供健康筛查的美国大公司中,近一半的公司使用财务激励来说服员工参与。
当然,今天公司似乎不太可能强制使用药物。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公司可以惩罚健康状况不佳的人,为什么这些公司不能,至少在理论上,激励药物的使用,如果它非常安全,并使公司更有生产力和利润?
撇开法律问题不谈,这并不是很难实现的。许多公司已经有内部医生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包括药物测试-可以受雇来控制和规范使用。组织可以将这些药物整合到已经存在的健康计划中,以及健康的饮食、锻炼和良好的睡眠。
聪明的药物能让人们在工作之余过上更好的生活吗?也许反对使用智能药物的最有力的理由是,这可能会导致一场愈演愈烈的企业激烈竞争。很明显,我们目前无法在工作和非工作之间划清界限,这是令人痛心的。
各组织,甚至整个国家,都在与“总是在工作”的文化作斗争。德国和法国已经通过了一些规定,禁止员工在下班后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几家公司已经探索禁止下班后的电子邮件;如果一家意大利公司在一周内禁止所有电子邮件,员工的压力水平就会下降。这并不奇怪:盖洛普(Gallup)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那些经常在下班后查看电子邮件的人中,约有一半的人表示压力很大。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莫达非尼就是这一点的一种表达,是一种新的全天候工作程序的症状。但如果事实恰恰相反呢?比方说,你可以用比平时少得多的时间完成一项任务。然后,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利用剩下的时间,与家人一起度过,做志愿者,或者参加休闲活动。想象一下,一种药物帮助你在下班前集中精力清理办公桌和收件箱。这难道不能帮你在回家后放松一下吗?
换句话说,智能药物可以用来缓解压力,同时也能提高我们的生产力。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以更专注和更有成效的方式缩短工作时间,而不是以不专注和没有生产力的方式长时间工作。
综上所述,很难说高管们将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智能药物的问题充斥着伦理和商业困境。但是,就在我们问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在工作场所转向了聪明的药物。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作为一项新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与五个经常在工作中吸毒的人进行了交谈。他们的工作都很成功,经济上有保障,关系稳定,总体上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他们中没有人计划停止使用这些药物,到目前为止,他们对雇主隐瞒了这个秘密。但是,随着他们的同事变得更有可能开始使用相同的药物(毕竟人们都在谈论),他们还会继续这样做吗?
我还试图联系那些对这些药物有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在他们的公司),但都没有成功。我不禁要问:他们是不是完全不知道毒品的存在?还是他们在积极压制这个问题?目前,公司不能忽视智能药物的使用。而且高管们可以假装这些药物并不存在于他们的工作场所。但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