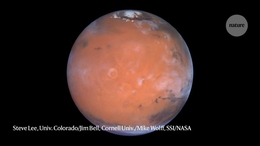复杂性科学家通过适应克服交通拥堵
墨西哥城以其博物馆、美食和文化而闻名,但也以交通拥堵而闻名。这座城市有近2200万人口和600多万辆汽车,每天上学或上班两个小时是许多人的规则。也许是因为延误是例行公事,上课或开会迟到10到15分钟通常是社会可以接受的。
人们如何在墨西哥首都出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两个变量,它象征着世界上一半人口面临的城市流动性挑战。在过去的20年里,这也是卡洛斯·格申森(Carlos Gershenson)最喜欢的问题,他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隶属于该校应用数学与系统研究所和复杂性科学中心。
格申森认为,要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科学家需要放弃传统方法,寻找新的方法来研究不断变化的挑战。2016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写道,“科学和工程都假设世界是可预测的,我们只需要找到适当的自然规律就能预见未来。”“但对复杂系统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通过使用专门研究适应而不是预测的计算机模拟,格申森将自组织作为一种改善城市流动性的工具。尽管他向各个城市提出的大多数交通系统解决方案都遇到了政治和官僚障碍,但他的想法于2016年在墨西哥城的地铁系统中成功实施。仅通过明确发出信号让乘客在上车前等在哪里下车,这个试点项目就几乎消除了上车过程中的所有冲突和推挤,并将上车时间减少了高达15%。
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学教授、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New England Complex Systems Institute)所长亚尼尔·巴尔-扬(Yaneer Bar-Yam)说,“卡洛斯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自组织交通流及其对现实世界控制和优化的影响的理解水平。”他曾在2007-2008年间与格申森(Gershenson)合作管理一个博士后项目。他补充说,格申森“重新设计了问题,这是一个人所能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末在Arturo RosenBlueth基金会攻读计算机工程本科以来,复杂性就一直吸引着Gershenson,在那里他对人工智能产生了兴趣。后来,在苏塞克斯大学攻读进化论和适应性系统硕士期间,他更深入地研究了哲学和认知科学。但当他在布鲁塞尔的自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说:“我对认知科学有点失望,因为它最终是非常主观的。”他重新关注自组织系统。
虽然Gershenson研究自我调节红绿灯和地铁系统,但他热衷于将自行车作为一种更高效、更少污染的城市旅行工具。他在社交媒体上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并在国家报纸Reforma上写了一个专栏,在那里他分析了科学、科学政策和政治等话题。
8月下旬,广达在格尔申森位于墨西哥城的家中通过视频电话与他进行了交谈,以了解更多关于自组织如何改善城市机动性的信息。为清楚起见,采访内容经过了浓缩和编辑。
您最初是如何涉足自组织复杂系统和城市移动性领域的?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高速公路交通很感兴趣:我编写了一个有无红绿灯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模拟程序。如果你能预测汽车什么时候会穿过十字路口,那么你就可以防止它们撞车,即使它们从未停下来;你只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它们的速度。在我的模拟中,它们几乎从来没有崩溃过,当然,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我已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了。
我还知道伯克利在20世纪90年代开发了一个有车队的项目,墨西哥著名工程师路易斯·奥古斯丁·阿尔瓦雷斯-伊卡扎(Luis Agustínálvarez-Icaza)参与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让车队自动化,这样汽车就可以以每小时55英里的速度紧随其后,从保险杠到保险杠,这是增加高速公路通行能力的一种方式。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这样做了,效果很好,但由于保险公司的原因,他们无法推出这项服务。有趣的是,20多年后,自动驾驶汽车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再一次,保险公司对他们施加了限制。
对于我的关于自组织系统的博士项目的第一次申请,我想,“让我们试着让一排排的汽车像鸟一样成群结队。”一群鸟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组织的典范。我在模拟中实施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其中之一是自组织:这就像有一个排,他们都试图以与邻居相同的速度前进。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因为一些汽车会加速,但随后会减速,你会得到一些令人讨厌的摆动。它没有起作用,我从来没有把它作为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
最有效的策略是自私的策略,每个人都试图尽可能快地前进。
事实上,我的第一个博士生路易斯·恩里克·科特·贝鲁科(Luis Enrique Cortés Berrueco)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他用博弈论和交通模拟来研究自私司机和合作司机之间的影响。事实证明,如果道路上的汽车密度较低,自私的司机会导致更高效的交通。但这只是在低密度的情况下,它只是着眼于效率。它也更危险。
如果你是中等密度的,那么当一个司机切断另一个司机时,它会减慢他们后面的每个人的速度。所以它就不那么有效了。如果密度太高,他们的自私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换车道。
这是实现或试验这一理论的完美方式。因为我学的是工程学和哲学,所以我喜欢发展概念,但也喜欢用这些概念来解决问题或构建系统。
一旦您构建了系统,您的概念中的一些漏洞就开始显露出来。你面临着你没有预见到的问题。这迫使你改进你的理解,修改你的概念体系。答案总是带来新的挑战。但一旦你解决了这些挑战,你就可以回去,做出更合理的概念性贡献。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单个车辆的轨迹进行建模,因为它具有均匀的运动和加速度。这是基本的高中数学。当然,还有更多的细节,比如摩擦、风等等。但你可以忽略这一点。
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一辆车在未来某一时刻的准确位置不仅取决于它的加速度和速度等,还取决于路上是否有其他汽车或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如果其他车辆开得慢或快,根据每个人是否危险驾驶,就会有或多或少的空间。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互依存性。你无法预测一辆车会提前两分钟到哪里,因为这取决于前面的车是否准时对红绿灯做出反应,是否分心,是否有公交车,是否在不该停的地方停车,是否有人在擦挡风玻璃,是否延误了一切。
复杂性是由相互作用定义的,在城市移动性中,相互作用非常重要。这甚至没有考虑司机的人为因素,比如我是否分心、昏昏欲睡、下药或生气。
如果你试图简单地解决一个问题,而不考虑相互作用,你的解决方案将相当有限。城市交通领域有一句话(由技术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撰写):“增加高速公路车道来解决交通拥堵,就像放松腰带来治疗肥胖一样。”这是一个解决方案,没有解决运输需求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如何满足这种需求的问题。
开发反映高度复杂性的模型或模拟有多难?一定有无限的变量。您如何确定要包含哪些内容的优先顺序?
这取决于你想要你的模型做什么。如果你想让你的模型做出预测,那么是的,你需要包括很多细节。假设我们想要对墨西哥城的交通进行建模。然后我们需要有多少辆车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沿着哪条轨迹行驶。他们的平均汽车加速速度是多少,是否下雨,等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交通流量,你想要尽可能多地添加细节。
但是,如果您希望您的模型只是为了理解系统而不是预测它,那么在许多情况下,非常抽象的模拟可能会很有用。我的第一个模拟有点复杂,因为它们试图变得逼真。后来,我开始做更简单、更抽象的模拟-车辆有无限的加速度,车辆之间的空间有一种对称,这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但即便如此,这些模拟让我们发现在城市交通中有6到10个相变:你可以看到随着密度的增加,速度或流量会有急剧的转变。如果你有一个更复杂的模型,你就看不到这一点。
你已经在不同的城市做过模拟。墨西哥城有什么特别之处,使它的研究变得有趣?
嗯,首先,我们住在这里。[笑]。根据不同的指标,它的机动性是世界上最差的。此外,我们与当局有更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影响正在做出的改进或决定。当我在布鲁塞尔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们联系了那里的交通部长,…。比方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政治问题。
告诉我你在墨西哥城利用交通灯加快通勤速度和减少排放的项目。
红绿灯系统通常以一种应该是高效的方式进行计时和编程,但每个红绿灯拦截的确切车辆数量不断变化。即使你根据平均每分钟13辆车的流量来衡量,一分钟会有20辆车,另一分钟会是零辆,另一分钟会有6辆。
协调所有这些程控红绿灯以保持车辆行驶是一个问题。当你有更多的交叉口要协调时,它对计算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你增加和减少汽车,它也会改变。这是不可能预测的。
自组织红绿灯有传感器,可以让它们通过修改信号的计时来响应到来的交通。他们不是在试图预测,而是在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交通流量。但如果你能适应精确的需求,那么就不会有空转。汽车等待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其他汽车正在横穿马路。
红绿灯告诉汽车该怎么做。但是因为有了传感器,汽车也会告诉红绿灯该怎么做。有这样的反馈促进了排的形成,因为协调10个10辆车的排比协调100辆车更容易,每辆车都有自己的轨迹。
这自然而然地促进了“绿色浪潮”的出现,也就是一排排不停车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汽车。您没有在系统中编程“将会有一个绿色波浪,它将以这个速度减速”。交通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绿波本身。而且它都是自组织的,因为不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之间没有直接的通信。
这是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控制系统的方式,因为在控制论中,我们想要确定将会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您不需要告诉系统解决方案是什么。但是您要设计交互,这样系统才能不断找到所需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你想要做的,因为你不知道问题会是什么。
在模拟中,我们发现,通过实施自组织红绿灯,你可以减少25%的出行时间。而且由于在红灯时空转的汽车少了很多,排放也大大减少了。如果你试图估计一个像墨西哥城这样大的城市的减排效果,这相当于用10条Metrobús线路换取汽车,成本只有一条线路的一小部分。
当然,这是在模拟中进行的。我们不能确定,有了公共交通和墨西哥司机等,它是否会奏效。交通效率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突然交通流量变得更好了,这可能会激励更多的人开车。当然,如果你在街上有更多的汽车,那可能意味着比你节省的排放量更多。
所以我们想在小规模上试一试。但是已经15年了,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们一直无法在任何地方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布鲁塞尔试过,我们在纽约试过,我们在摩洛哥试过,我们在墨西哥试过。
我的同事斯特凡·莱默和德克·赫尔宾为德累斯顿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方法与我们的略有不同,但很管用。他们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过,比如五年。市政府对此表示支持,并为其提供了资金,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它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问题可能是,大多数工程师接受的是基于预测要控制什么的传统方法,他们试图改进这些方法。但是对于复杂的系统来说,预测几乎是没有希望的。当你达到最优的那一刻,问题就会改变。这个解决方案已经过时了。
我们已经展示的是,有了自组织,你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你可以总结为从预测到适应的转变。我们利用自组织技术对火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系统进行了模拟管制。它比大多数试图预测的控制机制要有效得多。
例如,在地铁系统中,每次列车到达车站,站台上都会有不同数量的乘客。因此,传统的做法是:“你必须在车站等这么长时间。”如果有更多的乘客想进去,他们不会让火车停留更长时间,如果乘客更少,他们就不会让火车停留更少的时间。如果你放松这些事情,那么系统的容量就会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没想到人们会开始排队上车。我们希望他们只给人们留出下车的空间,而不是他们会排队。因此,这是意想不到的,但它是有效的。我们实现了目标,但直到它完全起作用后,我们才明白它为什么起作用。
以前,游戏规则是:如果你想上火车,你必须推。如果你不推,你就上不了火车,所以即使你不想推,如果你想上车,你也必须推。这是每个人都在推动的反馈。
我们通过改变平台上的信号实现的是改变游戏规则。现在,如果人们排队上车,你就有了一种机制,把你什么时候上车的模棱两可的情况换成了“第一个排队的人是第一个上车的”,所以不需要再推了。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仍在推进的人就会受到制度的惩罚。人们会说,“等等,你为什么要推?不用再推了!“。
通过研究不同场景下的复杂性,您得出了哪些主要结论?
我认为改善城市机动性的最大挑战不是科学的,而是政治和社会的。
如果你说,“让我们改善城市流动性”,每个人都会同意。没有人想要继续这样下去,忍受污染、经济成本、浪费时间、压力和一切。我是说,每个人都会同意。但是怎么做呢?那么每个人都不同意。
因此,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如何为政府和公司、学术界和社会其他方面制定的解决方案建立协调机制。我们正在努力让不同的部门参与进来,他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但这些事情需要数年时间,而且情况恶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现在,随着流行病的蔓延,我们已经对如何在被迫时真正减少机动性有了一些看法。但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我们是从中吸取教训,减少旅行,尝试远程做更多的事情,还是回到我们的旧习惯,给每个人带来巨大的负担。
你是个狂热的自行车手。在一个车流量很大的城市里,骑自行车的人做得怎么样?
我认识的大多数研究交通的人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因为这是在城市里旅行的最好方式。对于中等距离,它可以是一种解决方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但你会看到在自行车基础设施投资的城市,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每个人都受益,即使是那些不骑自行车的人,因为没有那么多汽车。
当我们进入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时,你会有什么建议?你认为官僚主义和政府仍然是最大的障碍,而不是实际的技术发展吗?
我认为机器与我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但我认为它们不会取代我们。他们正在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和协调能力。很有可能,决策将更加分散。但最终,你遇到了责任问题,这又回到了保险挑战上:如果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发生了事故,那是谁的错?房主的?汽车制造商的?开发商的?
这些系统中的许多允许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信任他们的原因。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完全信任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有尽可能多的弹性。自组织为您提供了:它使您有可能在保持功能的同时进行适应。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准备好迎接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