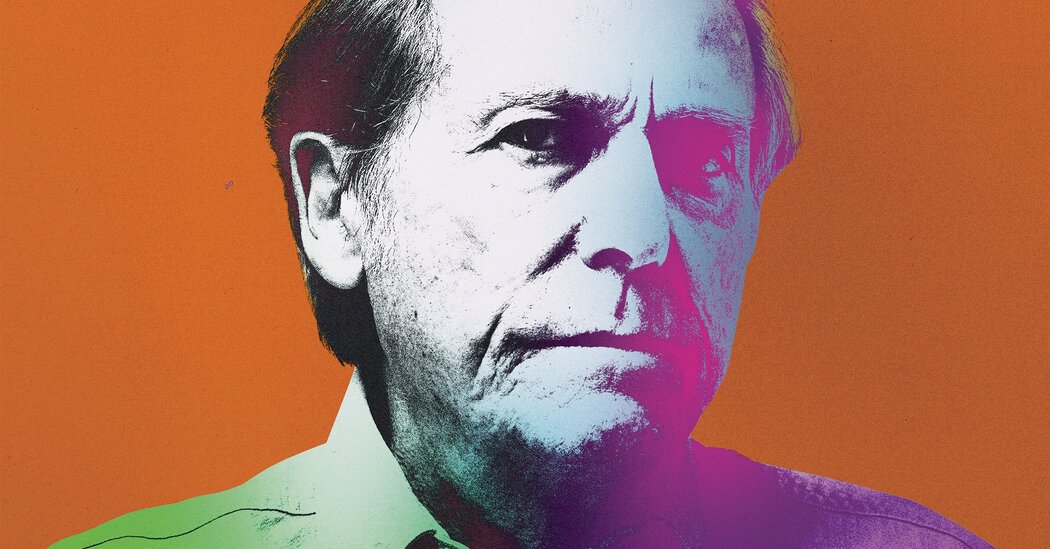我们都生活在唐·德里罗的世界里。他也被它弄糊涂了
一种无处不在的偏执狂。极其荒谬。阴谋和恐怖主义。技术异化。暴力正在冒泡,随时准备沸腾。这一直是唐·德里罗精湛的小说中的题材。现在是我们呼吸的空气。近50年来,83岁的德里罗创作了17部小说,其中包括“白噪音”(White Noise)、“天秤座”(Libra)和“冥界”(Underworld)等经典作品,他以最高的精确度和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召唤了美国经历中更黑暗的潮流。他对时代精神的敏感度经久不衰,以至于在讨论他的作品时,经常会出现“预言性”和“预言性”这样的词。他们很可能会再次出现在他的新小说“沉默”(The Silence)中,在这部小说中,2022年超级碗周日的一个神秘事件导致各地的屏幕变得空白。“我们文化发展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德里罗说。“我不认为这是好与坏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问一些“沉默”中没有的东西,至少现在不会了。在我读的第一本厨房里,有一个场景,一个人物在背诵灾难性的事件,提到了新冠肺炎。然后我被告知这本书有改动,并被送到第二个厨房。新冠肺炎走了。你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我没有把新冠肺炎放进去。是别人干的。其他人可能会认为这会让它更具时代性。但我说,“那是没有理由的。”
我很震惊,一个编辑或者任何一个有胆量把任何东西塞进你的书里的人,更不用说提到新冠肺炎了。它不会留下来,这是肯定的。
尽管如此,“沉默”给人的感觉是与当前的焦虑保持一致。是什么种下了种子?让我继续前进的是一个空白屏幕的想法。它引领了一切。然后是超级碗的概念,这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有几年了。看足球比赛让我们在一个方面走到了一起,然后突然看着一块空白的屏幕,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注脚。还有一次我乘坐的航班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出于某种神秘的原因,我做了笔记。头顶上的行李箱下面有一块屏风。所以我看着屏幕,那里有外面的气温,纽约的时间,到达时间,速度等信息。我不习惯这样。
我讨厌当我在飞机上意识到我不得不一直盯着屏幕的时候。你对这件事感兴趣的是什么?耐人寻味的是,我也被迫去看。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
这让我想起了“沉默”中的人物麦克斯和吉姆,他们总是把屏幕作为产生自己想法的替代品,而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这样做的。拥有屏幕这根持续不断的认知拐杖对我们的思维有哪些影响呢?科技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谈话方式。在这突如其来的技术进步之前,一切都不同了。我们的思维不那么沉思,而多少更具即时性。我不用手机,因为我想保持传统的思维方式。它帮助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页上的单词上。这一直是我工作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元素:简单地说,就是单词在页面上的出现,单词中的字母,句子中的单词。如果我可以继续说一分钟,我想它是从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的“名字”开始的:我记得清楚地看到了字母之间的视觉联系,一个单词中的字母之间,一个句子中的单词之间的视觉联系。当我开始写“名字”的时候,我决定将每一页限制在一段,每页一段,这在视觉上帮助我更深入地集中注意力,从那以后,我或多或少一直在这样做。例如,我记得在“地下世界”的结尾有一句话:原始的杂乱无章。“未加工”一词包含在“杂乱无章”一词中。在“名字”之后,这类事情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明显了。我必须补充一点:我仍然使用一台旧的奥林匹亚打字机。它的字体很大,让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页上的字母。
你所说的是对文字和语言美学的敏感度。数字生活是否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都是退化的吗?我不认为这是堕落。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是进步的一种形式。这就是技术之路。我不一定很想回到电脑出现前的日子。我接受我们所拥有的,在很多方面我对此感到惊讶。
你觉得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巨大的推力,如果它向前的话。无论技术能做什么,都会变成它必须做的事情。这是无法控制的。
比如,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监视某人,我们就会通过他们的电话监视他吗?绝对一点儿没错。如果某件事能发展起来,它就会发展起来。许多事情正在朝着人类和文明的普遍利益发展,然后是个人将会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找到了做这件事的方法。这就是造成技术和人们生活各种混乱的原因。因为一个人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做一些技术上的事情,他或她,取决于类型的人,他或她会这样做。
你不使用智能手机和电脑,对吗?非常少。我用旧电话更舒服。我正在用一部老座机和你通话,这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这让我感觉很正常。
你看什么网站吗?不,我没有。我妻子有一台电脑,但是没有,我对它不感兴趣。
你的小说,因为它是关于任何一件特定的事情,都是关于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所以我很好奇:什么能给你带来安慰?写作给我带来慰藉。试着去理解可能有点自我启蒙,也许是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但这是有帮助的。我个人的问题是,我还会继续写小说吗?答案是,我只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我可能会考虑安排一卷我的非虚构作品。我不知道。
也许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也许答案就是小说本身--但经过50年的思考和写作,你是否觉得自己对这个在很多方面让我们其他人感到困惑的美国社会有了坚定的理解?我想我一直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持开放态度,就像其他人一样对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不认为我所做的工作能让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任何深刻的认识。我的意思是,在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我不能与你讨论一定程度的情报问题。
想必你也不想这么做。你是对的。我会看总统辩论吗?我可能在看棒球比赛。
你有没有在空荡荡的体育场看比赛?我看过一些。空位令人吃惊。与看台上有假面孔的其他体育场相比,我更喜欢空着的座位。我认为这是对棒球的亵渎。空着的座位,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令人满意。由于看台上没有人,这项简单的、传统的棒球运动几乎被提升为一种艺术元素。这一切都很风格化。我注意到了我通常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人们一直在打界外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界外球。界外球。三又二数,界外球-几乎不可避免地在三和二数的情况下。这一切的奇特之处。打出一支本垒打,打到空的看台上。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如果你已经写完了你的上一部小说(正如你建议的那样,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你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有何感想?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第一本小说会出版,它是由第一个看过它的出版商出版的。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很幸运。
我理解你对能够以作家的身份谋生的感激之情,但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你做了你开始做的事情了吗?也许在20世纪70年代,我可以做得更好,从那以后,在较小程度上,我可以做得更好。但当时我认为我已经尽我所能了。回想起来,某些小说可能会更好。我能不能说我应该克制自己开始写这类小说的冲动呢?
如果你想的话。当然,撇开“亚马逊人”不谈。[笑]。也许我可以在“身体艺术家”中做得更好;“Point Omega”。这些书的反响很热烈,特别是“点欧米茄”,但当我工作的时候,我想我并没有完全达到我通常会达到的热情水平。但我还是继续往前走。
“沉默”真的是一种职业总结吗?我问是因为它让我想起了你的一堆其他书。就像“玩家”一样,它始于飞机。超级碗与“终点区”有着足球联系。就像“白噪音”中那样,有一场灾难性的事件。甚至有两个人物试图记住科学家摄氏度的细节,这就像你的短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午夜”中的来回,人们试图记住关于摄氏度的一些东西,这甚至是一段快速的来回往返。在短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午夜”(Midnight In Dostoevsky)中,人们试图记住关于摄氏度的一些事情。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我不认为书与书之间的联系。也许除了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一事神秘地出现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美国人”的结尾。这个角色驾驶他的汽车沿着肯尼迪总统所走的车队路线行驶。几年后,我决定写一本以肯尼迪总统遇刺为题材的小说可能会很有趣。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需要我做大量的研究。奇怪的是,我最终来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布朗克斯区,因为我得知李·奥斯瓦尔德和他的母亲在布朗克斯区住了一年,住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地方。我去拜访了他的老邻居。也许这就是我开始看“天秤座”的原因。我决定用他的出生星座给这本小说命名。我希望是天蝎座,因为我喜欢这个词。但他的出生星座原来是天秤座,天秤。我已经满足于此了。
你知道你的两本书里还出现了谁吗?默里·杰伊·西斯金德。两次都被描述为留着“阿米什”胡须。默里·杰伊!提醒我,他在哪本书里?
“亚马逊人”哦上帝啊。你怎么记得的?我不记得了。
我想我刚有独家新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公开承认过“亚马逊”是你写的。我可能是这样做的,在某个地方或其他地方。[笑]。也许是给来自泰国的采访者。
让我从你的工作中回到主题:偏执,阴谋,信息过载。所有这些东西的威力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人们在你的书中看到预言性的部分原因。看到你的主题继续以这样的力量在世界上上演,你得到了什么?嗯,我认为肯尼迪遇刺后的整个几十年都是偏执狂的时代。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或者更年轻一点的人来说,这就是超越了整个文化的东西。人们对每件事都疑神疑鬼,突然之间就有了所有关于暗杀的书籍和研究。我有整个图书馆的书架,包括沃伦报告的26卷,其中一半是我在写“天秤座”时读得相当透彻的。它吞噬了文化。这并不夸张。在1963年11月22日之后,每个人都开始以偏执的方式思考。然后它就不见了。
你认为文化没有变得更偏执吗?我们可以说,在大流行的当前形势中存在阴谋因素,但我不确定这个时代的评论员和学生对此有多认真。否则,我认为现在的阴谋感不像过去那么普遍了。
让我瞎猜一下:你读过文化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吗?我不这样认为。
他有这样的想法,每个时代都有他所说的感觉结构,这基本上是人们体验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方式。在过去,你曾写过肯尼迪遇刺事件和9/11事件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大流行会改变我们的感觉结构吗?绝对一点儿没错。问题是它将如何改变?当我们最终能够生活,可以说又是正常的时候,这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如何回想这次大流行?我们还会继续受到它的影响吗?我想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会感到巨大的宽慰,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很难回到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通的状态。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感觉。我希望这主要是一种重新发现的自由感。你想去看电影吗?你想去博物馆,在餐厅用餐。那些平凡的事情将会显得非同寻常。
大流行期间你去过曼哈顿。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如何?如果我散步,一条有四个人的街道会看起来几乎很拥挤。我们应该戴口罩,但不是每个人都戴,人们必须避开某些人。一个人必须有意识地意识到谁正向我们走来。谁在我们后面。尽管一个人可能会期待外出一段时间,但这些自我强加的限制开始发挥作用,人们预期的任何乐趣可能都不会完全体验到。
这听起来和你小说里的一模一样。老实说,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在胡言乱语。
你的小说里也有角色胡言乱语!看,这都是有联系的!这一切都是有联系的。
显然我读了太多唐·德里罗的书了。说到这里,我可以问你一个左外野“拉特纳之星”的问题吗?我一直想知道托马斯·品钦对那本书的影响有多大。在我看来,它在风格上更接近他的作品,而不是你自己的其他作品。我的天啊。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对那个时期的品钦很感兴趣。它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它可能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还有另一个风格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像“Zero K”这样的书体现了可能被认为是晚期风格的东西。你认为这样想有什么道理吗?当我想到“Zero K”,就我能记得的程度而言,我是在视觉上思考。其中一个人物杰夫,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然后是秘密的沙漠大院和地下洞穴,冰冻悬架,人们希望在某个时候恢复生命。有很多著名的运动员就是这样做的。
泰德·威廉姆斯的头被冻住了。是泰德·威廉姆斯。人们能复活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再一次,我在视觉上思考:一排排人在这些吊舱里,处于冷冻悬挂状态。当我在做“零K”的时候,我在想,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当然我没有。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奇怪的部分标题,“第一部分:车里雅宾斯克时代”(Part 1:In the Time of车里雅宾斯克)。“第二部分:康斯坦丁诺夫卡时代。”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但见鬼的谁知道那是什么。
我怀疑这可能是你对我很多问题的回答。相信我,这会是个诚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