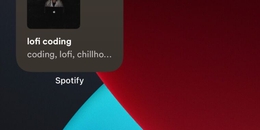魅力:现在你有了,现在你没有了
读大卫·A·贝尔(David A.Bell)对现代史上魅力的精湛描述,不去思考高尔夫球车上的人,是不可能读到“马背上的人”(Man On Horse Back)的。尽管从未提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但我们国家自己的“不能具名的人”几乎在每一页上都投下了恶意的阴影。在他清晰而令人振奋的历史中,贝尔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位富有魅力的骗子是如何占据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职位的。
就像探戈一样,魅力也是如此:它需要两个人。就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各种著作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尽管没有进行这种比较,从被广泛阅读的《政治作为一种职业》(1919年)到很少有人阅读的《经济与社会》(1922年)。韦伯自己也是一位颇具魅力的人物-他的学生们对他令人着迷的存在感到惊叹-韦伯将魅力十足的人定义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者至少是特别特别的非凡力量或品质”的人。这些力量拥有拯救这个世界的希望。(韦伯圈子里的几位成员相信,用政治理论家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的话说,他们的导师是注定要把德国从战后政治和经济混乱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
然而,与伯克利主教的最有魅力的人不同的是,韦伯声称,只有当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被认为有魅力时,他才会保持魅力。他认为,有一种互惠或“认可”将有魅力的领导人与他们的追随者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是单方面指挥,不如说是双方同意;从本质上讲,这种共识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归根结底,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言家,也取决于所见的人。
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不仅属于失败的房地产开发商和赌场大亨,也属于成功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在考虑这样的数字之前,贝尔首先从一个失败的冠军竞争者开始:帕斯夸尔·保罗(Pasquale Paoli)。虽然现在科西嘉岛以外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科西嘉岛是他为之奋斗的独立岛屿,但最终未能实现-保利在18世纪中叶确实在欧洲成名。
他能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早在他成为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之前,博斯韦尔就因写了一本类似保罗的传记而声名鹊起。1765年,这位年轻而易受影响的苏格兰人在他的岛上大本营拜访了这位革命领袖,从而将他的欧洲之行推向了高潮-贝尔指出,博斯韦尔致力于会见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伟人。然而,贝尔没有注意到的是,博斯韦尔之所以进行这次旅行,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被誉为伟大,还因为他们承诺回答生死的重大问题。
虽然保罗不能提供这样的答案,但他给了博斯韦尔一个目的:传播这位非凡人物的名字和事业。在他回到英国后出版的关于他访问的畅销书中,仍然被迷住的博斯韦尔创造了一个比世界已经知道的他更大更大,但也更私密和亲密的保罗。鲍斯韦尔宣称,保利是一个“生活在古代”的人--他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最高理想的实现”。保罗令人敬畏的体格和头脑不仅打动了博斯韦尔的想象力,而且他平等主义和博爱的性格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博斯韦尔所坚持的那样,他是一个属于人民的人,而不是高于人民之上的人。
最后,保利没有解放科西嘉岛。法国很快吞并了这个岛,保罗在伦敦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年。但他确实解放了欧洲其他国家-或者至少是有文化的精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政治领导力和魅力。正如贝尔所说,保罗取代了早期遥远的统治者和被动的臣民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建立在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想象中的、密切的关系上的模式;他是一个非凡的领导人,他的非凡品质鼓励普通人与他产生共鸣。构成保罗魅力的元素-被博斯韦尔磨砺和放大-成为随之而来的成功革命魅力的模板。这位苏格兰人对保罗的刻画,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与人民的融洽关系,都代表了一些全新的东西。他的英雄气质,而不是被旧政权的等级世界所框定,现在被大西洋两岸正在涌现的新的民主政权所照亮。这种新型领导人不是站在他领导的人之上,而是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在新兴印刷媒体的影响下,这一新的政治场景中,合法性不是来自于领导人对上帝的直接联系,而是来自于他与人民的魅力纽带。
然而,魅力是反复无常的。它不仅依赖于领导人和被领导者之间反复无常的共识,而且还诱使领导人从民主统治的保障转向
在他对乔治·华盛顿、拿破仑·波拿巴、图桑·卢维特和西蒙·波利瓦的丰富而富有成效的肖像画中,贝尔描绘了这种动荡动态的各种弧线。我们被提醒,华盛顿显然不可抗拒地登上国会圆形大厅的天花板,并不是所有同时代的人都对此欢呼雀跃。在大陆议会就是否赋予华盛顿更大的战争权力进行辩论时,焦急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承认,他“看到我们的一些议员倾向于崇拜自己手中已经熔化的形象,感到很难过”。亚当斯补充道:“我说的是对华盛顿将军的迷信崇敬。”
最终,华盛顿证明了他的神话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将军还是作为总统,他都拒绝将他令人敬畏的权威转变为威权主义。贝尔毫不客气地抨击了我们自己的伏地魔,他写道,“与他的一些继任者不同,华盛顿并没有吹嘘他的人群的规模,更不用说试图通过参考他的民众支持率来压制或威胁他的对手了。”事实上,华盛顿是古罗马人的倒退--但回到了辛辛那图斯,而不是凯撒。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华盛顿辞去军事指挥权,隐退到弗农山的先例,我们的宪法可能永远不会获得批准,它创造了一个赋予可怕权力的行政机构。
多亏了这些同样令人敬畏的权力,这份文件现在受到了一位总统的威胁,他的前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拥有一幅自己的肖像,打扮成一位富有魅力的领导人,与华盛顿不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受普通规则约束的上级: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parte)。贝尔认为,尽管--或者可能是因为--1789年事件引入了对法律的崇拜,但在革命的法国,对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的渴望根深蒂固。对于一个骑马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时刻出现呢?尤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马背上塑造了一个可怜的形象,委托画家雅克-路易斯·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描绘他骑着一匹白马英勇地穿越阿尔卑斯山-而不是他真正骑着的骡子。拿破仑既是一位杰出的宣传者,也是一名战略家,他在忙于重塑法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同时,也重塑了自己。用他的死对头杰曼·德·斯塔尔(Germaine de Staël)的话说,拿破仑打破了保罗和华盛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崇拜者--塑造的富有魅力的模式的局限,“垄断了所有名人只为他自己,并阻止了所有其他现存的人能够获得任何名人。”
虽然卢维特和玻利瓦尔的魅力规则也借鉴了华盛顿模式,但他们不断深化的威权性格使他们更接近拿破仑模式。但是,无论这些人倾向于民主还是独裁,他们都反映了一个基于名人和魅力的政治现实,这是在革命时代形成的-这一现实仍然束缚着我们。就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我们面临着一个令人不安但又不可避免的悖论:民主政治不能有魅力,但也不能没有魅力。尽管进步和自由运动理所当然地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拥有的魅力拒之门外,但贝尔警告称,我们不能放弃这种权力,而必须利用它。尽管他开出的药方--即我们必须谨慎选择有魅力的领导人--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令人放心,但贝尔对我们困境的描述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