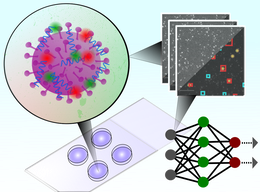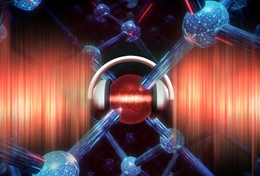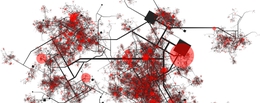一位科学家对机会的残酷估计
在去年8月底一个铅中毒的下午,也就是大流行席卷这个国家的六个月前,我发现自己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重症监护病房里,通过呼吸机呼吸。我完全清醒,失血过多,不能冒险镇静。我记得我抓住了吗啡点滴上的按钮。当护士给我换了床位时,我的脖子扭到了一边,口水开始往喉咙里流。我用食指在丈夫的手上一遍又一遍地拼写“C-H-O-K-I-N-G”,直到护士拿着一个吸球回来。在那个恐怖的夜晚,一直到第二天,这台机器把我的呼吸吸进吸出。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英年早逝,它会在我们世界的某个空虚的地方。我想我会被狂风卷走,在沙漠中迷路,或者离火山太近了。作为一名行星科学教授,我的职业生涯是在遥远的地方做田野工作,试图了解地球上的生命是如何生存的,并最终了解它是否可能存在于火星上。我已经从澳大利亚内陆盐壳沉积物中提取了分子化石,并对阿塔卡马的红沙进行了测序。我乘坐直升机来到南极干燥山谷中古老湖泊的海岸线,在玄武岩熔岩管的黑暗中艰难地爬行。在这些极端的环境中,有一些已知的风险,我总是意识到,如果我不小心,我可能会突然遇到我自己的一些致命的极限。但我从未想过我的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星期一的早晨,一场医疗事故。
如果时间可以解开,我会回到开始,或者回到我认为是开始的地方。春天在我们华盛顿特区的公寓里,到处都是鲜花,一种轻松的温暖,预示着真正的炎热即将到来。我做了验孕,看到最模糊的粉色线条出现,我惊叹不已。我那时39岁。这将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
夏天已经过去几周了,我顺道去我的产科医生办公室做了一些快速的产前验血。我一个人去了,没想到要做超声波检查,但办公室的一台即将更换的机器闲置在门外,所以她把它推了进来。当她用魔杖抚摸我的肚子时,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了,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另一个身影。“双胞胎!”她喊道,小房间里充满了双重心跳的声音。我已经做了两次这样的超声波检查--一次是在8周,另一次是在10周--而且没有人注意到第二个孩子。当我打电话告诉我丈夫这个消息时,他不得不回避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大笑起来。
那天下午更详细的成像显示,这两个婴儿是一模一样的,这让我们年幼的儿子和女儿非常高兴。两条生命,都来自同一个模板。机会有多大?这似乎是创造之谜的一个转折--出乎意料,完全令人着迷,就像在冰封的湖泊或地球表面下一英里处发现生命一样。当我想到所有随意存在的奇迹,以及这一奇迹是如何发生在我身上时,我忍不住笑了。
我拒绝了在莫纳罗亚的一个研究机会,我的丈夫开始来实验室帮我抬起沉重的液氮杜瓦尔。在我进入第二个三个月后,我开始在网上选购小型配套服装。我沉浸在对所有发明的巧妙装置的评论中:Twingaroo婴儿搬运器,Twin Z哺乳枕头,双子城摇篮。随着夏天的进行,怀孕从感觉特别,几乎无法解释,变成了令人放心的平凡。在某些方面,这感觉就像是在地球边缘安顿下来进行一次探险。过了一段时间,每一次宏大的冒险都开始感觉正常,只是一生工作的一部分。
像大多数怀孕双胞胎的妇女一样,我被安排进行频繁的检查。一天早上,就在秋季学期开始之前,婴儿们像往常一样出现了-挥手跳舞。但是后来超声波技师检测到胎盘中有一些异常的血液流动。有点担心,我们的产科医生把我和我的丈夫送到另一家医生的办公室进行后续会诊。我们仅仅两小时后就到了,但是,当下一次超声波聚焦时,我们的一个婴儿正死气沉沉地漂浮着,就像一个掉进游泳池的孩子一样。
接下来的几秒钟延伸到几分钟,延伸到几个小时,都是麻木的太妃糖。一队医生迅速动员起来,如果我们要抢救另一个孩子,我们需要输胎血。经过几个小时的焦急等待,它终于来了-一大品脱,而我们只需要几毫升-一位医生把一根细长的针扎进了我的子宫。她一边做实时测试,一边鼓舞人心地点了点头: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在手术的最后,脐带血管莫名其妙地开始凝结。房间里变得安静了。如果血液流动被扼杀,我们的宝宝就会窒息。因为会议纪要
回到家里,在二十四个不眠之夜之后,我试着休息。我想到了那个已经死了的婴儿,我会一直带着他到怀孕结束,他会被制成木乃伊,变成一个纸质的胎儿。悲痛中不时夹杂着安慰,或者我试图安慰: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我们仍然有一个孩子,而那个婴儿是我们失去的那个的复制品。有点,但当然不是。
仅仅两天后,我的肚子就开始收紧了。我们赶回了医院。又一次超声波,我们的焦虑既是痛苦的新的,又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使劲听着一颗未出生的心脏的声音,在医生们的脸上搜寻他们即将破碎的消息。他们关掉了显示器。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最后,我站了起来,带着两具没有生命的身体。
当取出胎儿的手术被安排好的时候,我期待着它的到来。这至少会让我快速地度过一些痛苦,结束我一直生活的虚幻生活。我睡着了,醒来,一切就都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坏故事的最后一章变成了另一个坏故事的第一章。我对那次事故没有记忆:一条看不见的动脉,无意中被刺破了。当麻醉剂在恢复室逐渐消失时,我记得的是越来越多的嘟嘟声,一种人们聚集在我周围的感觉。我告诉自己要深呼吸。当他们急忙把我送回手术室时,两升血已经从被刺穿的血管中流出,积聚在我的腹腔里。
我在重症监护病房呆了几天。即使在我被从呼吸机上移走后,我还是被管子刺穿了,我自己、朋友和家人都认不出来了。我最终被转移到医院病房,然后出院。但在我回到家的第二天,我被静脉注射部位迅速蔓延的感染所征服。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往返于家和急诊室之间。感染性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形成。扫描我的脑出血,扫描我的肺里有没有血块。那时我们的公寓里挤满了人: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妹妹。每次我们去急诊室,我四岁的女儿都会抓住我的腿抽泣。我的儿子刚满七岁,茫然地凝视着前方,有时会把牙齿塞进胳膊里。似乎我越努力恢复,并发症就越多,一股激流我无法逃脱。
当时间到了,当我终于好起来的时候,我并不是真的。我的身体仍然布满伤疤-麻木的皮肤绳索,两侧是钉书钉的小孔。有些晚上,我根本睡不着,当我睡着的时候,我做了令人不安的梦,在梦里我想尽一切办法窒息:我的舌头在嘴里肿胀,一场海啸压在了我身上。我会在临死前醒来,我的胸部就像一个被吓到的鸟笼。
我一直认为生活是坚韧不拔的表现。我研究的有机体可以在最难以想象的条件下生存--可以茁壮成长。它们可以承受惊人的压力,沸腾的温度和冰冷的温度。他们可以用光秃秃的岩石建造一个家。我推断,如果火星上曾经有过生命,那么它的痕迹很可能还在那里,因为我们对生命能忍受的东西了解得越多,它似乎就越不可能从一个星球上完全灭绝。即使是我年幼的孩子,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抑制的印象,他们强壮而充满活力。但现在,在我手术后的几天和几周里,他们似乎决心对危险进行分类:他们需要知道最近的火山在哪里,最近的小行星在哪里。我试图向他们保证一切都很好,世界不是茶杯。我向他们保证,前方会有快乐的时光。
十月底的一个早晨,我们把婴儿们埋在一个安静的峡谷里。做这些安排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跳过了医院停尸房的电话,然后是殡仪馆的电话,直到最后我们决定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用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送来的鲜花剪报覆盖了坟墓。看来我们终于到了损失的最低点。
第二天,我父亲晕倒在浴室地板上。当他失去知觉时,血从他的鼻子溅到了乙烯基瓷砖上-我们会了解到,这是肺栓塞的结果。我们急忙把孩子们送上车,打破了高速公路的限速,赶到了他被送往的西弗吉尼亚医院。第二天晚上,我代替母亲坐在父亲床边的充气床垫上。我试着入睡,战胜了一次恐慌症发作。我回到了医院的病房,荧光灯,护士冲进大厅的匿名警报。
几天后,我父亲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转移性癌症。医生说他可能得了不到六个月的病。他们可以减慢它的速度,但不能治愈它。在他离家出走的两个月里,他帮助照顾我和我的家人,父亲一直避免抱怨他的疼痛;他认为这只是因为睡在不舒服的沙发上。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微小的实体-一个甚至不是真正活着的实体-正在寻找进入人体的途径。直径只有125纳米,比光的波长还小,它悄悄进入宿主的核糖体并开始复制。随着冠状病毒开始在武汉悄悄传播,从丈夫传给妻子,传给孩子,传给老师,再传给旅行者,我父亲开始接受癌症治疗,以减轻他的痛苦。在与他的新医生会面的间隙,我会见了我自己的一批专家。哥伦比亚特区最早的-19病例是在3月初记录的。看我的血液学家、心脏病专家、初级保健医生和创伤治疗师,以及我父亲的肿瘤学家,都转到了屏幕上。
在我厨房进行的一次Zoom预约中,我得知了一系列基因测试的结果:我遗传了一种凝血障碍。它是由一个点突变引起的。在组成我的染色体的30亿对核苷酸中,有一个错误。但这个小小的错误造成了一个大得多的问题,将蛋白质扭曲成错误的形状,在我的血液化学中引发了一系列其他变化,并导致了亲血栓症,即形成血栓的倾向。这种凝块可能会积聚在胎盘内,或者会阻塞癌症患者肺部的血液流动。
我很难接受这个消息,不是因为前景很糟糕--这种情况很容易治疗--而是因为它让最近的不幸连锁反应看起来是如此可以避免。我情不自禁地想着那些假设,那些本可以带来不同的、更快乐的结局的许多小动作。要是在它所属的地方有一个小鸟嘌呤基地就好了。如果我知道这种突变,并在怀孕期间每天服用一些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就好了。如果我坐的或睡的不一样,或者超声波检查早一天就好了。如果在第一个癌细胞迁移到我父亲的血液之前,我就能看到他的痛苦就好了。同样的想法在大流行的早期是不可抗拒的,今天仍然很诱人:如果我们早点开始检测,或者早点戴上口罩;如果那个一百二十五纳米的病毒被风带走了就好了。
有时,我想到最近发生的事件,无论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只是罕见地偏离了正常的事情方式,是深不可测的坏运气的结果,这让我感到安慰。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想法给了我一种希望的感觉,好像只要我们能避免出差错,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一个注定要发生的积极结果。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命运之轮深深地植根于生命本身--从细胞层面到行星层面。我的双胞胎是在胚泡崩溃时形成的-但后来,没有死亡,反而加倍了。融合在它们微小基因中的DNA是一系列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结果,从数十亿年前一颗恒星的诞生开始。它们的细胞携带着生命起源、多细胞起源、意识起源的回声-大规模灭绝和灭绝大流行的指纹,数千代人适时相遇和配对的指纹。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两个微小的身体,不可重复,充满了无限的潜力。
前几天,我的儿子试探性地蜷缩在我的大腿上,问我因果关系,这是他在隔离期间在网上看的一节课的主题。我告诉他,他学到的想法是我作为一名科学家工作的基础,这些想法提供了我一直在问的基本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他和他妹妹也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迷惑地看着我。我说,因果是解开宇宙的工具。我们学得越多,掌握得越多,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也就越能更好地应对我们的恐惧。“就像日冕一样,”他说。
我解释了我们现在如何阅读生命的每一个字母的基因指令;我们如何通过人体窥探某人为什么生病,他们在哪里流血,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如何瞄准他祖父体内的流氓细胞,而不去理会健康的细胞;我们如何控制病毒的冠冕,并追踪其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我向我的儿子保证,这些都是希望的理由,它们确实是。我们现在正在从幸存者的血浆中提取19种抗体,为那些仍在与这种疾病作斗争的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并部署新的快速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