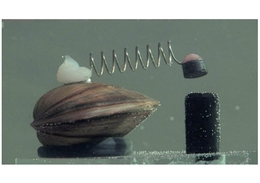1980年塑造了生物技术未来的两个月
在40年前的这周开始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五件事,塑造了生物技术产业和生物科学研究。回顾这些开创性的事件,可以提醒人们发生变化的奇怪方式。
1980年10月14日,星期二清晨,加州斯坦福的保罗·伯格家的电话响了。叮当作响的电话让伯格和他的妻子担心,因为伯格的父亲年迈生病,他们担心最坏的情况。相反,伯格听到了他的斯坦福同事亚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的声音,告诉他保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瑞典皇家学院一直无法找到伯格未登记的电话号码,但康伯格的一个儿子一大早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消息,并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后者也给伯格打了电话。
伯格获得了当年核酸基础研究和“重组DNA的某些方面”奖的一半。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和沃尔特·吉尔伯特(Walter(Wally)Gilbert)分享了另一半,以表彰他们对DNA测序的发现。
斯坦福大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科学家对重组DNA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人质疑为什么伯格是唯一的接受者。这些奖项总是很难颁发,特别是诺贝尔委员会自己设定的任何奖项的获奖者不得超过三人的限制(和平奖除外)。
一旦化学委员会决定承认桑格和吉尔伯特进行测序-每个人都在非常不同的方式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就只剩下一个重组DNA的空位。没有人怀疑伯格和他的实验室对该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推动该领域向前发展的动力。但伯格还有另一个角色,让他从人群中脱颖而出。他是组织暂时暂停重组DNA研究的领导者,也可以说是领导者,并组织和主持了著名的关于重组DNA的Asilomar会议,会上讨论了暂停研究的问题。
大约在伯格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同时,一家成立4年的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的普通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IPO)。基因泰克的业务是以重组DNA为基础的,它的第一批产品(当时还需要两年时间)是由细菌制造的人类蛋白质,人类基因已经使用重组DNA技术插入其中。开盘时,该股交易价格为每股35美元。当天结束时,投资者将其价格推高了-一直高达每股88美元-最后收于71美元。
第一次生物技术热潮开始了,导致许多其他羽翼未丰的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上市。基因泰克令人印象深刻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否要归功于当天早上宣布的伯格重组DNA诺贝尔奖?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整整一周后,也就是10月21日,吉米·卡特总统签署了“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案”(Stevenson 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它回应了人们对政府支持的技术商业化不够频繁的担忧。该法案鼓励美国国家实验室,如费米拉实验室、布鲁克海文、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和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等,传播有关政府拥有的技术的信息,部分方法是要求它们建立研究和技术应用办公室,以确定和推广具有强大商业潜力的技术。卡特政府支持这项法案的部分原因是它保持了对谁将把联邦政府手中的这些新技术商业化的控制权。
这是生物技术五项活动中最不重要的一项。国家实验室虽然为来自核武器研究的组织从事了数量惊人的生物学研究,但在当时并不是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创新的温床。
12月2日星期二,标志着这一系列生物技术事件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安静的,但也不是最不重要的。美国专利商标局向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N·科恩(Stanley N.Cohen)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赫伯特·W·博耶(Herbert W.Boyer)两位发明家授予了美国专利号4,237,224,“生产生物功能分子嵌合体的方法”。这项专利被授予利兰·斯坦福初级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董事会。正如我和同事雅各布·谢尔科(Jacob Sherkow)在2015年所写的那样:
“这项专利是1974年研究创造重组DNA过程的结果,也就是重组基因,这似乎是遗传学家的圣杯。科恩-博耶的技术不是繁琐的突变或杂交研究,而是允许遗传学研究人员孤立地研究和创造基因。随着对限制酶功能和特性的研究不断增加,重组DNA技术为研究人员分离和纯化单个基因以及创造自己的类似基因打开了大门。“。
在授予这项专利的时候,我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重要宣传,但在接下来的20年里,科恩-博耶的专利构成了生物技术行业和许多生物研究的基石。它广泛宣称拥有重组DNA的方法,并为其受让人赚取了约4亿美元。
斯坦福大学管理着科恩-博耶的专利,并为其麻烦收取了15%的收益。其余的由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系统平均分配,这两个系统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它们。斯坦福大学的做法是(现在仍然是)将收益的三分之一捐给发明人,三分之一给发明人所在的部门,三分之一给发明人所在的学校。科恩是斯坦福医学院(Stanford Medical School)遗传学系的成员,这笔约7000万美元的财富并没有引起伯格和科恩伯格的生物化学系的喜爱,这两个系在伯格的实验室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大量的重组DNA研究。另一方面,遗传学系对谁获得(和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并不太满意。
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在被授予专利时充分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或者说是多么有利可图。尽管如此,科恩-博耶的专利最终帮助改变了大学将研究商业化的方式。其丰厚的回报促使最初数十所,然后是数百所学院和大学开设了技术许可办公室。今天,大约有200个这样的办公室存在,尽管每年只有十几个是盈利的(而且这些办公室每年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包括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办公室)。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发生在12月12日星期五,当时的跛脚鸭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签署了专利和商标法修正案法案,也就是更广为人知的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这项法律为大学和其他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提供了一种明确而简单的方式,拥有他们利用联邦研究资金创造的全部或部分知识产权。它经常被认为是启动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功臣。随着科恩-博耶专利的成功,它当然鼓励大学将生物学的某些部分视为潜在的利润中心。
当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和堪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首次向第95届国会提出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Small Business NGO Patent Procedure Act)时,美国经济正受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来自日本的经济挑战的困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时期。
国会当年没有对该法案采取行动,但贝赫和多尔在第96届国会重新提出了该法案。尽管民主党人控制了参众两院,但卡特总统反对这项法案。他希望走一条更多由政府主导的道路,就像史蒂文森-怀德勒法案(Stevenson-Wydler Act)中所采取的那样。强大的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拉塞尔·朗(D-La)从更民粹主义的角度反对该法案。他希望政府从任何专利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在1980年11月的选举之前,该法案没有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
那场选举让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入主白宫,也让民主党失去了12个参议院席位,这将使共和党从1981年1月开始在第97届国会获得参议院多数席位,这是自1954年以来共和党首次获得参议院多数席位。伯奇·贝赫(Birch Bayh)是不会重返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之一,他被未来的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击败。
第96届国会仍由民主党参议院占多数,在11月选举后举行了一次跛脚鸭会议,这是自1940年以来39届国会中的16次此类会议之一。它的紧迫性来自于政府大部分部门缺乏预算权力,但也来自其他一些重要、困难和有争议的立法,这些立法被推迟到选举之后。
他们队伍中对Bayh-Dole的强烈支持阻止了即将成为多数派的参议院共和党人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但要在那次会议上对该法案进行投票,需要参议院的一致同意-这意味着长时间竖起大拇指。他默许了,据说是出于对他即将离任的同事伯奇·贝赫(Birch Bayh)的尊重和友谊。
卡特总统没有暗示他是否会签署该法案。宪法给总统10天(不包括周日)来否决一项法案,签署一项法案,或者在没有他签名的情况下让它成为法律。在可能的最后一天,12月12日,卡特签署了这份协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恩-博耶的专利是在Bayh-Dole法案让大学更容易为受益于联邦资金的发明申请专利之前颁发并分配给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这两个机构都使用了NIH和私人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相关的重组DNA研究,但他们不必等待Bayh-Dole通过就可以为这项发明申请专利。联邦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前身)和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之间存在一项预先存在的专利协议,允许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在Bayh-Dole生效之前为该技术申请专利。
因此,在不到两个月的两天里,新兴的生物技术产业和大学生物技术研究被推向未来,获得了一项诺贝尔奖,一次令人惊叹的生物技术首次公开募股(IPO),两项研究商业化法案,以及一项基础专利。当时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集体重要性。没错,当时还发生了其他事情。在最初的三周里,当时似乎处于美国政治保守派极端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挑战了温和保守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并在11月4日击败了仅任职一届的卡特。在此期间,美国驻伊朗德黑兰大使馆的53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被囚禁,这是他们在11月初被拘留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年。经济仍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及其引发的高通胀中摇摇欲坠(即将陷入急剧衰退)。
在这一切之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生物技术新时代的基石走到了一起。
历史往往也是如此。一些关键事件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些事件则悄悄接近我们。无论是明目张胆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在所有这些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继续着我们的日常工作、爱情和生活,只是很少回顾和注意到我们生活的时代-有时才过了40年。
亨利·T·格里利(Henry T.Greely,J.D.)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法学教授和遗传学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担任斯坦福法律和生物科学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Law And Biosciences)主任,并担任斯坦福生物医学伦理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他感谢雅各布·谢尔考(Jacob Sherkow)和罗伯特·库克-迪根(Robert Cook-Deegan)对这篇文章的有益评论,以及他的研究助理布列塔尼·卡扎科夫(Brittany Cazakoff)和卡西迪·安伯·波莫罗伊-卡特(Cassi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