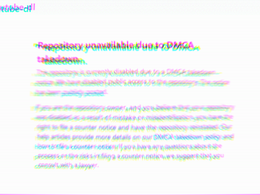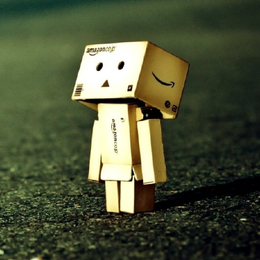不再有大胆的未来愿景
我希望未来是什么样子?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希望看到哪些令人惊叹的发明,并帮助建立这些发明呢?今天早上我意识到我不知道。我当时很震惊。
我从小就在修补技术,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一直在投资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六十多个关于未来的赌注。我应该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大胆的愿景,我支持的论文,以及我以技术乐观的方式配置的资本。我开始投资初创公司,因为我想帮助塑造未来。虽然我仍然为与有大胆想法的创始人交谈而感到兴奋,但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宇宙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未来主义饮食中长大,我有很多伟大的想法:太空飞行、超音速旅行、磁悬浮列车、测地圆顶、长寿生物纳米技术,以及为所有人提供最大自由的社会组织。俗气,但很乐观。
现在我29岁了,我没有什么大的、乐观的想法。我认为大量的套利和效率的提高。虽然我相信更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带来更多的建设和创新,但缩小模糊的价格差距并不像梦想在人类经验和可能性的前沿进行伟大的冒险和探索。
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大众媒体的激励错配正在导致两极分化加速,如何补救气候变化的影响,等等。但这些都是修正和反应。感觉就像在船的肚子里,疯狂地堵住漏水的洞,甚至连想船应该去哪里的心思都没有。表面上看,这些决定是在船上的驾驶台上做出的,到2020年10月,驾驶台上似乎挤满了善意的个人,但他们做出良好集体决策的能力受到了阻碍。
最近几年的情况告诉我,要做出任何有意义的公共决策是多么困难。每一场辩论都是无休止的争论,每一个话题都有意义的细微差别,每一个决定都有非常难以预测的二级效应。现在的世界比20年前要复杂得多,其影响令人瘫痪。政策制定者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我甚至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我明白,在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里,几乎所有的工具都可以被使用-而且更多时候,将被使用-无论是好是坏,以及在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世界里,多年的结果是多么难以预测。我了解到,技术很少能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我已经无数次地看到公众对“这项技术/人/政策是好的”到“这是坏的”的看法过山车。
这让我陷入了真正的困境,因为我的观点很有说服力,而不是微观上的关注。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努力发展对比特币的长期看法。根据网络效应,我认为很明显,从长远来看,我们将要么拥有法定的,要么拥有加密的-要么完全集中,要么完全分散-而不是两者兼而有之。我想生活在哪个世界?我没有把握。一方面,很明显,我们现有的美国金融体系是脆弱的,存在系统性风险,这是一个暴露于潜在不负责任治理的花花公子。你可能会说它的机制对大众不公平,但你也需要指出,在过去的110年里,它实际上在创造繁荣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它运行得非常好!)。我同意有必要彻底改革这一体系,但我不确定是否明智,扔掉整个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打开世界上最大的权力真空。这很少有好的结局。老实说,我不知道哪条路是最好的。我怀疑没有人会这样做。
其他大问题和大变化的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困境。也许结果是,我发现自己不再有远大的梦想。我的梦想很小,在那里效果是可以预测的。关于远大梦想,有责任和效果的瘫痪,但多年来也有一定程度的愤世嫉俗,因为随着远大梦想变成现实,它们变得更加令人担忧和复杂。当我看着技术时,实现重大变革的细微差别、复杂性、难度、责任感,以及往往不可逆转的因素,已经慢慢地从我的眼睛里移走了星星。也许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变化的严重性。
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不下大的、大胆的赌注,我们将永远被困在局部最优的山谷中。正如贝佐斯所说,你的冒险规模应该随着你企业的规模而增加-在规模上,我们应该一直在进行许多大胆的赌博。但感觉这并不是真的发生。感觉就像我们花了很多精力辩论边缘的细微差别,坐在船的腹部进行维护,而不是绘制前进的路线。
2020年很难成为乐观主义者。我钦佩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他们仍然有勇气实现远大的梦想,并提醒自己,未来可能是令人惊叹的,值得为之奋斗。
这篇文章的灵感尤其来自布莱克·肖尔和Boom将我们带回超音速飞行时代的坚定不移的努力,以及创始人基金在他们年度会议上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