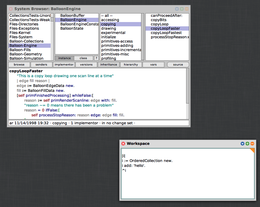瘟疫后的艺术:历代画家如何应对传染病
在14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候,比萨的多米尼加修道士委托为哥特式门廊创作了一系列壁画,这些壁画围绕着该市的公墓坎波圣地(Campo Santo),或称圣地,这是一个与邻近的大教堂及其著名的倾斜钟楼一样引人注目的地标。一个简单的墓地已经不再适合富裕的商人社区的品味,这个社区是中世纪晚期世界上最复杂的城市之一。除了关于早期基督教隐士、“最后的审判”和地狱恐怖的传说外,墓地的新壁画还包括一幅令人痛心的“死亡的胜利”。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是谁绘制了这幅非凡的景象-布法尔马科·布法尔马科还是弗朗西斯科·特雷尼,他们两人都在现场工作。也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被处决的-1336年或1348年1月之后的某个时候,当这个繁忙的港口成为欧洲致命的黑死病大流行的首批到达点之一。
瘟疫仍然伴随着我们,而且可能从新石器时代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这种疾病14世纪的昵称来自坏疽肉的颜色,这种症状是当跳蚤携带的鼠疫耶尔森氏菌进入人体血液导致小凝块爆炸时发生的,这些小凝块通常集中在鼻子、手和脚等四肢上。凝结导致致命的坏死,今天可以用抗生素治愈。瘟疫的其他受害者遭受了巨大肿大、脓肿的淋巴腺(称为Buboes)的痛苦,特别是在腹股沟和腋窝,这使鼠疫耶尔森菌成为其最著名的名字,腺鼠疫。更致命的是肺炎形式的鼠疫,当细菌进入肺部时,这种疾病就会发展;然后,受害者可以通过呼吸飞沫或肺部衰竭时咳嗽出来的血液传播传染病。
比萨在黑死病中失去了70%的人口。(在附近的佛罗伦萨,居民人数从1347年的11万人下降到1351年的5万人。)。圣坎波大教堂(Campo Santo)壁画的最新修复者倾向于将死亡的胜利日期定在1336年左右,依据的是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将阴郁的人物与多米尼加修士的同时代手稿照明和布道进行了比较,并找到了对比萨当时政治形势的典故。总而言之,证据是细腻和主观的。在这幅壁画中描绘的死亡破坏的规模在13世纪30年代的欧洲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在13世纪30年代末和13世纪40年代初,该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饥荒,但饥荒区分了富人和穷人,而圣坎波人的胜利死亡则没有明确的区分。顺便说一句,1944年盟军的炸弹袭击了墓地,几乎摧毁了壁画,烧毁了纪念碑修道院的木制屋顶和将壁画灰泥固定在建筑大理石墙上的被敲打的芦苇。他们的风格,剩下的东西,只能透过一面黑暗的玻璃才能看到。
尽管比萨凯旋号的最新修复者有着非凡的技能,死亡仍然是一个朦胧的幽灵。拉丁词MORS和意大利语MOTE都是女性名词,因此比萨的“严峻的收割者”几乎看不见,因为她是一个憔悴的、凹陷的眼睛,长长的白发在身后拖着长长的白发,穿着麻布,带着警棍般的翅膀飞行。她的整个世界看起来就像古代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苍白的死亡”,贺拉斯和她一样,“不偏不倚地敲响穷人的小屋和富人的塔楼”。死亡也许是憔悴苍白的,但她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安布罗吉奥·洛伦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从附近的锡耶纳创作的壁画“坏政府的寓言”(Allegory Of Bad Government)中,死亡以数十种不同的形式在乡村徘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于过多的暴力原因。这幅壁画肯定是在1336年至1339年的瘟疫之前绘制的。但在比萨,死亡驾驶着一辆联合收割机降临,用最新的14世纪农业技术跟踪她的人类作物:一把巨大的、闪闪发光的镰刀。在发明这种巧妙的省工器之前,收割机用镰刀一把一把地收割谷物,但这把镰刀,其弯曲的剑状刀片(中国)固定在长轴(斯奈斯)的末端,允许农民用一种全新的计量单位割谷物:条带。然而,圣坎波河墙上的死亡形象并不是普通的镰刀;她的收割机巨大的三角形刀片,比弯刀更锋利,是用来切割人群的,而不是琥珀色的谷浪。
她下面已经躺着一堆身体,不分青红皂白地混杂着国王、修女、主教和女士,还有一个穿着毛皮衣服的商人和一个穿着奢华格子的男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用垂死的呼吸驱逐自己的灵魂,赤身裸体的婴儿从他们的嘴里冒出来,天使和恶魔徘徊在那里,等待着将新生的灵魂带上天堂或地狱。严酷的收割者飞过大屠杀的上空,全神贯注地准备好她的镰刀,同时将目光投向下一组受害者:一群贵族聚集在一起。
我观看,不料,有一匹苍白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神,地狱跟随着他。又有权柄赐给他们管理地的第四部,可以用刀杀、饿杀、死杀、并地上的走兽杀戮。启示录6:8)。
这匹苍白的马正在迅速变成骨架,它是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痛苦的马的模型,至少根据西班牙人的朋友、西西里画家雷纳托·古图索(Renato Guttuso)的说法。死亡也是如此,当他在人群中疾驰而过时,他的皮肤一条又一条地脱落,有些人活着,有些人快死了,有些人很早就得到了帮助。他挥舞着一把优雅的弓,这是古代神阿波罗最喜欢的武器,阿波罗的箭如雨点般落在希腊人、罗马人和伊特鲁里亚人身上。阿波罗的名字的意思是“破坏者”,他的一个称谓是“远飞镖”,但奇怪的是,他也是一个治愈的精灵,这幅挂在医院墙上的死亡形象可能带有一些古代神的模棱两可:对于在这幅阴郁的壁画下受苦的基督教患者来说,死亡也是通向拯救的大门。由于阿波罗对意大利想象力的持续控制,15世纪的观众可能会将死亡之弓与流行病联系在一起,而箭在流行的瘟疫圣徒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的殉难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塞巴斯蒂安是一名年轻的罗马士兵,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被绑在树上,被弓箭手射杀。
就像比萨的“死亡的胜利”一样,这幅西西里壁画特别针对精致、老练的公众。许多死亡受害者都穿着漂亮的锦缎。当苍白的马和他的骑手横扫风景时,戴着奢华帽子的珠光宝气的女士们随着竖琴和琵琶的音乐在大理石喷泉附近跳舞,她们的指尖几乎没有接触到彼此。一位少女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她的视线,一个穿着缎面紧身衣的金发天鹅在她面前跪了下来,一支意想不到的箭卡在了他的喉咙里。一只光滑的白色猎犬在它甜美的脸庞(褪色得很厉害,几乎看不见)嗅着空气时焦躁地嘎嘎作响,与其说是不安,不如说是好奇。动物们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但它们又回到了怪异骑士已经袭击的地方。死亡对他们的感官来说太快了。
1629年,瘟疫以特别致命的方式回到意大利北部,在那里肆虐到1631年,这一年还见证了其他几场灾难,如休眠几个世纪后那不勒斯的维苏威火山喷发,以及瑞典,特别是瑞典大炮,卷入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致命冲突,这场冲突最终被称为三十年战争。在罗马,法国画家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试图通过他的艺术来理解这种暴力和苦难。他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又是一位了不起的画家,他从希伯来语圣经(撒母耳前书5:6)中选择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在这段插曲中,非利士人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偷走了约柜:
他们搬来搬去,耶和华的手就极大地攻击那城,击杀城中的人,无论大小,暗处都长了瘤子。
伏尔盖特版本的文本,Poussin知道的版本,补充道:“老鼠出现在他们的土地上,整个城市都在死亡和毁灭。”
对于普桑来说,非利士人表现出了腺鼠疫的症状(和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1631年阴郁的一年选择了这段话。在他的“阿什杜德瘟疫”(Poussion Of Ashdod)(被蹂躏的非利士人据点的建筑和服装与这位艺术家最熟悉的古罗马的建筑和服装相似)中,普桑在古典建筑的庄严宁静和疾病带来的人类混乱之间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但更根本的是人类的罪恶,至少根据圣经的说法,正是这种罪恶首先导致了疾病的爆发。就像巴勒莫“死亡的胜利”的画家一样,他使用了一系列聪明的视觉线索来吸引其他感官。关于这场瘟疫的大多数书面报道都强调了受害者的器官和身体腐烂时有多么难闻,但普桑这位最优雅的画家是少数几个如此专门关注瘟疫恶臭的人之一,他优雅的人物避开了他们的头,或者用手捂住了他们的鼻子。他以同样敏锐的眼光详细描述了人类关系是如何破裂的。在这幅画的正中央,一位有两个婴儿的哺乳母亲和她的一个孩子刚刚倒地身亡。另一个婴儿还活着,仍在努力哺乳,但无法从他死去的母亲的乳房中吸奶。一个年轻人,可能是他的父亲,用手捂住他的脸,捏住他的鼻子,忍住眼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弯下腰把孩子抬到安全的地方。在他脚下伸展的软弱无力的、灰白的身体可能在片刻前还是他心爱的家人的心脏,但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只不过是身体,是致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