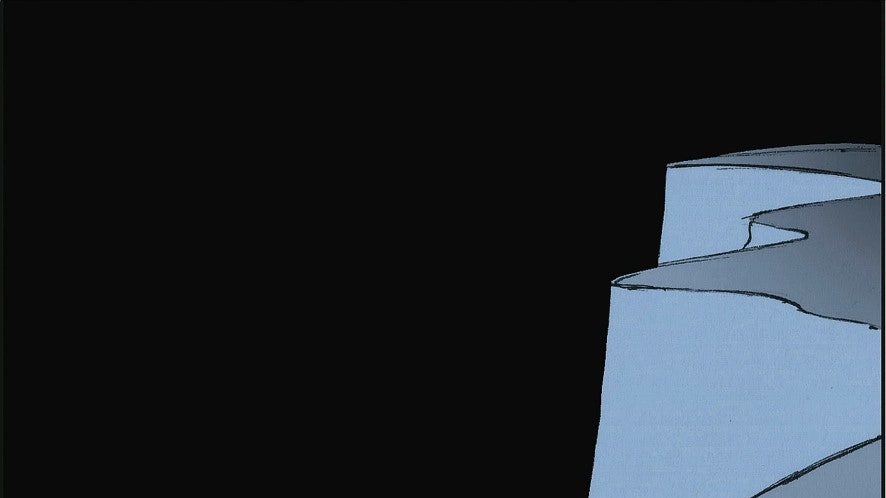水族馆:一个孩子的隔离病(2011)
2010年7月15日,我的妻子Teri和我带着小女儿Isabel到医生那里进行了定期检查。她只有9个月大,似乎身体健康。她的第一颗牙齿进来了,现在她经常在餐桌上和我们一起吃饭,胡说八道,然后将米糊铲进嘴里。她是一个开朗,快乐的孩子,对人有好感,开玩笑说,她不是从她先天脾气暴躁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我和Teri总是一起去看望孩子的医生,这次我们还接了伊莎贝尔的大姐姐Ella,她快三岁了。 Armand Gonzalzles博士办公室的护士对Isabel的体温进行了测量,并测量了她的体重,身高和头围,而Ella很高兴自己不必经历同样的磨难。正如我们所说的,G。博士聆听了Isabel的呼吸,检查了她的眼睛和耳朵。在电脑上,他绘制了伊莎贝尔的发展图表:她的身高在预期范围内;她体重不足。一切似乎都很好,除了她的头围,这是她上次测量值的两个标准偏差测量值。 G博士很担心。由于不愿送伊莎贝尔进行MRI检查,他安排第二天进行超声检查。
那天晚上回到家,伊莎贝尔很焦躁不安。她很难入睡。如果我们不去G.博士,我们会以为她简直太累了,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一个基于恐惧的框架。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把伊莎贝尔带出我们的卧室(她一直和我们一起睡)使她平静。在厨房里,我演唱了她摇篮曲的全部曲目:“ You Are My Sunshine”,“ 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和我小时候学到的莫扎特作品,我奇迹般地想起了他在波斯尼亚语中的歌词。通常不停地唱歌三个摇篮曲是可行的,但是这次花了一段时间才让她把头放在我的胸口上并安静了下来。当她这样做时,感觉好像她在某种程度上安慰我,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当时很担心,我想象着一个未来,有一天我会回忆起那一刻,并告诉其他人伊莎贝尔如何使我平静下来。我的女儿,我会说,照顾我,她只有九个月大。
第二天早上,伊莎贝尔对她的头部进行了超声波检查,整个过程中泰瑞都在怀里哭泣。我们回到家后不久,G。博士打电话告诉我们,伊莎贝尔患有脑积水,我们需要立即去急诊室,这危及生命。
伊莎贝尔(Isabel)即将进行CT扫描,而医生希望她入睡,这样他们就不必为她服药,因此芝加哥儿童纪念医院E.R.的检查室处于黑暗状态。但是她不允许进食,因为有可能进行随后的MRI检查,并且她一直因饥饿而哭泣。一位居民给了她五颜六色的陀螺,我们吹起它来分散她的注意力。她终于睡着了。在执行扫描时,我们等待一些东西能够显示出来,太害怕了无法想象它可能是什么。
儿科神经外科负责人Tadanori Tomita博士为我们阅读了CT扫描:伊莎贝尔大脑的脑室扩大,充满了液体。富田博士说,有一些东西在堵塞排水通道,这可能是“增长”。迫切需要MRI。
麻醉药施行后,Teri将伊莎贝尔抱在怀里,然后我们将她交给护士进行了一个小时的MRI检查。医院地下室的自助餐厅是世界上最可悲的地方,霓虹灯闪烁,灰色桌面凸显,那些远离患病的孩子准备烤芝士三明治的人们的不祥预感。我们不敢猜测MRI的结果;我们固守在那一刻,尽管那是可怕的,但还没有延伸到未来。
被召集进行医学影像检查时,我们在一个过道的走廊遇到了富田博士。他说:“我们相信,伊莎贝尔患有肿瘤。”他向我们展示了他计算机上的MRI图像:位于小脑,脑干和下丘脑之间的伊莎贝尔大脑中心正好是一个圆形的东西。富田博士建议,这只是一个高尔夫球的大小,但我对高尔夫球从来没有兴趣,也无法想象他的意思。他将切除肿瘤,只有在病理报告后我们才能发现肿瘤的类型。他说:“但是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四面体。”我也没有理解“ teratoid”这个词,这超出了我的经验,属于Tomita博士现在指导我们的领域,这是难以想象和难以理解的领域。
伊莎贝尔在恢复室里睡着了,一动不动,天真无邪。泰瑞和我亲了亲她的手和额头,在那段将生命分成前后的瞬间哭泣。在此之前,永远被取消抵押,而在之后,则像一颗闪烁的星星一样散开,进入一个黑暗的痛苦世界。
我仍然不确定Tomita博士所说的话,我在互联网上查询了脑部肿瘤,并发现了一张与伊莎贝尔几乎相同的肿瘤图像。我读到它的全名是“非典型的类畸胎/类胡萝卜瘤”(A.T.R.T.)。它是高度恶性的,极为罕见,仅发生于百万分之三的儿童中,占中枢神经系统小儿癌症的约3%。三岁以下儿童的生存率不到百分之十。还有更多令人沮丧的统计数据可供我考虑,但我从屏幕上退缩了,决定只与伊莎贝尔的医生交谈并信任他们。我再也不会在互联网上研究她的病情了。我已经理解,如果我们不失去理智,就必须管理我们的知识和想象力。
7月17日(星期六),富田博士和他的神经外科小组在伊莎贝尔的头部植入了一个Ommaya水库,以帮助排出并减轻积聚的脑脊液压力。当伊莎贝尔回到她在神经外科手术室的病房时,她以不愿做的事揭开了毯子。我们将此视为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这是漫长旅程中充满希望的第一步。星期一,她从医院被释放出来,等待在家中进行切除肿瘤的手术,该手术计划于本周末结束。 Teri的父母在城里,因为她的姐姐在伊莎贝尔(Isabel)体检的那天就生了她的第二个儿子-太担心伊莎贝尔(Isabel),我们几乎没有注意这个家庭的新来者-埃拉(Ella)与她的祖父母度过了一个周末,几乎没有注意到动荡或我们的缺席。周二下午天晴,我们所有人出去散步,伊莎贝尔绑在Teri的胸前。那天晚上,我们赶到急诊室,因为伊莎贝尔发烧了。她很可能受到了感染,这在孩子的头部插入异物(在这种情况下是Ommaya)后并不少见。
她接受了抗生素并接受了一两次扫描。 Ommaya被删除了。在星期三的下午,我离开医院回到了Ella,因为我们答应带她去附近的农贸市场。在持续的灾难中,我们必须信守承诺。我和艾拉(Ella)买了蓝莓和桃子。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从我们最喜欢的糕点店里买了一些一流的煎饼卷。我与艾拉(Ella)谈了伊莎贝尔(Isabel)的病情,她的肿瘤,并告诉她那晚必须和奶奶在一起。她没有抱怨或哭泣;她和任何三岁的孩子一样,都知道我们的困境。
Teri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手里拿着奶油卷饼回到医院。伊莎贝尔的肿瘤正在出血;需要紧急手术。 Tomita博士在进入手术室之前正在等待与我交谈。我花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间才到达医院,这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进行的,那里的人们在过马路时并不着急,没有婴儿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切都从容地转身远离了灾难。
在医院的病房里,手里还拿着一盒煎饼卷,我发现Teri在苍白的Isabel上哭泣。富田大夫在那里,我们女儿的出血图像已经在屏幕上拉开了。似乎,一旦排出液体,肿瘤就会扩张到空的空间,其血管开始破裂。立即清除肿瘤是唯一的希望,但伊莎贝尔有明显的出血致死危险。富田博士告诉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体内的血液刚刚超过一品脱,持续输血可能不够。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伊莎贝尔进行了两次脑切除术(其中将她的大脑半球分开,以使富田博士能够进入茎,松果体和小脑之间的区域并挖出肿瘤)以及另外六次手术解决排液失败的问题。一个管子已经插入她的胸部,以便可以将化疗药物直接注入她的血液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在她的额叶中发现了一个无法手术的花生大小的肿瘤,并且病理报告证实该癌症确实是A.T.R.T. Chemo计划于诊断后一个月8月17日开始,Isabel的肿瘤学家Jason Fangusaro博士和Rishi Lulla博士不愿讨论其预后。我们不敢按他们。
我和Teri在医院诊断后的头几周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我们试图与艾拉(Ella)在一起,尽管她可以在神经外科病房探望伊莎贝尔(Isabel)并总是让她微笑,但艾拉(Ella)并没有被允许进入I.C.U.。 Ella似乎处境很好。支持者的家人和朋友走过我们家,帮助我们分散了她对我们不断缺席的注意力。当我们与艾拉(Ella)谈论伊莎贝尔(Isabel)的病时,她听着,睁大了眼睛,感到担忧和困惑。
在苦难的头几周,埃拉开始谈论她的假想兄弟。突然,在她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哥哥的故事,这个哥哥有时一岁,有时在高中,由于某种晦涩的原因,偶尔旅行到西雅图或加利福尼亚,然后回到芝加哥去。在埃拉(Ella)的另一本冒险独白中出现。
当然,埃拉(Ella)岁的孩子拥有虚构的朋友或兄弟姐妹并不罕见。我相信,虚构人物的创造与两到四岁之间语言能力的爆炸式增长有关,并迅速创造出过多的语言,孩子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来适应这种语言。为了尝试一下她突然拥有的单词,她必须构造虚构的叙述。例如,埃拉(Ella)现在知道“加利福尼亚”一词,但她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经验。她也无法从抽象的角度(加利福尼亚的风格)对其进行概念化。因此,她的想象中的兄弟必须被部署到阳光充足的州,这使艾拉(Ella)可以像她了解加利福尼亚一样长时间地交谈。这些话要求这个故事。
同时,这个年龄段的语言激增在外在性和内在性之间产生了区别:孩子的内在性现在可以表达,因此可以外在化;世界翻了一番。埃拉现在可以谈论这里和其他地方。语言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是连续不断的。有一次,在晚餐时,我问埃拉当时她哥哥在做什么。他在她房间里,她说的是事实,发脾气。
起初,她的兄弟没有名字。当被问到他叫什么名字时,埃拉回答说:“ Googoo Gaga”,这是她五岁的表哥马尔科姆在他不知道该词时发出的荒谬的声音。由于查理·明格斯(Charlie Mingus)实际上是我们家中的神灵,我们向埃拉(Ella)建议使用明格斯(Mingus)这个名字,而她的兄弟明格斯(Mingus)成了。此后不久,马尔科姆(Malcolm)给了埃拉(Ella)一个外星人的充气娃娃,她随后选择将那玩偶体现为滑溜的明格斯(Mingus)。尽管艾拉(Ella)经常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玩,但并不总是需要外星人的身临其境才能向明格斯(Mingus)发出假父母命令或讲述自己的出逃故事。当我们的世界被缩小到无休止的恐惧的幽闭恐惧症的大小时,埃拉的行为却在扩大。
非典型类畸形横纹肌瘤如此罕见,以至于很少有专门为其设计的化疗方案。许多可用的协议都源自髓母细胞瘤和其他脑部肿瘤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经过修改后具有更高的毒性,可以抵抗A.T.R.T.的恶性恶性肿瘤。其中一些协议涉及集中放射治疗,但这将不利于伊莎贝尔这样一个孩子的成长。伊莎贝尔的肿瘤科医生决定采用的方案包括六个周期的极高毒性化学疗法,最后一个是最强烈的。事实上,如此之多,以至于早些时候提取的伊莎贝尔自己的未成熟血细胞必须在那个周期之后重新注入,这就是所谓的干细胞恢复过程,以帮助她的耗竭的骨髓恢复。
在整个化学过程中,她还必须接受血小板和红细胞的输血,而她的白细胞计数每次都需要自行达到正常水平。 她的免疫系统将被暂时摧毁,一旦恢复,另一个化学循环就会开始。 由于进行了广泛的脑外科手术,因此伊莎贝尔(Isabel)不能再坐或站,而必须在两次化学治疗之间接受职业和物理治疗。 有人建议,在不确定的未来中的某个时候,她也许能够回到预期的同龄孩子的发育阶段。 当她的第一个化学周期开始时,伊莎贝尔才10个月大,体重只有16磅。 在美好的日子里,她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