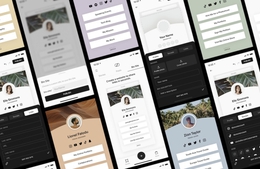中心问题:波斯中心的古代世界
近年来,人们做出了共同努力,以“全球化”对古代和中世纪世界的研究,并“分散”欧洲在近现代历史中的作用。第三到第七个世纪的学生有充分的理由困惑地看待这种趋势,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至少自1971年彼得·布朗出版《上古世界》以来),它的大部分历史就是西方欧亚大陆的真正重心不在地中海,而在波斯。
从220年代初期到630和640年代的伊斯兰征服,现在包括伊拉克和伊朗的土地构成了萨萨尼亚帝国的心脏地带。萨萨尼亚的酋长国在其首都切蒂芬(距巴格达约20英里)考察了广阔的政治视野:在西方,他们看到了主要的“文明”竞争对手罗马皇帝(最终从君士坦丁堡统治);在南部和东部,他们深入参与了阿拉伯世界,波斯湾,红海和印度洋的事务;在北部和东北部,他们争夺对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并与中亚的游牧帝国(例如匈奴人和土耳其人)相威胁,他们威胁要压倒他们的领土。
他们接待了欧洲蛮族国王的外交官和使节,同时派遣了自己的使节前往唐朝皇帝。在六世纪,罗马评论家认为这个帝国站在世界的中心。确实,在620年代,波斯国王莎胡二世几乎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濒临摧毁罗马帝国的边缘。如果他成功了,将会发生什么仍然是历史上的重大反事实问题之一。
因此,萨萨尼亚教士拥有丰富而复杂的意识形态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视自己为“中间罪行”的最高主人Eranshahr的主人,全人类的王子都应向他们致敬并致敬。作为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和编纂者),他们将自己描述为神圣秩序原则的捍卫者,在地球上以定居的城市化伊朗人口为代表,他们与该国野蛮的游牧统治者处于冲突之中图兰(Turan)体现了混沌原理,因此代表了它们的宇宙学对立面。中世纪初期的第一次“圣战”不是穆罕默德制定的圣战:相反,这是萨萨人与欧亚草原帝国的斗争。
在《伊朗的最后一个帝国》中,迈克尔·邦纳(Michael Bonner)撰写了一篇有关萨萨尼亚帝国兴衰史的令人钦佩的,透彻的,深刻的,全面的叙述历史。他散文的轻巧和优雅掩盖了其基础上的巨大学术努力。他利用拉丁文,希腊文,波斯文,亚美尼亚文,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的资料(以及翻译中的中文资料),并充分利用了考古学和造币业提供的信息。邦纳还不断谨慎地向读者揭示我们对萨萨尼亚世界的知识所依赖的证据基础,以及有关资料来源的问题和特点。从六,七世纪的鼠疫的影响到萨桑人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他谈到了许多重要而新颖的事情。任何想要介绍这个迷人迷失世界的人,无非就是从这本出色的书开始。
彼得·萨里斯(Peter Sarris)是剑桥三一学院的晚期古董,中世纪和拜占庭研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