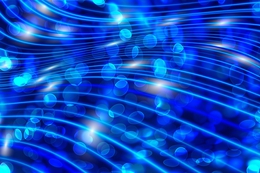技术解决主义不是解决办法
克里斯汀·罗森(Christine Rosen)是文化高级研究学院知识,技术和文化研讨会的主席。她是《传教优生学:宗教领袖与美国优生学运动》和《灭绝经验》(即将出版)的作者。
去年春天,当冠状病毒在美国漫长而致命的游行开始时,各州要求企业和学校关闭,人们呆在家里以限制病毒的传播,并通过视频会议平台(例如Zoom)进行交流和工作,微软团队和Skype被誉为技术的福气。与许多人在无限锁定期间所经历的炼狱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报纸上的文章树立了庆祝的基调,欢呼Zoom鸡尾酒时间的到来,并鼓励现在花大量时间在网上花费时间的美国人添加预选的数字背景,以描绘异国海滩和其他给他们打电话的快乐场面。
“ Zoom的女发言人Colleen Rodriguez对《华盛顿邮报》说:“看到人们如何使用Zoom以及他们如何发挥创造力,这使我们感到有些沮丧。 Zoom的使用有了惊人的增长:据《邮报》报道,“使用量已从12月的1000万每天的会议参与者增加到4月的3亿,包括商务和个人聚会。” 1 1 x朱拉·孔丘斯(Jura Koncius),“缩放欢乐时光的六个要点”,华盛顿邮报,2020年5月15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ifestyle/home/the-six-dos-and- donts-of-zoom-happy-hours / 2020/05/14 / e173af4e-93a0-11ea-82b4-c8db161ff6e5_story.html。
在危机中,Zoom(以及类似的视频会议程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直接,无缝的方式,使人们可以继续工作和社交,同时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物理距离。这是对大流行期间出现的许多复杂社会问题的简单技术反应,该解决方案似乎解决了实际挑战,同时也证明了Zoom口号的合法性:“我们提供幸福”。 2 2 x“关于我们”,Zoom,于2020年8月4日访问,https://zoom.us/about。
但是随着锁定期的过去,虚拟聚会从新颖性变成义务,每当新的Zoom会议出现在他们的日历上时,许多美国人就开始承认恐惧。人性,一种无法抑制的野兽,出现在“ Zoombombers”的故事中,他们利用该平台打断了课堂演讲和商务会议,以可恶的言论骚扰他人。然后是缺乏狂热的工人,他们忽视了关闭相机,对待同事以尴尬的方式展示了不经意间公开的私人行为。
到4月底,《纽约时报》记者凯特·墨菲(Kate Murphy)向读者解释“为什么Zoom太糟糕了”。她概述的失望不是技术性的(平台解决了其隐私和软件故障),而是经验性的。墨菲(Murphy)指出,即使在花了几个小时通过屏幕与人交谈之后,她仍对自己与他人的联系感到不安,因为她无法始终解释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微妙之处。这些破坏,有些是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会混淆感知并扰乱微妙的社会暗示。她的大脑紧张以填补空白并理解这种疾病,这使我们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隐约感到不安,不安和疲倦,”她写道。 3 3 x凯特·墨菲(Kate Murphy),“为什么缩放很糟糕”,《纽约时报》,2020年4月29日,https://www.nytimes.com/2020/04/29/sunday-review/zoom-video-conference.html。
此外,随着家庭生日,婚礼,仪式和其他庆祝活动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许多人的每一个细节都开始变得模糊。心理学家Gabriel Radvansky和Jeffrey Zacks描述了“事件边界”在记忆形成和认知中的关键作用:“事件是人类经验的中心,事件认知是对人们如何感知,构想,谈论和记忆的研究。他们,”拉德万斯基和扎克斯写道。但是,这些事件需要明确地划分界限,以帮助我们将彼此区分开,并形成我们经验的永久记忆。在锁定期间,我们无休止的Zoom商务会议和社交聚会源源不断地打破了界限,拉平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我们对这次危机的记忆,虽然这是一次很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事情更改。 4 4 x Gabriel A. Radvansky和Jeffrey M. Zacks,“记忆和认知中的事件边界”,行为科学最新观点17(2017年10月):133–40,https://doi.org/10.1016/j.cobeha .2017.08.006。
当然,还有其他替代方法可以进行缩放。在长时间的锁定期间,有些人使用了电子邮件或短信。有些人选择老式的电话;其他人重新发现了写作的谦卑乐趣。 5 5 x安迪·斯马里克(Andy Smarick),“科维德时代的来信”,评论,2020年6月;罗西·布朗特(Rosie Blunt),“写信:不连贯的时代中的联系”,BBC新闻,2020年5月20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52709729。但是,在这场危机中,许多人似乎都觉得Zoom和类似的在线会议空间比起诅咒更能带来福气。
正是美国人以迅捷和不加批判的热情接受了一个“简单”的技术解决方案,以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这表明我们越来越对技术解决主义感到满意,而不仅仅是在危机时期。在不确定性盛行的时候,这种默认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我们继续努力寻找自己的方向,值得考虑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已经做出的重大选择,并开始应对后果。
技术解决主义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它优先考虑针对人类问题的工程解决方案。它的首要原则是应用程序,机器,软件程序或算法为任何复杂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解决主义者对技术权威的呼吁,即使是制定公共政策或公共卫生措施的诉求,也常常表现为非政治性的,即使其后果通常并非如此。技术解决主义用未来的语言说话,但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在急于接受即时技术修复的过程中,其倡导者常常忽略了可能的长期影响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技术解决主义在实现其目标方面也常常毫不掩饰地激进,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阿朗·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是这种推理的较热心的提供者之一,他最近指出:“流行病很清楚:我们需要全自动奢侈品共产主义,”他将其描述为技术解决方案系统的简写,他称之为“围绕自动化,可再生的技术革命。能源,人工智能以及更多类似“信息商品”的物体。” 6 6 x Aaron Bastani,“流行病清楚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全自动的豪华共产主义”,OneZero博客,Medium.com,2020年7月10日,https ://onezero.medium.com/the-pandemic-makes-it-clear-we-need-fully-automated-luxury-communism-737a756ea1d9。巴斯塔尼(Bastani)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称为“全自动奢侈品社区(Verso)”。
即使很少有人购买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我们都在目睹并且在大流行的压力下,我们或多或少地放弃了自己对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两个领域日益依赖技术解决主义的依赖:公共卫生和教育。
甚至在COVID-19到达我们的海岸之前,美国人就我们采用技术的监视文化的利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Shoshana Zuboff等学者指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日常监视,如何对个人和自由社会构成长期威胁。 Zuboff写道:“数字领域正在超越并重新定义所有熟悉的事物,甚至在我们没有机会思考和决定之前。” “我们赞扬网络世界以多种方式丰富了我们的能力和前景,但是随着可预测的未来逐渐消失,它催生了全新的焦虑,危险和暴力领域。” 7 7 x Shoshana Zuboff,《监视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权力新边界上为人类的未来而战》(纽约,纽约:PublicAffairs,2019年),第4页。
但是,一旦危机爆发,以提倡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公共卫生措施为名,这些问题便被迅速搁置或忽略了,这些措施承诺提供更大的安全性并降低风险,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其实际有效性,也几乎没有关于其危险性的辩论。在以前的公共卫生危机中被证明有效的简单措施(戴口罩,洗手,保持距离)虽然被官员反复提倡,但被认为只是敷衍了事,当然不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