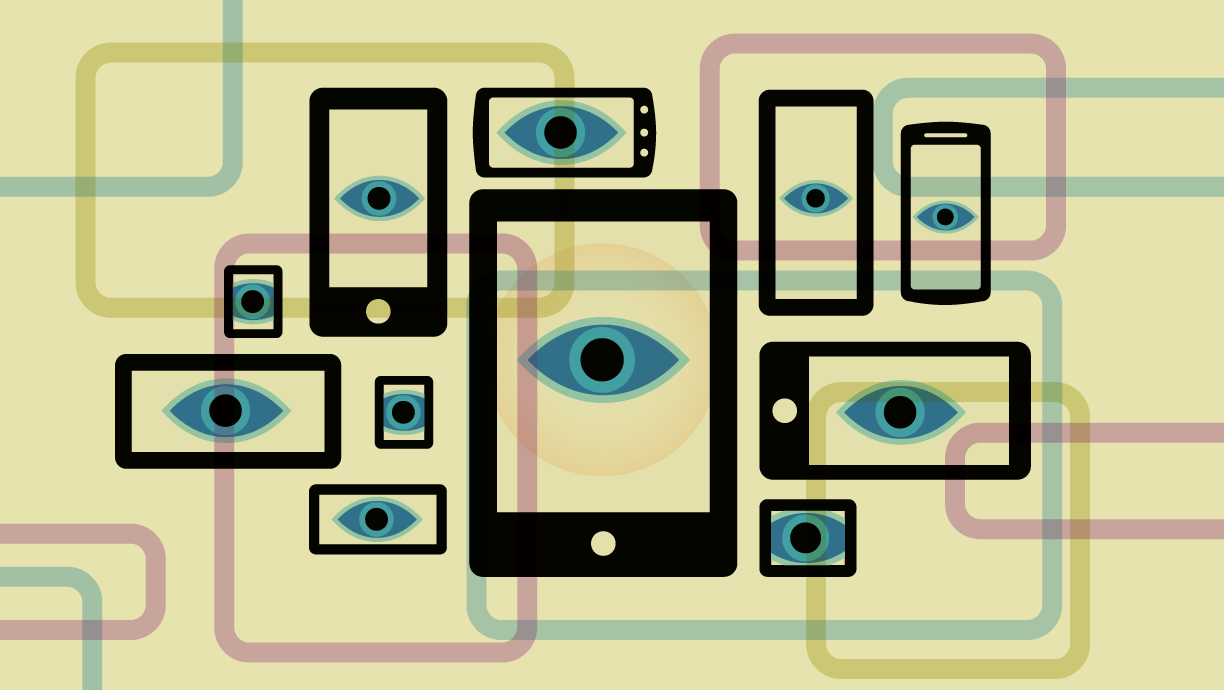所谓的“同意搜索”损害了我们的数字版权
想象一下这种情况:您要开车回家。警察将您拦下,据称是因为交通违规。提供许可证和注册后,警务人员会发问您:“既然您什么都没有藏起来,您不介意为我解锁手机,对吗?”当然,您不希望该人员复制或翻录您手机上的所有私人信息。但是他们有徽章和枪,您只想回家。如果您像大多数人一样,就会勉强遵守。
警方每年都要使用这种策略数千次,以回避《第四修正案》的要求,即在法官搜索某人的电话之前,根据法官对犯罪的可能原因进行的独立调查,警方必须获得逮捕证。这些误导性的“同意搜索”侵犯了我们的数字隐私,给有色人种带来了不同的负担,破坏了对警察搜索的司法监督,并基于法律小说。
立法机关和法院必须采取行动。在高度强制性的环境中(例如,交通停车),必须禁止警察对我们的手机和类似设备进行“同意搜索”。
在强制性较低的情况下,必须严格限制此类“同意搜索”。警方必须有合理的怀疑,犯罪正在发生。他们必须收集和发布有关同意书搜索的统计信息,以阻止和检测种族特征。同意范围必须狭义地解释。警察必须告诉人们他们可以拒绝。
当前,其他类型的侵入式数字搜索也基于“同意”。学校使用它来搜索未成年人的电话。警察还使用它从家庭物联网(IoT)设备(如Amazon Ring的门铃摄像头)访问数据,这些设备已简化,可满足大量警察的要求。此类“同意”请求也必须受到限制。
最终根据权证要求进行的“同意搜索”基于一种法律虚构:对军官对“同意”的要求说“是”的人实际上已经同意。理论上的原罪是Schneckloth诉Bustamonte(1973),该案认为,即使被搜查的人不知道其拒绝的权利,仅“同意”是搜查的法律依据。正如瑟古德·马歇尔法官在异议中解释的那样:
警察所要做的就是无可避免地成为寻求同意的伪装。如果他们表现出任何坚定的态度,那么毫无疑问将出现口头表达的同意。
历史证明马歇尔大法官是对的。现场数据显示,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同意”。例如,伊利诺伊州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所有交通站点的统计数据表明,约有85%的白人驾驶员和约88%的少数族裔驾驶员同意。
实验数据显示相同。例如,耶鲁大学法学杂志(Yale Law Journal)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名为“自愿同意的自愿性”的研究要求每个参与者解锁手机进行搜索。在两个大约100人的队列中,依从率分别为97%和90%。
该研究分别询问其他人,假设的合理人是否同意解锁他们的手机进行搜索。这些参与者自己并没有被征求同意。这两个队列中约有86%和88%(每个参与者约100名)预测,一个理性的人会拒绝同意。作者观察到,这种“移情鸿沟”出现在许多关于服从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中。他们警告说,法官在其会议厅的安全中可能会认为被警察拦下的驾车者可以随意拒绝搜索请求,而实际上驾车者则不会。
人们为什么不愿意遵守警察的搜索要求?许多人不知道他们可以拒绝。许多其他人有理由担心拒绝的后果,包括更长的拘留时间,超速罚单,甚至进一步升级,包括人身暴力。此外,许多精明的人员使用他们的单词选择和语气在要求客观怀疑的命令与不需要客观怀疑的命令之间跳线。
2020年10月,Upturn发表了有关警方对我们手机进行搜索的分水岭研究,称为“大规模提取”。调查发现,遍布50个州的2,000多家执法机构已购买了可以对我们的移动设备进行“法医”搜索的监视技术。此外,警察已经数十万次使用这项技术从我们的手机中提取数据。
Upturn的研究还发现,警方的许多此类搜索都基于“同意”。例如,在明尼苏达州的阿诺卡县,同意搜索占所有手机搜索的38%;华盛顿西雅图约有三分之一;在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占18%。
更为常见的是“手动”搜索,在这种搜索中,人员自己无需外部软件的协助即可检查我们手机中的数据。例如,在2017财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手动搜索与法医搜索的比例为十比一。手动搜索同样威胁着我们的隐私。警察实际上访问了相同的数据(某些取证搜索会恢复“已删除”的数据或绕过加密)。此外,警察使用手机的内置搜索工具来查找相关数据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与取证搜索一样,大部分手动搜索都是通过“同意”进行的。
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Riley v.California(2014)中所解释的那样,电话搜索对隐私的侵犯性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裁定,仅逮捕一项并不能免除警察在搜查电话之前获得逮捕证的一般职责。从数量上讲,我们的手机具有“巨大的存储容量”,包括“数百万页的文字”。从质量上讲,他们“在一个地方收集许多不同类型的信息-地址,便笺,处方,银行对帐单,视频,这些信息组合起来比孤立记录要多得多。”因此,电话搜索“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类似于“受现实限制”的容器之类的容器的搜索。而是通过电话搜索显示“个人私生活的总和”。
与受客观标准约束的决策者相比,当决策者具有高度主观判断力时,存在种族和其他有意或无意的偏见的风险。这在包括雇佣和执法在内的各种情况下都会发生。
是否要求一个人“同意”进行搜索是一个高度决定性的决定。该人员根本不需要怀疑,几乎总是会得到遵守。
可以预见,现场数据会在“同意搜索”中显示出种族特征。例如,与白人司机相比,2019年伊利诺伊州警察(ISP)寻求同意搜索拉丁裔司机汽车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多,但在搜寻白人司机的汽车时发现违禁品的可能性却高出50%以上与Latinx驱动程序相比。 ISP数据显示其他年份的种族差异相似。
当涉及到电话搜索时,警察很有可能同样经常从有色人种中寻求“同意”。尤其是在我们日益了解“黑人生活至关重要”的全国性认识中,我们必须制止这种不公平地加重有色人种负担的警察做法。
法官经常检查警察的无根据搜查。在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告采取隐瞒证据的行动,在民事案件中,如果被搜查人员起诉该官员,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无论哪种方式,法官都可以分析该官员是否具有必要的怀疑水平。这激励了人员在野外时转弯。并有助于确保执行《第四修正案》对“不合理”搜索的禁令。
警察通常通过获得“同意”进行搜查的简单权宜手段来逃避司法监督。法官失去了调查官员是否具有必要怀疑水平的权力。相反,法官只能询问“同意”是否真实。
鉴于上面讨论的所有问题,警察对我们手机的“同意搜索”应该怎么做?
立法机关和法官应禁止警察在处于高压环境中时,基于同意,搜索该人的电话或类似的电子设备。该规则应适用于交通停靠,人行道拘留,房屋搜查,车站软禁以及任何其他与警察发生的冲突,而合理的人将不愿离开。此规则应同时适用于手动搜索和取证搜索。
Upturn的2020年研究呼吁禁止移动设备的“同意搜索”。这是因为“手机同意书搜索的功能和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且无法解决,因此,“同意”是“基本上是一种法律虚构”。此外,同意书搜索是“种族特征分析的女仆”。
长期以来,诸如公民自由联盟(ACLU)之类的民权倡导者一直要求禁止在交通停站期间“同意搜索”车辆或人员。 2003年,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与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逻队达成和解,对同意书的搜查暂停了三年。 2010年,伊利诺伊州ACLU请求美国司法部禁止伊利诺伊州警察使用同意书搜索。 2018年,马里兰州ACLU支持一项禁止他们的法案。当然,电话搜索比汽车搜索更具隐私侵犯性。
在非强制性环境之外,某些人可能真正有兴趣让警察检查手机中的某些数据。一个被告可能希望提供地理位置数据,表明他们离犯罪现场很远。约会强奸幸存者可能希望从袭击者那里收到一条短信,显示袭击者的心态。在强制性较低的情况下,同意提供此类数据更有可能是真正自愿的。
因此,没有必要在强制性较低的设置中禁止“同意搜索”。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立法机关和法院也必须施加严格的限制。
首先,在进行电话同意调查之前,警察必须有合理的怀疑犯罪正在发生。大约在二十年前,新泽西州和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对在交通停止期间的同意书搜索施加了这一限制。罗德岛州法规也是如此。该规则限制了官员的主观判断力,从而限制了种族貌相的风险。此外,它可以确保法院在侵犯个人隐私之前,可以评估该官员是否有犯罪谓词。
其次,警察必须收集和发布有关电子设备的同意搜索的统计信息,以阻止和检测种族特征。这是警察对行人,驾车者及其影响进行搜查的一种普遍做法。当时,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帮助通过了伊利诺伊州的法规,该法规要求在交通停靠期间这样做。加利福尼亚州和许多其他州也有类似的法律。
第三,警察和复审法院必须狭义地解释一个人同意搜索其设备的范围。例如,如果某人同意搜索其最近的短信,则必须禁止警官搜索其较早的短信,照片或社交媒体。否则,对电话的每次同意搜索都会变成对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自由查询。出于同样的原因,EFF提倡即使根据授权书,也要缩小设备搜索范围。
第四,该人员必须在同意之前搜索某人的电话之前,必须将其拒绝的合法权利通知该人员。罗德岛州法规要求此警告,尽管仅适用于年轻人。这类似于著名的米兰达(Miranda)关于保持沉默权的警告。
当然,警察对我们电话的同意书搜索并不是威胁到我们数字版权的唯一同意书。
例如,许多公立K-12学校都通过“同意”搜索学生的电话。确实,有些学校使用法医技术。鉴于未成年学生与其成年教师和校长之间固有的权力失衡,学校对同意书搜索的限制必须至少具有与上述相同的保护隐私的能力。
此外,一些公司还建立了家庭物联网(IoT)设备,以方便警察向居民提出大量同意请求。例如,Amazon Ring建立了一个集成的家庭门铃摄像头系统,该系统使当地警察能够通过单击鼠标向居民发送一条消息,请求路人,邻居和他们自己的镜头。一旦警察掌握了录像,他们就可以无限使用和共享录像。基于环的同意请求的强制性可能不如在家搜索时强。但是,仍然必须遵守上述严格限制:合理怀疑,发布汇总统计数据,缩小同意范围的范围以及关于保留同意权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