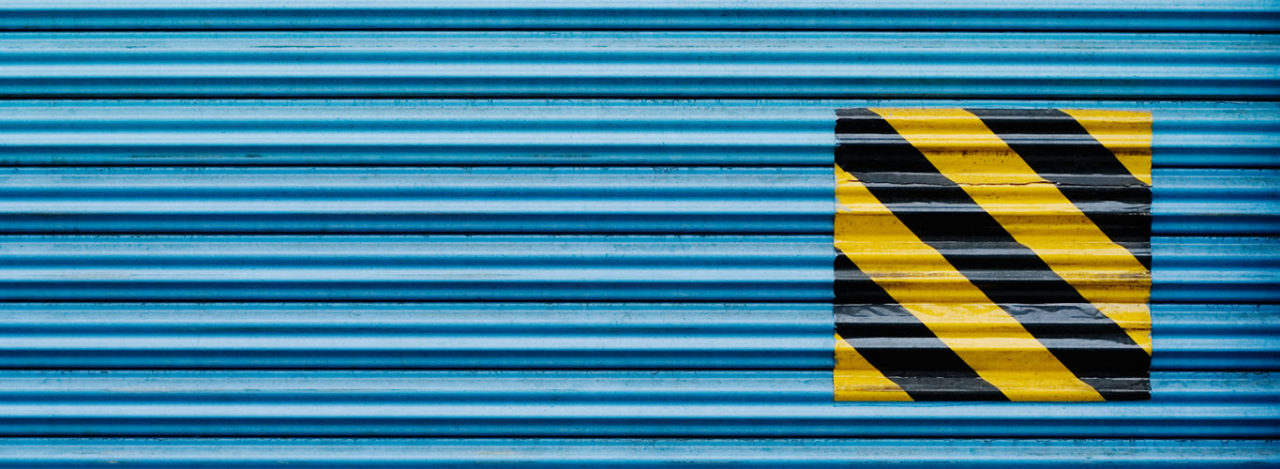感觉的声音无法说出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yadayadayadayayadayadayadayadada,”她开始,就像一个吟唱,没有,不,不,不,不,不,不,摇头,做她所能魔法在她面前出现的东西。这种反应,我感觉到的强度,比我所看到的更多。在早晨的阳光下,它的颜色如此清脆,我只能将现场视为某种博物馆展览,这是一部电影集。我打开嘴巴说,在我慢慢曙光恐慌中:'这不是一个笑话,是吗?“
这令我震惊了我,就像我说的那样,可能会让我感到震惊,就像一个奇怪的和令人惊讶的孩子一样,但当时,当时,它觉得我唯一的意思是我在感觉池中交叉的唯一意味着我沉浸在其中包括D.的共同语言世界。
“不,这不是一个笑话,”我的朋友说,她回到她的诵经,从现场转身。
几分钟后,她打电话给警察。我意识到这应该是我对警方发表讲话的是我并没有真正处于一定的状态,但这是日本,日本人总是做所有人的合适人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明智的:我以前从未打电话给紧急服务,我甚至没有知道有什么是正确的,礼貌,官方方式,说有人绞死了自己。
所以我站在那里,听,就像她开始听起来更平静一样,我听到了她放松了一个哭泣。
“不!”她倒下了电话,几乎过度通气,“不,我们不能把他带走,我们不能把他带走。”
把他带走,带他下来 - 日语单词,在她的嘴里,奥森瓦,奥森娜,有一些噩梦。它冲进了我的发呆,在那里种植了一个思想:如果他还活着怎么办?我仍然没有看到男人的脸,所以它似乎是一种独特的可能性。如果我要让这名男子戴上怯懦和娇气怎么办?这是它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然而,这一场景似乎似乎,它可能实际上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他可能会呼吸他的最后一个,因为我让我像水一样跑过我,而我的d留在手机上,我踏上了山顶的平坦表面,走到身体挂在哪里,我的心我胸口的打击乐器。山峰的峰值形状像薄锥形,这条路径一直以来,你可能会想象所有山顶的方式,如果你永远不会遇到仙女故事之外,那么绳子粘在一支在旁边的树枝上。身体的重量将绳索拉紧作为杆。没有刀子,我意识到,释放他就是不可能的。
就在我身后听到了我的声音,歇斯底里穿过它的闪亮线。我转过身来。
“我想检查,”我告诉她。 “我们不能让他失望。”
“不,”她摇了摇头,就像她试图摇晃现实一样震撼它,我充满信心地说'Orosenai'在手机上没有身体上的意思,而是别的东西。她有意思:带他下来不是在我可能的可能性的领域。我仍然怀疑,毫无意义,如果我能够,我本来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失望。我是否有胆量。在那一刻,我是否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
为了等待紧急服务,我们稍微沿着路径移动,靠在一棵定位在其侧面的大树。经过不长久的时间,我们听到警报器,然后从山脉的波兰管中搅拌。进一步下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暗锅炉西装的闪光,在携带巨大的担架的胸前围绕着反射带。我们开始向他们呼唤,最终半步移动,以便一直引导他们备份。在某个时候,当我们近乎在那里我抬起头来,试图衡量我们必须走多远,直到顶部,在那里,他在我面前,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脸,灰色米色颜色。
我以前从未见过一个死人。我怀疑,即使我有,在那里看到他会觉得好像没有。在山顶的顶部,我已经看到了他的背部并以为他是一个展览,这是一款诡计,突然将人类世界侵入这个自然空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在不同的世界中似乎没有这个世界方式,他仍然是令人叹息的味道与柔和的蔬菜和棕色的山脉,好像自然已经把他声称为自己的野蛮人。然而,他的表达,他的头脑倾斜,都是直接从一种可怕的胶片中脱颖而出。慢慢地,慢慢地,然后快速地,它在我挣扎时恍然大悟,恐慌疲惫的大脑,这正是可怕胶片基于的那种现实。
也许在像这样的危机那样,这将是这样的标准本能反应,这将是在某种程度上登记我所看到的,但我的本能保持沉默。我所有的精神血流都是针对内部消化的 - 我回到了一个被朋友家里被一只黄蜂被嘲笑的无言的孩子,太困惑并尴尬地对任何人说任何事情。如果我回到童年时,它就不会逃避我,无论是在这里玩我的父母,那么在这里突然爆发的爆发;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提醒她面对死人,让她进入歇斯底里,然后我会不得不处理。
夹克宣布他们从消防局设立工作的人,指示我们等待;作为发现身体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举行警察的陈述。我们再次走在山上,站在我们的背上到大的树干,标有路径的转弯。现在我告诉D:我看过他的脸,没关系。对我来说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我用这句话做了什么。我正在提出平静。没有什么是可怕的,我告诉我们两个人 - 一个人的实体比我想象的更坚实的形式。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爬到山上,这次是警察,谁必须在某些时候加入火战士。他告诉我们,那个男人已经死了。从他的身体中加强的开始,他们可以告诉他今天早上沉没了自己。看到他的脸后,我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我的一部分感到有些像救济一样的知识,即使我有一些奇迹设法让他失望,我就无法救他。我没有感受到责任。另一部分锁定在清晨的单词上:sōchō。现在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一个新的定义,敲击另一个,更标准的一个,到较低的位置。 sōchō:他杀死自己的时间。即使是几个月,几年后,人们会对我说,“我早上起床去跑步,”我想到了他,那个名字我们从未认识的人,并在喉咙里感到肿块。我会想象他在那里旅行。太阳又来还是不一样?他口袋里的绳子?他没有包。
Policemen说,像这样的美丽的地方,有一个观点的地方 - 这是人们想要这样做的地方。他似乎完全不受影响,因为我想你会是,或者必须是,在这份工作这么久之后。一个短,宽容,友好的人,带着动画的说法。每个人都知道自杀率在日本的高度,人们在通勤列车前跳跃的普遍问题,“蓝色星期一”现象在周末返回工作后的自杀率会飙升。当我从日本第一次回来时,我试图在自杀周围写一部小说;现在我可以看到我对任何事情都知道的几点。这并不羞于我觉得恰好,而是一种突然的广泛谦卑感。
我们想见他吗?警察问道。我们互相看着彼此,什么都没说,所以他继续:我们推荐它,人们发现它有所帮助。并令我惊讶的是点点头,说她愿意,所以我们走到所谓的观察牌上,这根本不是甲板,而是只是蔓延的地球。现在,布置在地上,绳子脱离了他的脖子,他看起来与我抬头看着他 - 他看起来像个男人。他看起来像一个你在火车上看到的人,谁没有露天的工作,他意味着没有伤害,谁没有发现很容易谈论他的感受。距离他们带来的机器,他们带来的机器,如果一个可能的话,他们试图重新播种他。
警察带我们去了一边,开始采访我们。也许十分钟以前,D已经对我说了一棵树干,“我想我会受到这个',我的回应是非常受伤的,”真的?“这是我的学位麻木,也许是震惊,但也感觉到内部世界上发生了几乎绝对的鸿沟,在发生语言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在他站在地球上时,在看到他成为历史中的人之后,麻木就开始了未处理。我试图在我发言时保持冷静,但在日本人描述了一小时之前发生了一小时的刺激任务。我说话,但我的声音很开心,对我来说,它不再清楚哪些细节很重要,哪个没有。最终我已经到了像我的账户一样结束,警察对我微笑。
“好的,”他说,铅笔在他的论文上掌握了,“所以你在山上,绕着一个圆圈,然后你抬起来,然后去吧,”uwaa!“
似乎是我,我可以觉得我的内心是转身。我知道这个男人无论是有意识的,都是试图让我的经验对我施加。他可以感觉到,我相信,害怕挂在我和d的迷雾,并且友好,善良,以医院工作者,幼儿园老师指导我们稳步回到一个是一个没有创伤的发现。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常态,在其经历中,我想象的经历,我想象的是几乎每天都有。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我感到含羞的不适感。勉强,只有只是勉强,我设法搞清楚了它发生了什么,它立即重新悔改,进入我所感受到的是动漫适应,我的故事的漫画版。 uwaa:当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时,你做的声音。我现在进入了在线日语/英语词典,并引出了以下翻译列表:
我什么都没说。我没有说是的,我没有说不,我盯着警察,再次沉默在里面发生的事情,我无法进入他共同共享的世界。
当我学习日语时,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表达的可能性所震惊;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我感受到了它的平庸,它的正常化能力,以及如何压迫这些事情。这是关于装扮我的思想和感情的兴趣,现在有一种感觉似乎很重要,我挂在一起,我不希望它通过平滑,制作的语言从我身边被偷走公共,可口易懂,可理解。我觉得我只用英语感受到了一些东西:如果表达的可能性会如此根本地歪曲我,那么卡通别人,那么我希望与他们无关。
现在年龄较多,更老和更聪明,更熟练的演讲者,不再在震惊的抓地力和更潜在的语言不足之情,我知道这只是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工作。警察并没有试图描述我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在我身上搬到我身上的感情和我所做的协会,而是为了故事讲座。他这样做是不是取代我的版本,但是他有他的报告所需的东西。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日语中的故事板更有可能包含声音效果。
然而,我仍然无法忍受通过那个乌瓦的镜头在那一刻想到我的感觉。代表我在单个单词中经历的复杂性,并且对于那个人来说,这不仅觉得我不仅背叛了自己,而且还背叛了让我感受到这种方式的人和世界这完全带来了它。如果来到那之上,我每次都会选择沉默。
这是Polly Barton首次亮相非小说工作五十声音的摘录,在APR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