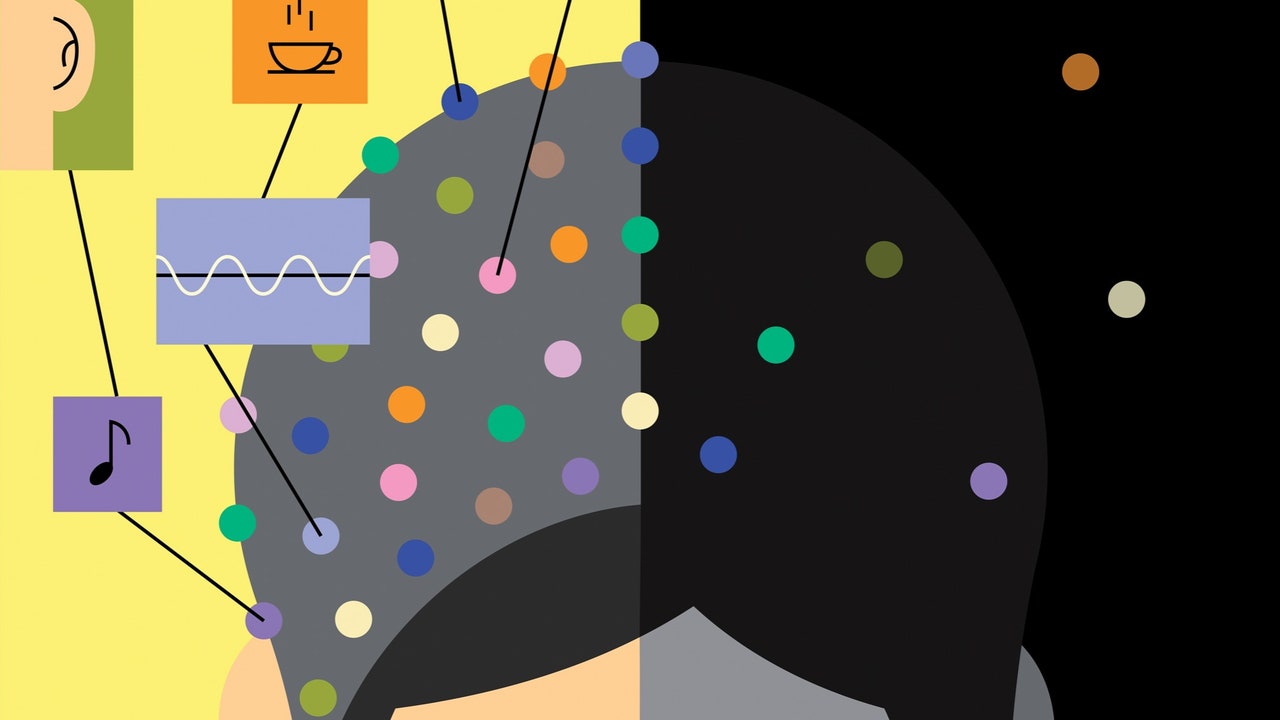脑植入物改变你的身份吗?
丽塔·莱克特的第一件事是当她恢复意识时看到的是一双刺耳的蓝眼睛,奇怪地凝视着她。 “我认识你,不是吗?”她说。蓝眼睛的男人回答说,“是的,你这样做。”但他没有说别的什么,而且虽然虽然是一段时间才醒目并盯着看。然后它来到她:“你是我的外科医生!”
它是2010年11月,Leggett刚刚在皇家墨尔本医院接受了神经外科。她回忆起孤独的激增,因为她在经营前一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独自一人等待,并且当她进入手术室时,她感到害怕。她担心外科医生切断腰部长度的头发。我在这里做什么?她想。但就在麻醉占据之前,她回忆道上,她曾据说,“我应该得到这个。”
Leggett四十九岁,自她出生以来患有癫痫患者。在操作期间,她的外科医生和德鲁莫科夫在她的头骨内放置了一个实验装置,其中一部分脑电器界面,它希望能够预测她即将有癫痫发作。由西雅图公司开发的设备,叫做Neurovista,已在医学研究中进入一个试验阶段,作为“首先在人类中”。从墨尔本的三个着名的癫痫中心绘制的研究团队选择了十五名患者来测试该装置。 Leggett是患者14。
她的癫痫发作了很多表格。在学校,她会发现,只有当老师在她或她的同学嘲笑时才会出现。曾经,作为成年人,她在烘干菜肴时,当时呼喊和没有警告,她送一块飞往空气中的餐盘,然后奇怪地设法抓住它。并非所有的缉获都是如此轻柔。有一个时间她摔倒了一些楼梯,在医院后醒来时,她的下巴如此糟糕地破碎,外科医生必须拿一块她的肋骨来重建它。 Leggett是四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另一个时候她在暴力癫痫发作后住院,她的青少年儿子被指控殴打她。
当Leggett的神经科医生询问她是否想参加Neurovista审判,她毫不犹豫。两个月后,她在手术室里有一个小洞,在她的头骨上钻了。摩洛哥仔细编织了她的头发,这样她就会失去尽可能少。一旦他制作了洞,他就把一个横向形的硅树脂条滑动并铺设在她的大脑表面上。带有十六个电极的条带,摩洛哥在Leggett的皮肤下,摩洛哥跑车,在她的耳朵后面,躺在她的脖子上,以与他植入胸部的装置连接。该设备将接收记录Leggett的神经活动的数据,并将其无线传输到外部处理单元,她应该随时与她保持一致。
外部单元的两个翻转电话的大小在一起,它需要一些习惯。如果系统预测缉获似乎是塞起,则该单位会用红灯警告她,令又嘟嘟声,虽然她发现令人痛苦地响亮并转过了声音。公司让她尝试在肩带上携带设备,困扰着她,或者在腰带上的小皮套上,这效果更好。她被告知要保留日记,每次她经历癫痫发作时都会注意到。
虽然Leggett适应了自己的设备,但实际上,该装置的效果是适应她的。由她头部中的装置检测到的电信号被传输到实验室,其中一组计算机开始读取她的神经活动的模式,构建对她的需求定制的算法。
最初,Neurovista患者器件记录的读数是如此奇怪 - 与正常的脑活动或典型的癫痫的模式不同 - 试验几乎被遗弃。后来,研究人员意识到大脑简单地反应被篡改 - 术后伤口的电气量值。这次干扰在几个月后沉降了,然后系统的学习开始了。一旦设备录制了一半的Leggett的典型癫痫发作,研究人员就可以将算法微调到她大脑的独特电力签名,即可将界面从观察到预测移动到预测。
该设备首次发出警报时,Leggett在理发师,她家的几个街区。外部单元显示白光,然后是红色的。她仍然记得它的冲击 - 让机器与她沟通的陌生性并建议她在她头脑中发生的事情即将发生的事情。她被告知该设备能够在癫痫发作前十五分钟警告她。这给了她的时间离开美发师并在家安全地睡觉。
科学上,Neurovista试验是成功,验证其潜在的概念并产生丰富的有用数据。这也是Leggett的成功,但是,这种方式比她或研究人员更深入,更复杂。目标很简单:通过让她更加控制她的病情来改善她的生活。然而,效果是让Leggett感觉像一个完全新的人。她从来没有自我以前相信。当我和她谈话时,她谈到了这个设备,好像是合作伙伴。 “我们被校准在一起,”她说。 “我们成了一个。”
自F.D.A以来,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首先批准了使用深脑刺激的装置 - 治疗必要的震颤和先进的帕金森病。今天,在全世界至少有两十万人,患有各种各样的条件,生活在某种神经植入物中。近年来,Mark Zuckerberg,Elon Musk和Bryan Johnson,Printree的付款处理公司的创始人都宣布了恢复甚至提高人类能力的神经技术项目。正如我们进入这个新的超人类智力的新时代,很明显,许多人与他们的设备发展强烈的关系,通常对他们的身份感影响。这些效果虽然仍然很少研究,但对治疗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人脑是超级银河系复杂的小电气装置。它包含一个估计的百亿个神经元,它们之间的更多联系在于银河系中的星星。每个神经元通过将电荷沿其长度传递电荷,导致神经递质跳到下一个神经元,这依次点燃,通常与数千人在一起。不知何故,人类的智慧从这种常量,激动人心的编舞中出现。它如何发生仍然是一个几乎完全的谜,但很明显,只有他们学习这一舞蹈的步骤,神经技术才能与大脑同步。
在她的手术后三年,Leggett和她的设备一起愉快地生活。但2013年,她的神经科医生给了她一些坏消息。 Neurovista已经耗尽了资金和停止运营。 Leggett的神经装置必须出来。
2020年1月,在澳大利亚夏天结束时,我沿着里德车道,过去的松树种植园和远程庄园,到南澳大利亚小镇。这是一个炎热,干燥的一天,但虽然火灾在他们没有到达这里的大多数国家都在燃烧。 Rita Leggett住在一个漂亮的殖民地风格的房子里的镇边缘。在它背后,一棵粗糙的树胶树超过一百岁的牙龈树在废弃铁路的旧铁轨上铺展了它的分支。
Warning: Can only detect less than 5000 characters
Gilbert在他的采访中遵循了一系列标准的问题,但在某些时候,他会放弃剧本。他没有遇到任何人透露出来谈论与脑电电脑界面合并的主观经验。 “与设备一起,我发现自己,”Leggett告诉他。 “这个设备成了我。”他一直要求她告诉他更多。她的意思是,她发现自己并成为她的意思?当她用全部结束的方式表达了挫败感时,吉尔伯特想挖掘那个经历。他的问题很简单,但他可能会感觉到她,他们是一个释放和启示。
吉尔伯特认为,神经技术注定要为我们的生活中的迫切需要审查和监管。四年来,他一直在组建一个独特的证据,以支持他的观点,通过寻找脑植入物和学习他们的经历。他相信Leggett经过的不仅仅是去除设备。当设备和Leggett开始合作时,一个新人出现 - 一种脱秀的身份,一种机器和思想的共生。吉尔伯特将这种情况与电影“刀片跑步者”相似,其中人类的Androids培养了自我感,并逃避他们的创造者。
塔斯马尼亚大学,吉尔伯特自2010年以来曾在霍林顿山脉的山麓努力工作,俯瞰着庞大的河流。当我在那里拜访他时,这是一个明确的日子,并爬到他的车上陡峭的山丘,感觉就像爬梯子一样。吉尔伯特,谁是哲学家的四十多岁和不寻常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并没有停止呼吸。他在附近的森林里,他的一些最疯狂的森林,他的老板们又徒步旅行,他后来告诉我,他是唯一一个在塔斯马尼亚南海岸赛道上取得个人最好的人,六天通过减少他携带的水量,通过荒野。
吉尔伯特在魁北克市以外的一个农场上长大的一个巨大的家庭。他在农场做了家务,并在附近的森林里玩了几个小时的森林和他的兄弟们的表兄弟。吉尔伯特在一支足球队上,是一个特别快速的跑步者。当他在19世纪纪念日时,法国的一支美国足球队,巨人队圣·Étienne,为他提供了一个地方。他在欧洲和他们一起旅行,一年后他回到魁北克队踢了大学橄榄球,但他已经过度训练并受伤了自己。当您在一个背景下构建您的身份时,他告诉我,失去您在这种情况下有用的能力破坏了您的身份。 “你觉得无用,徒劳无功,”他说。他决定他需要休息一下。
吉尔伯特搬到瑞士,并在学习哲学学习日内瓦大学。他发现哲学概念最重要的是人们生活中有形的重要性。当时,克隆是一个热门话题,吉尔伯特写了他的硕士学位。对他来说,克隆可以完全重现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的假设,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我们五年或十年前的人。他的博士学位进展,他研究了自由意志,并开始与大学边界在遗传实验室的科学家闲逛。这让他以科学的方式考虑确定主义。如果有自由的东西,他决定,它必须是生物学的。
这是在二千岁的时候,围绕F.D.A.将深脑刺激的批准扩展为帕金森的一般治疗。研究大脑 - 计算机界面,由国防部大部分地推进。该领域对吉尔伯特自由意志的工作有吸引人的影响。假设人为刺激的大脑犯罪的人:他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吗?
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深脑刺激是有益的和生命变化,但偶尔有奇怪的行为反应报告,如丑陋和过度的高度。然后,在2006年,法国团队发表了关于其他成功植入意外后果的研究。脑植入后两年,六十五名患者在其婚姻或关系中受到崩溃,六十四个百分之百分点想要离开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的智力和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水平与以前相同,或者在焦虑的情况下,甚至有所改善,但它们似乎从自己身上遇到了基本的疏远。一个人喜欢电子娃娃。另一个人说他觉得Robocop在遥控下。
吉尔伯特将自己描述为“应用的消除主义者”。他不相信灵魂,或者一个心灵,至少在我们通常想到他们,并且他强烈地提出了你可以称之为自我的东西。他怀疑婚姻崩溃的人建立了他们的身份及其在病理周围的关系。当那些被移除时,关系不再有效。吉尔伯特开始采访患者。他使用了标准化问卷,这是一种方法论对实现可靠的比较至关重要,但很快他就会感到遗憾的是,当个别故事被遗弃时丢失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人类经历。即使这些身份发生变化,他正在学习的效果是米中的含糊不可分割。
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在治疗后的人完全不同于他们曾经梦想过症状的人。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不协调的浮力和信心。一个女人感觉十五岁年轻,并试图抬起一个泳台桌,在她的背上破裂了磁盘。一名男子注意到他的新发现信心为他的妻子努力了;他太“全面”。另一个女性变得冲动,在手术后九天散到心理学家的预约10公里。她对她的家人无法辨认。他们告诉她,他们为老她悲伤。
Neurovista审判中的每个人都喜欢他们的设备,以Rita Leggett所做的方式。在墨尔本的南部,我遇到了一个古怪的思想妇女,她在三十岁的古怪,她曾在循环中告诉我,衷心的叙述她如何讨厌她。作为一个孩子,她告诉我,她为舞蹈而奋斗,但是当她十六岁时,她有第一个宏伟的马士
......